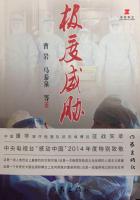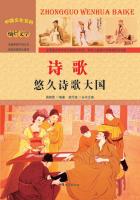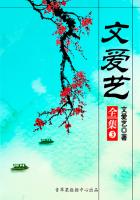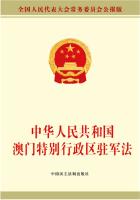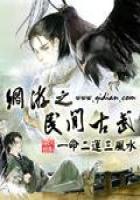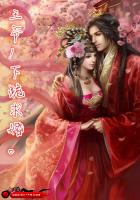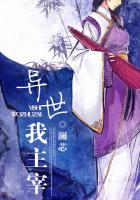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历史上的游侠进入现代学术的视野,可以说已有一个世纪了。从晚清社会一些维新派激进分子和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所进行的、旨在为社会政治变革张本的有关侠之源流与精神品格的探讨,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文化热及武侠小说热而不断升温的诸多对中国侠文化的考察论证,尽管各个时期的学术立场及视点有所不同,中间也有过曲折的历程,应该说在许多方面的研究还是不断地走向具体、丰富和深入。然而,当我们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以一种更为苛责的眼光重新审视过去一个世纪所获得的研究成果,会发现仍有缺憾存在。例如像游侠在历史上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社会角色这样一个最为基本的命题,笔者认为研究者们至今仍然未能给出一个明确一致的合理判定。
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一命题在二十世纪其实已经在个别学者的考述中获得正确的结论,却终于未能赢得普遍的关注与认同而被悬置了起来。
诚然,整个二十世纪的游侠研究似乎不间断地一直在进行游侠社会身份的探讨。美籍学者刘若愚教授在其六十年代撰作的《中国之侠》(犜犺犲犆犺犻狀犲狊犲犓狀犻犵犺狋犲狉狉犪狀狋)一书中,曾经归纳了此前几种他认为揭示游侠社会渊源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它们包括:冯友兰教授于1936 年、劳干教授于1950 年发表的游侠清一色地来自平民(并以游侠为职业)说,陶希圣先生于1931 年、杨联升教授于1957年发表的游侠不全都出身于平民(也有破落的武士成份)说,以及日本增渊龙夫教授于1952年发表、并得到刘氏本人赞同的游侠不是特殊的社会集团(不过是一群具有侠客气质的人)说。在六十年代的大陆学术界,以阶级分析为准绳,更有过一场游侠到底属于哪个阶级(是属于穷困的、受压迫的下层人物,还是属于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的争论。至于八十年代以来诸多有关侠文化、侠文学的著述,一开篇也都会首先涉及对游侠原始形态之社会构成的认识与界定。问题在于,这方面的探讨大都仍未能有效地帮助澄清游侠的本来面目。三四十年代那些从社会史角度提倡游侠来源于平民或破落武士的说法,大抵奠定了将游侠形象勾画为集游民、武士、门客于一身的一般知识,虽然受到过这样那样的质疑,但其后人们的阐释仍对此多有沿袭。这些说法的一个主要依据,归根结底,在于韩非将“带剑者”列为“五蠹”之一,又说过“侠以武犯禁”,以及“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之类的话,于是“私剑”即径直被视作游侠,为私门效力、专事“行剑攻杀”成了游侠最为主要的特征。
然而,诸如此类的特征与司马迁在《史记· 游侠列传》、班固在《汉书·游侠传》中所载战国时信陵、平原、孟尝、春申四公子那样“藉王公之势,竞为游侠”显相牴牾。从司马迁、班固的记载来看,当然表明至少汉代学者并未将游侠仅限于平民,刘若愚教授即据此而证否前二说。不过,这里更值得追问的恐怕应该是,“私剑”是否就是游侠?如果是,为什么司马迁在《史记》中要将游侠与刺客分列二传?如果不是,那么出身贵族的战国四公子与出身平民的朱家之流并可称为游侠,他们之间共通的特性究竟在哪里?刘先生最终以“习性”、“气质”来解决游侠在社会出身上的不一致性,作出“他们是具有强烈个性,为了某些信念而实施某些行为的一群人”这样的结论,在当今的学术界亦已为不少论者所接受,看上去是抽绎出了“卿相之侠”与“布衣之侠”的共通特性,实际上却因未曾解决“私剑”与游侠之身份关系这样一个前提(如他仍将荆轲一类的刺客列为战国的游侠加以介绍),而仍未切中早期历史上游侠之事实特征。当然,下面将会说到,这与其书所讨论的基点在于侠文学是有关系的。因此,上述这样的问题如果得不到切实的解决,则游侠的真实面目终难得到准确的揭示,他们在社会上的作用、地位也难以得到充分的估价。
二、游侠非“私剑”
其实,早在1942年2 月,钱穆发表于《学思》第1 卷第3 期的《释侠》一文,已经在逐一检讨战国、秦汉以来有关文献对侠的解说与定义的基础上,多侧面地对侠与“私剑”进行了辨析(刘若愚教授偏偏忽略了这样一种重要的观点)。钱文的中心在于辩驳“近人遂有疑侠即墨徒,遂目儒墨为文武士之分者”,据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我们知道这主要是针对冯友兰所持说的儒、侠之对立即儒、墨之对立,因墨即出于侠。钱氏在举证儒墨与游侠流品各别时,曾专门对何为游侠提出自己的看法。首先,他体会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所言游侠与韩非微异:“史公特指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为侠,至其所养,则不当获侠称,故曰匹夫之侠,湮没不见。如史公意,养私剑者乃侠,而以私剑见养者非侠。故孟尝、春申、平原、信陵谓之卿相之侠,朱家,郭解之流谓之闾巷之侠、布衣之侠”。尽管对于先秦时代匹夫之侠何以湮没无闻的原因(或者初始究竟有无布衣之侠)我们尚可展开讨论,但太史公指为近世游侠的战国四公子与韩非所说的“私剑”
明显不同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正是基于这一点,钱穆先生进而在“养人”与“见养”的性质上将游侠与“私剑”明确地区别开来:游侠是“盛养门客,食客,刺客者”,“私剑”不过是游侠门下所养的刺客一类人物。这在为我们厘清游侠与刺客分际的同时,实际上也揭示了卿相之侠与闾里之侠、布衣之侠的共通特性。其次,他以荀悦“立气齐,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如淳“相与信为任,同是非为侠,所谓权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汉书·季布传》颜师古注“侠之言挟也,以权力侠辅人也”等有关定义为佐证,意在说明游侠在“结私交”上所具有的非凡的“威”、“强”、“权”、“力”,非一“私剑”之武力技艺可当,这恰好表明,上述诸说于游侠亦显然“主养人者言,不指见养者言”,“谓侠辅人者为侠,非见侠辅者为侠也”,“否则一剑之私,岂足以武犯禁乎?”如此一方面是从行为方式的角度进一步对游侠与“私剑”作出判别,正如他接下来不烦引证,重申太史公所述游侠之行谊,无论是设取与然诺,还是振人不赡,趋人之急,无论是以躯借交报仇,还是藏命作奸,凡其种种“修行砥名”之举,皆为救人急难而维护所与交游的利益,“岂有专指私剑之养、刺客之勇、武士之一德,而即以谓之侠乎?”从而引导我们把握游侠的基本特征在于结纳(特别是司马迁说的“士穷窘而得委命”)而非行剑攻杀;在另一方面,则在展示游侠的“威”、“强”、“权”、“力”与“私剑”的武力性质之不同,以及指明游侠是权力的拥有方与施与方、因而其社会地位与影响与“私剑”不可同日而语上,为我们提供了富于价值的认识。再次,他又就“任”的释义,推原古人于“任侠”之所指:“《史记· 季布传》集解引孟康曰:‘信交道曰任。’如淳则曰:‘相与信为任。’《说文》:‘任,保也。’《周礼》:‘五家相比,使之相保。’夫五家相保所以便于讨亡命而诘奸,今任侠之保,则特为信然诺以藏匿亡命而作奸。然则将亡命者为任侠乎?抑藏匿亡命者为任侠乎?此不烦辨而知矣。”认为游侠无疑应是藏匿亡命者而非亡命者,以此来补证上述游侠与“私剑”在“养人者”与“见养者”、“侠辅人者”与“见侠辅者”之间的界别。
总之,经过钱氏辨析的游侠身份与时人所论迥然有异,他们不是寄人门下的宾客地位(当然也不是什么武专家或者武士),而是以盛养宾客、招纳“私剑”、藏匿亡命而拥有相当权力的“私门”之主。关于这一点其实不难理解,身为卿相之侠的战国四公子,自不必说,广招天下贤者,门下宾客如云;即便是布衣之侠如朱家,也是“所藏活豪士以百数,其余庸人不可胜言”,又郭解,所养宾客当亦不在少数,以至“邑中少年及旁近县贤豪,夜半过门常十余车,请得解客舍养之”。很显然,尽管所处时代、社会条件不同,政治地位也各有差异,但他们在广招宾客这一点上是共通的。也正因为如此,班固在《汉书· 游侠传》中将汉初代相陈豨,吴王刘濞,淮南王刘安,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侯等新一朝代的王侯权贵也尽数列入,原因即在于陈豨是常常“从车千乘”;刘濞、刘安是“皆招宾客以千数”,窦婴、田蚡也是,其徒属“竞逐于京师”。至于该传所叙汉成帝河平中王尊所捕击的那些市井之侠,如萭章及作箭者张回、酒市中人赵君都、贾子光之流,亦无非“报仇怨养刺客者”。原涉初与新丰富翁祁太伯为友,太伯的同母弟王游公一向仇视原涉,就在新上任的茂陵守令尹公面前给他罗列了许多罪状,其中重要的一条便是“涉刺客如云,杀人皆不知主名”。可见钱穆所谓游侠皆“盛养门客、食客、刺客者”,言之有据,游侠非为人所养之“私剑”,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明白了这一点,则司马迁将游侠、刺客分列二传的问题便也迎刃而解了。
不过,这里也还存在着一个问题,钱氏并未就韩非所论本身对游侠非“私剑”作出进一步辨正,尽管他在上述辨析的最后引韩非《六反》之说,以为其言任侠本与廉勇有殊,一则活贼匿奸,一则行剑攻杀,此亦无大异于司马迁,然而若由他认为司马迁言游侠与韩非微异的立论来推导的话,则似乎他自己也觉得韩非至少在《五蠹》中所论是将“游侠”与“私剑”的概念混为了一谈。
如果汉代史家对游侠的认识与更早的韩非真的不能一致,那么这种对于游侠的重新诠释仍将不能令人信服。这里的关键恐怕就在对韩非《五蠹》中“群侠以私剑养”一语的解读。钱穆先生是将此句理解为群侠以私剑见养,亦即群侠由于是私剑而为人所养,故认为与太史公所载以盛养宾客的战国四公子为游侠有异。
究竟这样的解释是否符合作者的原意,看来还是应该作全面而审慎的推究,作为游侠产生时代见存最早的见证,韩非之说毕竟是无法绕开也不应绕开的。
在八十年代以来诸多对游侠探讨的著述中,章培恒教授发表于《复旦学报》1994年第3 期的《从游侠到武侠———中国侠文化的历史考察》是一篇值得重视的论文。如题所示,这篇文章旨在探求中国侠文化中“游侠”演变为“武侠”的过程,而要准确地描述这一过程,首先就必须对先秦和汉代游侠的实质有一真切的把握。在对游侠的原始意义及其实际内涵在先秦至汉代的变迁进行考察之后,作者得出结论,作为中国早期历史上实际存在的游侠,是广结宾客、不顾个人利害地拯其困厄、并由此获得广泛社会影响和强大力量的人。这一对游侠的重新诠释,在将其与“私剑”之性质、特征作出明确区分上,与钱穆先生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章文是从正面给予了游侠一个更为完整、准确的定义,而在论证过程中,则以《韩非子·五蠹》论侠的一段文字作为主要论据,对作者原意作了重新阐释,这又恰可成为钱文所论的补正。简括说来,章文据《韩非子·孤愤》中的有关论述推导出,所谓“私剑”,当是“私门”之“剑”,而非旧注以为的“侠客之剑”;又证之以同书《八奸》,得出“私剑”实即“私门”所聚的“带剑之客”、“必死之士”,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杀手。鉴于此,将“群侠以私剑养”释为“群侠由于是私门杀手而为君主所养”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将“群侠”全都作为私门杀手不符合事实,而只有理解成“群侠以其私剑养”,也就是“群侠”由于其“私剑”而为君主所“养”方为妥贴(这里的“养”,与上文“诸先生以文学取”的“取”
互文同义)。《五蠹》下文所说的君主“养游侠、私剑之属”,则是因“游侠”既以其“私剑”而为君主所取,也就意味着其“私剑”也为君主所“取”。经过这样的解释,韩非所论的游侠与“私剑”显然亦不是一回事,他们的身份确然有别,游侠不是门客而代表“私门”,“私剑”则是它的徒属,所谓的“侠以武犯禁”,并不是说游侠自己行剑攻杀而犯禁,而是用其“私剑”之属行违法之事。
这一推证意味着韩非在论说游侠的问题上与汉代史家并无歧义,而这一点对我们全面考察先秦、汉代的游侠是至关重要的。
在游侠与“私剑”之间作出明确区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个世纪以来人们所持有的对游侠的一般认识,正是在混淆了游侠与“私剑”之概念的前提下作出的判定与描述,无论是赋予它游士的特征、门客的特征还是武士的特征,实际上都是将“私剑”的种种特质加诸游侠之身,或者至少是将游侠与“私剑”的特质杂糅在了一起。虽然这种一般认识的形成,有其更为复杂、深远的历史原因,但只要循着此一线索,我们便获得了趋近游侠历史本真的款要。
三、作为一种豪强的游侠
既然游侠非“私剑”,而是盛养宾客、招纳“私剑”、藏匿亡命的“私门”之主,那么它在社会上所担当的角色及作用、地位应该重新得到认定,因为以往人们认识上那种“游侠”与“私剑”的错位,使得游侠在社会上的地位、影响明显地被低估。
在六十年代有关对游侠所属阶级的认定及其评价问题的讨论中,已经有学者对当时学界认为《史记· 游侠列传》中所描述的游侠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该传体现了高度的人民性的主流意见提出过自己不同的看法,认为从朱家、郭解、剧孟等汉代“布衣之侠”的经济状况及他们所藏匿亡命的成份来看,游侠不是穷困的、受压迫的下层人物,而是地方上的“豪强大家”,属于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所谓的“豪强大家”是否一定就是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这是值得商榷的,并且仅以财产多寡的标准来衡量游侠的地位、身份也是不够全面的,因为许多平民出身的游侠,其“散财结纳”之财力并非本身具有,而是“作奸剽攻”、“铸钱掘冢”之非法所得。又对游侠来说,财产不过是拥有权势的一种手段。不过,这一观点对于我们重新认识游侠的实际身份与地位还是有所启发的。
我们知道,汉代的学者往往又将游侠称作豪、贤豪、豪侠、豪桀、豪俊乃或豪猾,如《史记· 游侠列传》中即多“贤豪”之称,司是指那些以出众的才智与德行赢得威信的人。按照古人的看法,“德”与“威”是相辅相成的,所谓“德盛者威广”,而“道德之威成乎众强”,也就是说,惟有以种种德行才能建立起令众人服从的权威,从而获得强大的社会力量,故如《淮南子》一再强调:“人以义爱,以党群,以群强,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则威之所行者远,义之所加者浅,则武之所制者小矣。”“能强者,必用人力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⑨游侠而称“豪”,或者成其为所谓的豪强,正在于它是以种种修行砥名的手段广结宾客,通过尽力维护这一交游圈中人的利益来获得他们生死与共的拥戴与效力,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集团势力,从而拥有现行政治权力结构之外、能为社会所仰赖的一种个人权威。如此来理解荀悦《汉纪》中的定义———“立气齐,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以及司马迁《史记· 游侠列传》所说的“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应该有更明晰的感受。
那么,以游侠为豪强,是否仅仅是汉代学者的看法?或者换一种角度说,是否仅仅汉代游侠才具有豪强的特征?有一些研究者即持这样的看法,如认为“西汉时代的游侠是以著名侠魁为核心的社会集团的方式进行活动的。这与战国时代游侠以分散、个体方式进行活动不同”,“西汉豪强与游侠交往甚密,游侠也逐渐与豪强融为一体。这同战国时代游侠依附于权贵的情况不一样”。这里的问题在于,虽然作者依据《史记》、《汉书》中有关游侠的记载,已认识到了汉代游侠拥有某种集团势力的特征,但对战国游侠的认识仍在“私剑”的错位上,而将战国四公子视作是养游侠的“权贵”而非游侠之本身。其实韩非在《八奸》中就曾说到过,在所谓“人臣之所道成奸”的“八术”中,有一术叫做“威强”。他解释说:“为人臣者,聚带剑之客,养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为己者必利,不为己者必死,以恐其群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谓威强。”根据前面已引的分析,这一类“为人臣者”,应该就是司马迁说的战国卿相之侠,他们聚养“私剑”之属,欲以个人拥有的权威对朝廷、社会产生影响,其结果亦势必将令人主被“壅劫”
(谓蒙蔽挟制)并“失其所有”,故韩非认为“不可不察”。这里说的“明为己者必利,不为己者必死”,即其《饰邪》中所说的“人臣之私义”,而所谓“行其私”,即其下文中所说的“人臣私其德”,因此,从韩非所描述的“威强”的种种特征来看,则游侠原来就是一种豪强。
揭示游侠豪强身份的意义在于,它将有助于我们从权力的角度来重新认识与评估游侠的存在。以往人们在分析游侠的社会渊源时,往往将关注的焦点投注于“王纲解纽”之社会剧变下“四民”阶级构成的升沉变化,其结果,社会权力结构所发生的变动反倒被遮蔽掉了。的确,游侠的产生与春秋以来随周王室衰微而出现的政治失序、社会动乱之背景有关,然而它的出现与其说是以原来固定的生产关系及社会阶级发生变动为契机,不如说是其时政治权力下移的一个直接的后果。《汉书·游侠传》在一开头自古代国家政治权力的等级体制及其崩坏叙起,是有着非常敏锐的政治家眼光的。班固将游侠之兴作为承“周室既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桓、文之后,大夫世权,陪臣执命”、“陵夷至于战国,合纵连衡,力政争强”三个政治权重逐级而下的阶段后,君主专权的政治结构进一步失衡所产生的一种新的情况,这种新的情况表现为一些“人臣”放弃了他们在原有政治秩序中的职责,而在此正常政治权力结构之外,通过结纳宾客、藏匿亡命,另构一种个人权势,如“四豪”,如虞卿,此即所谓“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这样的游侠,也正是韩非一再提到的与“主上”、“公庭”相对之“私门”,而其《八说》中所说的“弃官宠交谓之有侠”、“有侠者官职旷也”,也正是从这种情况来对他们加以定义的。到了汉代前期,君主独裁的高度集权化政治体制尚未完善,新一代权贵之“卿相之侠”通过广招宾客发展个人权势,自然构成对天子权威的威胁,而如朱家、郭解那样的“布衣之侠”,以一介平民“结私交”、“立强于世”,作为一种地方势力的代表,亦在现行权力体制外行使其个人权力,所谓“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或者如范晔在《后汉书· 党锢列传》中所说的“令行私庭,权移匹庶”。这种情形发展下去,在游侠令社会民众有所凭藉的同时,将使君主完全丧失对权力的控制,难怪站在统治者立场的班固要引曾子所说的“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呼吁“明王”重建天子权威。关于这一要求,同样站在统治者立场的董仲舒说得更加明白:“君之所以为君者,威也,故德不可共,威不可分,德共则失恩,威分则失权,失权则君贱,失威则民散。”由此看来,游侠在社会上之所以具有不容小觑的地位、影响,并非因为它具有超凡的武艺,或者仅仅具有强烈的个性、坚定的意志,而正在于它拥有一种将可与君主“共德”、“分威”的实实在在的个人权力,这种势力及强大的社会影响力一旦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发展起来,足以构成对现行政治秩序的颠覆,东汉末包括魏、吴、蜀三国开国之主在内的豪侠竞雄,便是这方面一个很好的例证。也正因为如此,历代统治者以至站在其立场上的政治家于游侠皆欲严加禁灭。
以往那种对于游侠与“私剑”错位的认识,是以“私剑”一己之武力或勇力,混淆了司马迁所说的游侠令“士穷窘而得委命”
那样一种“夹辅人”的“权力”之概念。虽然也大都强调其“结私交”方面的特征,但在这个交游圈中究竟谁是权力的主体却常常颠倒位置或含糊其辞。早在明代,据说李贽在解答何为游侠时就曾说过:“今人都不识侠。侠从人从夹,为可以夹持人也。如千万人在危急之中,得此一人即安,失此一人即危。人人可以凭藉之,方谓之侠。今人不识侠,转以击剑报仇为侠,则可笑甚矣。”这位对豪侠有着特殊情结的智者,于当时已经存在的认识游侠之误区所作的精辟分析,在今天仍然适用。游侠的权力功能,主要表现在能够令身处危困的人们投靠它有所依恃而非杀人夺命,正是凭这一点,对社会人心具有相当大的号召力与凝聚力,此其一。其二,游侠这种为人所依恃的权力的另一面,也就是获取他人服从的能力,作为权力的拥有方与施与方,它在这样一个拥有相当广泛的社会网络的交游圈中始终居主使地位。
在上述章培恒教授的论文中,他据《说文》“侠,俜也”,“俜,使也”,“使,令也”,段注“令者发号也”,而将“游侠”的原始意义解作是交游圈中发号施令的人,也可从另一个侧面证明游侠在正常权力结构外所谓“令行私庭”的权威主体地位。从这些情况来看,游侠所具有的地位和社会影响力确非“私剑”可望项背,亦唯其如此,汉代人才会将游侠比作“敌国”之重。
四、余论:从游侠到“侠客”
将游侠与“私剑”或者刺客混为一谈,并不是近世以来才有的一种认识现象,而是由来已久,若《史记集解序》索隐曰:“游侠,谓轻死重气,如荆轲、豫让之辈也。”表明唐代学者概念已不甚清晰。这种现象想来也好理解,侠与客虽然主、宾之间地位、身份并不相同,但是两者确实又具有非同一般的关系,他们彼此构成一个有共同利益、结交方式及原则大抵相似的紧密交游圈,被人们视作是同一个社会群体,因而也就很容易被认作是同一个对象。钱穆先生所说的“然既以养私剑为侠,浸而亦遂以见养者称侠,既以藏匿亡命者为侠,浸假而遂以见匿者为侠,此亦偶可有之”,应该便是基于此一层面的推想。
不过,这种误解或误读不是偶然的,一种认识对象在历史上发生变异,更应该是各个时代认识主体能动地调整其主观视野的结果。如今已有学者不约而同地注意到游侠形象在由历史记载向文学创作转移的过程中逐渐转化为武侠的事实,认为特别在以唐传奇为代表的侠文学中,随着所表现的人物由记实而转为虚构(或者说文学作者的主观色彩较之史家大大强化),作为历史原型的侠的形态发生了向剑侠转化的变异。这是非常有见地的。文学化是游侠形象发生转变的一大契机,因为在文学的塑造中最便于寄托人们的理想。侠的形象由以聚养宾客、招纳亡命为主要特征,演变为以仗剑行侠为主要特征,正显示出人们的主观视野逐渐由游侠向“私剑”转移,这当中社会大众对塑造凭一己之勇力技艺救人危难的个体英雄的心理需求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
这里想作两点补充说明。一是这种主观视野上侠的观念的调整,其实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记载中已经显出端倪,鱼豢所撰《魏略·勇侠传》便是一很好的例证。该传所载四人,所谓“远收孙、祝,而近录杨、鲍”。孙宾硕、祝公道之事义,主要犹是藏匿亡命,尚应合司马迁所说的“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然而像杨阿若、鲍出,则突出表彰其义勇孝烈,前者行节主要表现在以一己之勇力赴义讨贼,后者行节主要表现在以一己之勇力救母于危难中,正如传之标题所显示的,有关侠的观念已由传统游侠的“结私交”逐渐转化为以勇力相标榜。这样一种认识恐怕代表了那个时代对于侠之价值取向已有某种变化的社会心理。
二是自魏晋南北朝兴起的以侠为表现主题的文学创作中,出现了一种“侠客”形象,恰好具体承载了人们将关注的视点投向游侠交游圈中“私剑”的认识转移。这种“侠客”形象与传统上描绘的游侠形象有相当的差异,我们比照张衡《西京赋》与张华《博陵王宫侠曲》二首中的有关表现便可明了,如果说前者描写的“都邑游侠”所强调的特征仍在“结党连群”、“其从如云”而拥有生杀之权,那么后者所谓的“侠客”或者“雄儿”已经突出地围绕着剑器的意象在写。这里的“侠客”应该是什么身份?这是我们首先需要搞清楚的。在当今的时代,游侠又称“侠客”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然而当我们在将历史上原始形态的游侠与“私剑”作出明确区分之后,我们就有必要对“侠客”这一指称作一番推究:既然游侠非门客、食客、刺客,又何以会有“侠客”之名?
其原义究竟是否与游侠相同?“侠客”这样的词语在历史记载中出现,最早大概可追溯到《史记·游侠列传》,其中有“侠客之义”
的说法。就司马迁而言,既然将游侠与刺客分列二传,游侠与其所养之客不能是二而一的概念应该是清楚的。因此,这里的“侠客之义”,只能理解作游侠交游圈中侠及客的结交之义,“侠客”
是一表并列关系的名词性词组。此后的史籍当然也有沿袭这种用法的,但我们注意到,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侠客”作为一个名词也已正式出现,如《后汉书· 阴兴列传》谓阴兴“虽好施接宾,然门下无侠客”。阴兴为光武甚见亲信的外戚,却颇知谦退自保,从所引的上下文意来看,“侠客”当指私剑之属或者违法之亡命,因为其下句为上句的补充说明,谓阴兴所交接的宾客中排除了这一类“以武犯禁”的门客。同样,《三国志·许褚传》曰:
“诸从褚侠客,皆以为虎士。”许褚在汉末即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算得是一方豪强,此次率众归附曹操,作为许褚的从属,所谓“侠客”当然是指客,且曹操皆用为“虎士”,说明他们都是武勇之士,该传下文即曾补充说:“初,褚所将为虎士者从征伐…… 皆剑客也。”因此,在这些记载中“侠客”的词义,应该理解作“侠之客”,是一种表领属关系的偏正结构,用来专指游侠之“私剑”之属,而与“游侠”并非同一指称。我们回过头来看张华诗中的“侠客”,这是一个以幽隐自处的个体,因此不可能在侠、客并举的意义上加以理解,而只能是“侠之客”,作者表现的是他纵逸于法令之外、又因穷困之处境慷慨不已的壮士之心,若结合第二首的情形,很可能就是杀人犯禁的亡命者(这种情绪我们在鲍照的《代结客少年场》中也能看到)。至于诗中的“雄儿”,即是当时所谓的“少年”,他们通常为豪侠所聚,是游侠的基本队伍,如诗中所描述的,常常干一些击剑报仇的违法之事。严格就身份而言,“侠客”或“雄儿”仍应是游侠的“私剑”之属而非游侠本身,但诗歌的创作者在极力张扬他们的武力和敢于犯禁之勇气的同时,却将诸如“任气侠”、“侠骨香”的赞誉加诸其身(李白的《侠客行》也袭用了“纵死侠骨香”这样的赞誉),这种认识对后世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我们再来看唐传奇中表现的侠的形象。陈平原教授曾在《千古文人侠客梦》一书中提到一个颇令人困惑的问题,那就是侠客为“报恩”而行侠,他以为这基本上是唐代小说家的发明,如红线、昆仑奴是报主之恩,聂隐娘、古押衙是报知己之恩,而这与古侠的行为风貌大有距离,报恩应该是刺客荆轲、聂政的行径,与游侠无涉。这一问题的发现是值得玩味的。其实,这一刺客才有的“报恩”特征,恰好说明了这些形象与其说是游侠,不如说是上述意义上的“侠之客”,他们的身份原本就是“私剑”之属。
章培恒先生在他的文章中也曾指出,像《聂隐娘》和《红线》两篇中的主人公,“他们都介入了藩镇之争,成为替某个藩镇效力的人,也即其本身成了藩镇的‘私剑’”。有鉴于此,描写这一类侠客形象的小说与其说是“豪侠小说”(如上述传奇在《太平广记》
中大都列入“豪侠”类),倒真不如称其为“侠客小说”更为确切。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描写这一类侠客形象的小说被阑入“豪侠小说”,恰好说明了后人确已不能体察司马迁区分刺客与游侠的良苦用心,而将两者混淆了起来。
总之,自魏晋南北朝以来,随着人们在对游侠这一特异的社会人群日益关注的同时,主观视野逐渐由游侠交游圈中的游侠向“私剑”转移,曾经活跃于中国早期历史舞台的游侠形象开始出现某种变化,一些刺客的性格特征被日益附丽于游侠身上,两者的界限日趋模糊,这当中有关侠文学的表现因其特殊的功能起到了十分关键的示范树鹄作用,对后世的游侠认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此我们终于明白,现代学术中之所以会出现将游侠与“私剑”混淆的误解,在很大程度上实在也是受到了这种由来已久的社会心理及审美经验的制约。
(原载《复旦学报》200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