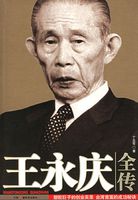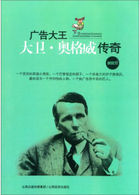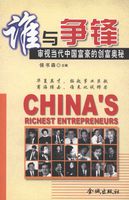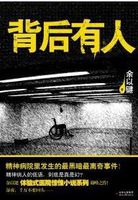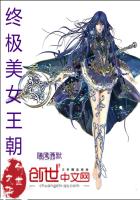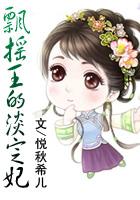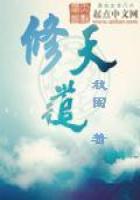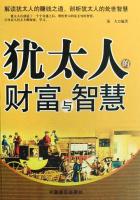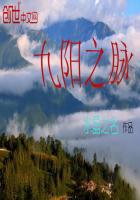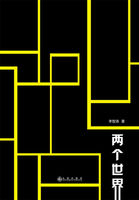学童们一见到这位有些令人敬畏的老先生,顿时霍地一声齐站起来,深深地向他鞠了一躬。由于苏若泉是一位本家,这也就算是拜师礼了。
老先生庄重地挥了挥手,示意学生们坐下,然后摆好戒尺,开始讲课。
一上来,老先生只是向蒙童们讲授《幼学琼林》、《三字经》、《千字文》、《增广昔时贤文》等,作为发蒙之始;其后,便开始讲《论语》、《孟子》、《中庸》、《大学》,以上“四书”,他要求学生必须哄堂叫读,直至滚瓜烂熟,以作为应考“童子试”的本钱。接下来,老先生开始串讲《左传》、《昭明文选》中的古文,并不时向学生提问;尤其是对那些课间好走神的学生,老先生从不客气,总是将其叫起,如果回答不上来,便要饱受戒尺抽身之苦。如果再调皮,老先生可就要打掌心了(这是旧时的正式打法)。——“打”,是这位苏老先生管教学生的主要方法;在他看来,“不打不成人,打到做官人”,对于小小蒙童来说,将来要求取功名,不挨打怎么成?
在经常被打的学生中,有维翰、维春(曼殊二叔的儿子)、煦亭(曼殊同父异母的哥哥),唯独曼殊极少挨打,因为他听讲认真,反应敏捷,甚得塾师喜爱。据曼殊的九妹苏惠珊回忆:
三兄曼殊素爱文学,书法极端整齐。所读的书,犹是如新,一圈一点,无不注重。我在幼年时也读古书,每到藏书室时,皆喜选读三兄所读过的书。如其作文、作对、诗词等,重箱叠叠藏于书室内,而其画刊卷卷笔生,藏于书柜中。……悉由长辈庶祖母及三庶母陈氏等料理。
但有一次,曼殊却差点挨了打。
一天,塾师在讲解《古文观止》中欧阳修的名篇《秋声赋》,老先生越讲越得意,禁不住拖腔拿调地吟诵起来:
噫嘻悲哉!此秋声也。胡为乎来哉?盖夫秋之为状也:其色惨淡,烟霏云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气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萧条,山川寂寥。故其为声也,凄凄切切,呼号奋发……
讲到这里,老先生不禁惊赞道:
“妙!妙!连用其色、其容、其气、其意,旨在引其声,文脉贯明,层层生发,文气便浏然而下矣!”接着,老先生又如痴如醉、摇头晃脑地吟诵道:
丰草绿缛而争茂,佳木葱茏而可悦;草拂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其所以摧败零落者,乃一气之余烈……
念着念着,老先生突然停了下来,眼睛牢牢地盯在曼殊身上,厉声问道:
“三郎,你在看什么呢?”说着,便拿着戒尺走了过来。
正在低头作画的曼殊,一见先生过来,不觉大窘,脸一下子涨得通红。
“上课不用心听讲,竟去画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说罢,便举起戒尺,要施行他的“扑作教刑”。
聪明伶俐的曼殊,急忙自我转圜地解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