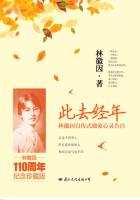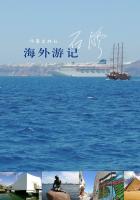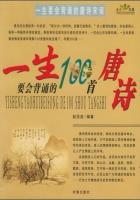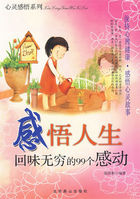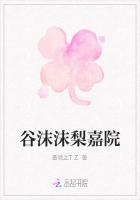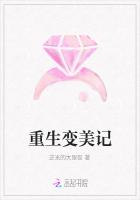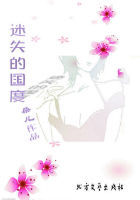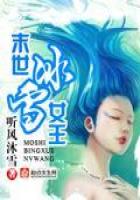再正常不过了,在等待饭局的时候,人们总要找个话题打发枯燥的时间。我偶然知道这位长者在托人买书,有《往事并不如烟》和《如焉》,分别是章诒和与胡发云的作品。巧合的是,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章诒和为胡发云《如焉》所写的序,章文的精练、细腻、韵味十足的美对我震撼颇大,我还专门下载了一份拿回家,将她的文章内容、记述方法和所用语言点评给同样爱好书籍的妻子听。
我选择了印象深刻的话题,没想到,却成了抛砖引玉。刚一提到章诒和,仿佛触动了他的兴奋点。刚刚读过《如焉》的他,略一沉思,就诵出章诒和的点评——“六朝无文,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而已;当代亦无文,唯胡发云《如焉》而已。”可惜,谈了没几句,宴席开始,觥筹交错,虚以委蛇,气氛从天空跌落尘世,“今天天气哈哈哈”。
但我的脑海里则依然萦绕着这简短的交谈。我对这位长者是敬佩的,刚进部门不久,得到他的书面表扬,简洁流畅的文字让我暗诵多次。事后多次见到他的工作计划、工作总结甚至“温馨提示”,都没有传统公文的干瘪枯燥,时不时“探头探脑”的典故、干净洗练而简洁有力的短句,让他的公文氤氲着美文气息。后来才知道,他青年时期所写的评论文章,就已登上大学教材。
日常交往也常常能感受他深厚的文学功底。有一次,他口头表扬一才气纵横、而行事微疵的同事说:“阿Q真能做。”有时他批评同事做事不讲方法,也用阿Q为例,“哪能直接说‘吴妈我要和你困觉’呢”。据说他是能将《阿Q正传》背诵下来的。还有,他用刘姥姥“金筷子夹不起圆鸡蛋”设喻,批评我们能力不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他也很熟,偶尔在酒后听到他借酒吟唱:“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毁誉交加,人之常情。因他所处的位置太惹眼,眼红他的人不能说没有;因他主持一个大部工作,取予权衡、利益杯葛,得罪人也是时有之事,所以,有时不免给人尊而不亲之感。就是我,也曾因受批评而对他有过腹诽。但这一次关于读书体会的短晤,让我深深感受到,他的心灵深处隐藏着一个“桃花源”。这种感受很温暖,就像久雨初晴的午后,有蜻蜓在满天飞舞。
饭后回单位,因他提及没有看过章诒和为胡发云《如焉》所写序的全文,我专门从网上下载了一份,送到他办公室去。没遇到人,就塞到门缝里。我外出办事时,接到他打来的电话。确认文章为我所下载后,他谈兴又起,再次聊起有关章诒和的读后感。他提起书中所记述的历史事件,脉络清晰,了如指掌,又从大背景说到章诒和的文字、思想,真是口若悬河,我都能想象他在电话那端的意兴遄飞。
过了一天,快下班了,他路过我们办公室,专程走进来,手上捏着一只未点燃的烟,再次向我推荐章诒和。他提到章诒和文字表现力时,说到了《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一文中描写马连良之死的一个细节:马连良去食堂打饭,摔倒了,先扔了拐棍,再扔了盛着面条的碗,“一个跟斗跌翻在地,似一片秋冬的黄叶,飘然坠落”。我事后买书对照,他说得完全吻合。他的记忆力真是不错,章诒和书中,如“终日借酒浇愁闷、半世悠悠困风尘……”之类的戏词,他都记得十分清楚。他笑说现在记忆力不济了,以前几乎是过目成诵的。他还说虽然现在事情多、杂、俗,但依然保持每月读两三本书的习惯。
宋人黄庭坚曾说三日不读书,便觉面目可憎,张爱玲也说过类似的话。我想,不读书虽不至于真的毁容,但读书的人是应该能修炼得“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就像这位长者,虽然他日常沉溺在繁琐的事务中,也许有些让人敬而远之,但他谈起书来的滔滔不绝,倾诉阅读体悟的不吐不快,让我所见到的,则是一个因书而富的读书人的可爱,还有老有所学的老年人的慈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