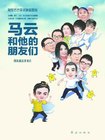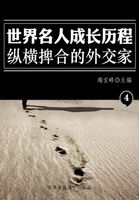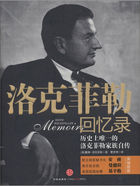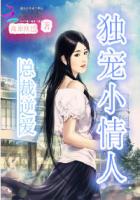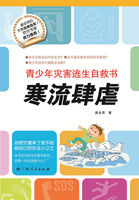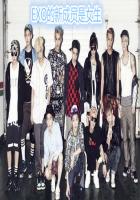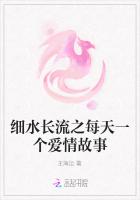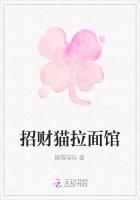1935年4月16日至7月17日这是聂耳在日本学习、考察的时期,也是聂耳一生的最后阶段。
聂耳1935年4月18日到达东京,当天就去“东亚日语补习学校”学习了两个小时日语。他住在东京市神田区神保町二町目十二番地,房东是一位从美国回来的高级裁缝,名叫原胜次,他家有栋三层楼房,聂耳租住在三楼的一个多边形的亭子间。他在日本的生活也很困难。月底经常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只能借钱度日。他的屋子里只有一个木头桌子,一把椅子,一个小行李,最珍贵的财产要算他手中的小提琴和一垛乐谱。但聂耳宁可不吃饭,也要买书,听音乐,他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学习,汲取音乐的营养。聂耳终日忙于参观学习,他听了日本新交响团、全日本新人演奏会的演出、观看了日本歌剧,《宝场少女》、《松竹少女》创作的第七回公演和日本的儿童舞蹈。站了三四个钟头去听《日本新剧活动》的讲演。观看日本的电影,参观剧场和电影摄影场。再次听了世界著名小提琴家巴里期特的演奏会。游览了东京名胜古迹。聂耳在繁忙的学习中,坚持天天练琴,除了基本功练习外,他还拉拉流行歌曲,但他拉的最多的是舒曼的《梦幻曲》和德尔德拉的《回忆》,倾诉他的恋国之情。在琴声中,他幻想着自己回到魂牵梦绕的祖国,回到他亲爱的妈妈身旁,他行前匆忙,都没有回到母亲身边道别……琴声寄托了他无限的情思,为了掩饰自己真实的身份,拉拉流行歌曲是对别人最好的迷惑。
每到星期天,他的屋里就有客人。有时多至一二十人,他们大都是东亚的学生,大家把他围在中间,听他拉提琴,弹吉他,尽享南国音乐的美妙。有一次,大家把用鲜花编织好的花环,套在他的脖子上,尽情地欢乐,聂耳是这些人的中心。
聂耳在东京住了80余天,没有假日,每天坚持4个小时雷打不动的学习(主要学习日语、音乐理论和小提琴),此外就是社会调查和参加各项活动。
他在短短的时间里,结识了一批中国左翼留日学生,像张天虚、杨士谷、杜宣、焕平、蒲风、黄风、陈学书、承箕、洪干、伊文等人,多次参加中国留日学生星期聚餐会、艺术聚餐会,中国留日诗人诗歌座谈会、中国留日戏剧同人座谈会等。6月2日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中华青年会馆内举行第五次艺术界聚餐会。聂耳在会上作了题为“最近中国音乐界的总检讨”报告受到极其热烈的欢迎。聂耳最后即席演唱了他创作的《大路歌》、《开路先锋》、《码头工人歌》、《义勇军进行曲》,每一首歌曲都赢得了听众的热烈掌声,直到散会以后,人们的耳朵里都还回响着“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的雄壮歌声。
聂耳在出国之前,曾以“黑天使”、“噪森”、“王达”等笔名,发表了一些切中时弊的短文和卓有见识的评论文章。到达日本以后,他也从未停笔,除了草拟在各种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外,还写了《日本影坛一角》、《法国影坛》、《苏联影坛》等多篇评论。他从不满足自己的学习进展和工作状况,总是在日记中检讨自己学习的不足和工作得不够。他为了更直接地了解日本剧团的演出情况,决定应邀参加新协剧团去大孤、神户、京都等地的旅行公演。正是因为这样,他才没有和绝大部分中国留学一起去房州海滨避暑度假,而是通过新协剧团照明部主任(灯光组长)李相南(朝族)的介绍,到了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沼海边洗海水浴和准备登富士山,然后赶到大阪与新协剧团的大队人马会合,参加演出。7月底返回东京,8月初去房州海滨与云南同乡欢聚。7月14日至16日,聂耳总结了他到达日本3个月后的收获。他在日记中写到:“日语会话和看书能力的确是进步了。听了很多的音乐演出,练小提琴的时间也比在国内多。”提前实现了第一个“三月计划”之后,聂耳又制订了第二个“三月计划”主要内容是“培养读日语的能力,同时加紧音乐技术的修养,要找一个老师学习小提琴,练习钢琴,学习和声。”聂耳的第三个“三月计划”是:翻译试作,作曲(唱歌、乐剧)。第四个“三月计划”是:俄文学习。整理作品,欧游准备。
但是就在这之后,聂耳到达日本仅仅3个月之际,1935年7月17日下午,与友人去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汹涌的海浪无情地吞没了聂耳的身躯,夺去了聂耳年轻的生命,聂耳不幸逝世时,仅仅只有23岁半。
7月18日聂耳的同乡和好友张天虚闻讯赶到鹄沼海滨,打开棺木验明了的确是聂耳以后,火化了聂耳的遗体,聂耳不幸逝世的消息传开,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及国内都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聂耳的同志和生前好友纷纷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怀念这位为中国的无产阶级音乐事业做出了极大贡献的音乐家。
1935年夏末,聂耳的骨灰和遗物由郑子平、张天虚护送回上海,聂耳的哥哥聂叙伦1936年专程去上海迎取聂耳的骨灰,然后寄回家乡,1937年10月1日,聂耳的骨灰安葬在风景优美的昆明西山上。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1954年在原地重建了聂耳墓,郭沫若同志为之亲笔写了碑文,日本的友好人士和团体,也在同一年(1954年),在聂耳逝世的鹄沼海滨建了聂耳纪念碑。1980年昆明市政府重修了聂耳墓,日本藤泽市聂耳纪念碑保存会于1965年也重建了被海啸冲毁的聂耳纪念碑,体现了中日两国人民对聂耳的深厚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