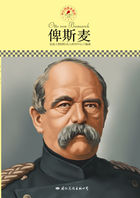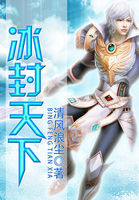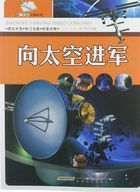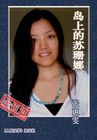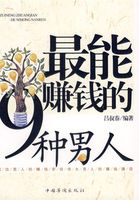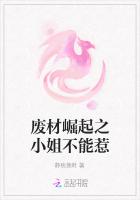1932年11月8日至1935年4月15日,这是聂耳从思想到创作都取得巨大成就的时期,也是他人生最光辉灿烂的阶段。
冬季的夜晚总是早早地来临,但今天的聂耳却更急切地盼着天黑,因为今天对他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日子。夜幕笼罩下的联华影业公司一厂,只有路灯发出昏暗的光,聂耳悄悄地来到摄影棚的一个角落,介绍人田汉、监誓人夏衍已经等在这里了。聂耳上前紧紧拉住田汉和夏衍的手:“你们早来了?”聂耳激动地说,田汉用力握了握聂耳的手:“我们开始吧!”原来由于北平剧联党组织的介绍,聂耳这个经过党长期培养的青年,在1933年初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刻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为怕反动军警的搜查,就在纸上现画了一面党旗来代替,聂耳庄严举起右手:“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永不叛党!”……从此,聂耳在党的引导和革命理想的鼓舞下,在继承中外优秀音乐遗产的基础上,聂耳在短短的两年多的时间里,用饱满的革命热情成功地创作出了数十首反映千百万被压迫者的痛苦生活,表现他们的辛勤劳动,并发出中华民族怒吼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优秀音乐作品。
聂耳1932年底回到上海后不久,就投入党领导下的电影战线,先是在联华影业公司一厂担任“场记”。拍摄影片《除夕》的时候,有两个演员需要表演一段因为生活所迫,不得不一同投江自杀的镜头。但是反复了几次他们总是酝酿不出悲愤绝望的情绪来。聂耳这时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在旁边拉起来小提琴,演奏的是他即兴创作的曲调。悲哀、忧虑的情绪很快就笼罩了整个摄影棚,在深情的乐声感染下,两个演员很快进入了角色,成功地拍完了这个镜头。这个办法后来拍摄《母性之光》等影片时,又使用了好几次,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聂耳的音乐才能也因此而更加著名,为人们所共知。
1933年夏天,聂耳为影片《母性之光》创作了一首电影插曲《开矿歌》(田汉词),这是聂耳所写的第一首电影歌曲,也是聂耳所写的第一首表现工人阶段的斗争意识的歌曲。那呆滞、缓慢的节奏,苦痛、沉吟的背景,伴随着“我们在饿肚皮,人家在餍高梁,终年看不见太阳,人家还嫌水银灯不亮”的愤慨,表现了矿工们的怨恨和不平;然而,并没有悲观,相反,倒从受压中寻求到了一条真理:“我们大家的心,要像一道板墙”,“我们造出来的幸福,我们大家来享”充满信心和希望。从此聂耳开始了正式的音乐创作。
影片《母性之光》中有一个黑矿工的群众角色,在化装时需要用颜料把全身涂黑。这样一个苦差事,当时没几个电影演员肯干。为这部影片担任场记的聂耳主动地承担了这个角色。并且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和高超的演技,成功地塑造了这个工人阶级的形象。电影演员陈燕燕等对聂耳成功的表演表示了祝贺。联华影业公司当时规定:“公司的职员除了担负自己的工作以外,还要根据需要在本公司拍摄的影片中,随时担任扮演各种群众角色的任务。”为此聂耳曾经在《城市之夜》、《小玩意》、《体育皇后》、《渔光曲》等影片中扮演过账房先生、小提琴手、卖油炸臭豆腐的小商贩、体育运动会上的医生、船夫等各种角色。
一天傍晚,当聂耳路过霞飞路(现在的淮海路)和吕班路(现在的重庆路)时,一阵阵叫卖声钻进他的耳朵:“《申报》、《时报》、《大晚夜报》,今朝的新闻真正好……卖报,卖报!”这声音多清脆,多好听。他顺着声音一看,是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在那里跑来跑去卖晚报。她穿着一件褪了色的小花布上衣,深色的布裤子,衣服上虽然有些补丁,却洗得干干净净。肩上背着一个大布袋。里面装着报纸,胸前还挂着一个装钱用的小布袋。聂耳走到小姑娘跟前,仔细端详着她。她有一双黑亮亮的大眼睛,脑后拖着两条小辫儿。甩动着报纸的小手冻得通红。叫喊“卖报”的声音真像唱歌一样好听。
聂耳同情地拉着她的手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小姑娘看了看聂耳,感到他不像个坏人,回答说:“我没有名字,大家都管我叫‘小毛头’。”原来小毛头全家由于一·二八日本飞机大轰炸,从闸北逃出来了。妈妈、姐姐和小毛头就靠卖报赚点钱过日子。每天天不亮就要到报馆门口排队等派报,晚上卖到很晚很晚才回家。不管刮风下雨,不管春夏秋冬,天天都要卖报。跑啊跑啊,喊哪叫啊,一天不卖报,就要饿肚子。
聂耳和小毛头唠了一阵子后,两人就交上了朋友。从那以后,聂耳只要见到小毛头,就要买几份报,有时光给钱不要报,有时还帮着小毛头卖报,小毛头也从心眼里喜欢聂耳,亲切地叫他“聂伯伯”。
小毛头唱歌似的卖报声,震动了聂耳的心弦。他脑中出现了一个念头:“我要写一首《卖报歌》。”
有一天,他把歌词女作家安娥领来听小毛头的叫卖声。安娥听了也很激动,就写了一首歌词《卖报歌》,歌词写出来后,聂耳很快就谱了曲。
这一天,聂耳高高兴兴地对小毛头说:“小毛头,我给你写了一首卖报歌,你一面唱一面卖报好吗?”小毛头当然很高兴:“我真想听这个歌,快点唱给我听吧!”聂耳把她叫到马路边,小声给她唱了一遍。她听了后,高兴得跳起来直拍手。聂耳说:“我来教你唱,耽误了卖的那些报纸,我都买下了。”说完,聂耳就一句一句教她唱《卖报歌》。小毛头很快就学会了。不过她歪着头看着聂耳,好像有什么话要说。聂耳问她:“小毛头,有啥话就说吧。”小毛头说:“聂伯伯,要是能把‘几个铜板能买几份报’的话也写上去,我卖报时就能唱这个歌了。”聂耳说:“小毛头,真有你的,伯伯一定给你改一改。”聂耳和安娥一商量,就按照小毛头的意思,把歌中的一句歌词改成“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从那以后,霞飞路一带,经常能听到小毛头清脆的歌声:
啦啦啦!啦啦啦!
我是卖报的小行家,
不等天明去等派报,
一面走,一面叫,
今天的新闻真正好,
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
1934年,聂耳作曲的戏剧《扬子江暴风雨》在上海演出时,聂耳请小毛头扮演剧中的报童,由她来唱《卖报歌》。她唱得那样动听,观众一阵阵为她鼓掌。《卖报歌》就是这样唱开的。
聂耳要到国外学习去,临走前对小毛头说:“我还要给你写第二首卖报歌,等我回来教你唱。”小毛头眼圈红了,难舍难离地说:“聂伯伯,我等你回来。”
1933年这一年,聂耳的工作是相当繁忙的,除了一部接一部地拍摄影片,担任各种角色之外,他还兼任了繁多的社会工作职务。2月9日中国电影文化协会成立,聂耳被选为常委并兼任组织部秘书。与张曙、任光、安娥等人参加“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1934年转为剧联音乐小组),发起组织“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集合一些革命音乐家共同商讨研究革命音乐的创作问题。
3月16日随剧联去大场演出话剧。3月21日任联华公司一厂的音乐股主任,除了要给影片配置音乐以外,还要辅导电影演员们练习唱歌。聂耳又是联华一厂俱乐部的执行委员兼秘书,具体负责出版墙报、组织体育比赛、举办春节联欢会等各种事务性工作。每天都要开各种各样的会:有一次曾经从早晨接连开到深夜1时。除此以外,聂耳自己还要抓紧时间练琴、作曲、看书、教唱歌、写信、记日记……
聂耳还是剧本讨论会起草委员会的成员,曾经写过一个表现学生斗争运动的电影剧本《时代青年》,8月中旬公司的剧本审查会要聂耳交出一个剧本来进行讨论,聂耳于是接连开了好几个夜车,在8月26日赶写出了一个名叫《前夜》的电影故事。当时影片《人生》正在紧张的拍摄之中,聂耳仍然担任着场记的工作,聂耳的身体虽然向来十分强壮,但是由于过度劳累,8月30日《人生》在南京路永安公司门口拍摄外景时,终于当场晕倒,送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诊断为脑充血,因此留在医院里治疗、休息了7天。(聂耳在明月歌剧社时,有次玩单杠,头朝下从单杠上摔了下来,当时就晕了过去,从此以后聂耳就留下了一个时常脑袋痛、犯晕的病根)因为聂耳这次是在工作时病倒的,所以医药费、住院费全由联华公司负担,但是医生叮嘱出院以后,至少需要休养60天的事,公司就不管了,当时休病假是没有工资的,聂耳只休息了12天,生活就发生了危机。9月18日勉强去上班,第二天被派到浙江石浦去,拍摄影片《渔光曲》的外景。为了赶工作,中秋节还在海里拍镜头,聂耳着了凉发烧40多度。“双十节”那天被送回上海,看病、吃药花了四五十元钱,全是向朋友东拿西借的,房租、饭费也欠了快两个月,等到病刚好了一些,11月1日聂耳就又带病上班了。
1933年,左翼电影工作在以夏衍同志为首的党的电影小组的领导下,有了很大的发展,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文化围剿”,恼羞成怒的国民党反动派,在向江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反共“围剿”的同时,终于撕下了所谓“文明”的遮羞布,1933年11月12日派遣“兰衣社”的匪徒,用法西斯的残暴手段,砸毁了曾经拍摄进步影片的艺华影业公司,同时在报纸上发布通告,到处张贴,散发传单,禁止各影片公司及电影院拍摄和上演“赤化”电影,否则严惩不贷。
聂耳由于积极参加各种革命工作,在资本家的心目中早就被认为是“左”倾分子,再加上聂耳经常率领联华同人会(即工会)与资本家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趁着这次“艺华公司事件”,1934年1月24日,联华公司借口请聂耳休养身体将他解雇了,联华同人会对此事曾经大加讨论,向资本家表示抗议。
此后聂耳准备应友人的邀请,去南昌的“怒潮”管弦乐队工作。党组织知道以后,及时告诉他这个乐队是蒋介石为指挥第五次反共“围剿”而设立的南昌行营政训处所属的机构,于是聂耳马上就改变了原来的打算。这就是聂耳在日记中所写的“××约我到南昌‘怒潮’去已经答应了又打了回票,原因是不应当去”的实质。
聂耳在日记里早就写到要好好准备,再去报考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但报考的结果,只是在1934年2月24日的日记上写着“音专失败”4个字。据我们了解,1934年初聂耳是报考了上海国立音专的小提琴专业。主考人是上海工部局乐队的首席小提琴、国立音专的兼职小提琴教授法利国,聂耳的演奏本来已到了录取的标准,但是校方因为听说聂耳曾经在明月歌剧社待过,认为录取了聂耳有损于国立音专这个全国最高音乐学府的声誉,于是又以聂耳的演奏水平低为借口,不予录取。
1934年春天,聂耳与张曙、任光、吕骥、安娥等人成立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小组,1934年4月1日,聂耳根据党组织安排进入英国人经营的“百代唱片公司”工作。尽管国民党当时对报刊、电影进行着严格的审查,也许是出于惧怕的缘故,国民党当时对百代唱片公司的活动,却很少进行干涉。英国老板则是只要赚钱就行,别的事情很少管。聂耳利用这些机会和方便条件,与原先已经进入百代唱片公司工作的革命音乐家任光、安娥一道,以出版赚钱的电影歌曲、流行歌曲为名,组织发行了大量的革命歌曲。仅聂耳的作品,就有20余首灌制了唱片。聂耳在百代公司工作期间,曾经组织过一个“百代国乐队”(又名“森森国乐队”),除为歌曲担任伴奏以外,还灌制过《金蛇狂舞》、《翠湖春晓》等7首民族器乐合奏曲,对发展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1934年的6月30日至7月1日,左翼剧联通过一所教会学校——麦伦中学里的进步师生,以庆祝该校校庆游艺会为名,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礼堂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戏剧演出。其中有一个节目,就是田汉编剧,聂耳作曲的歌剧《扬子江暴风雨》。聂耳亲自扮了剧中的主角——打砖工人老王。聂耳的高超表演技巧,获得了当时报纸舆论界的一致好评。聂耳一共为这部歌剧创作了4首歌曲,就是《码头工人歌》、《打砖歌》、《打桩歌》、《苦力歌》(后人将其改为《前进歌》)。
聂耳刚到上海时所住的“云丰申庄”,就位于黄浦江码头的旁边。聂耳从早到晚能听到码头工人们在搬运沉重的麻袋、钢条、铁板、木头箱时,所唱的雄壮的劳动号子。1932年初夏,聂耳随着明月歌剧社去武汉旅行公演。5月11日夜半轮船抵达九江,聂耳倾听着长江边劳动号子的呼声,深有感触地在日记中写到:“一个群众吼声震荡着我的心灵,它是苦力们的呻吟、怒吼!我预备以此动机作一曲。”1934年为谱写《码头工人歌》,聂耳又几次去黄浦江码头眼见着码头工人们一边喊着“唉伊哟嗬”的搬运号子,一边汗珠直滚地背着大麻袋、木头箱卸货的情景,聂耳把这些切身的感受,和他从实地采集来的工人们的血汗呼声,都创造性地谱写到了《码头工人歌》里,在《码头工人歌》中,聂耳成功地运用深沉的节奏,刚毅的曲调,表现了旧社会码头工人惨重的劳动生活和刚强的斗争精神。歌声中蕴涵着愤怒和反抗压抑的心情,同时又充满乐观、坚定,对前途充满信心,对工人阶级的力量充满信心。
1934年党直接领导下的“电通影片公司”成立了(老板之一是当时党的电影小组成员司徒慧敏同志)。电通公司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桃李劫》,聂耳著名的《毕业歌》就是为这部影片所作的主题歌。
有针对性才有战斗性,聂耳针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高唱着:“我们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具有号角式的旋律,表现出人民强烈的斗争精神。
1934年的秋天,聂耳担任了为影片《林路》配乐的工作,著名的《大路歌》和《开路先锋歌》,就是这部影片中的两首歌曲。《开路先锋》是影片《大路》的序歌,聂耳在创作这首歌曲时,为了要抓住进行曲的节奏,曾经有好几次晚上,踏着步子在房间里的地板上大步地走来走去。嘴里大声唱着歌曲的旋律,而且不断地练习歌曲中所需要的笑声,吵得住在楼下的房东几天睡不了觉,大发脾气,要撵聂耳搬家。
在《开路先锋》中,聂耳塑造了肩负扭转乾坤的筑路工人形象。豪放、雄浑、乐观的曲调,是那么震撼人心!聂耳把工人阶级写成了顶天立地的巨人,他们“要引发地下埋藏的炸药”,炸倒阻碍中国前进的“山峰”;他们坚信山河必将“岭塌山崩,天翻地动”,他们坚毅、自豪地宣称:“我们是开路先锋!”
聂耳在《大路歌》中塑造的是无坚不摧、无往不胜的工人阶级形象:“大家努力!一齐向前!大家努力!一齐作战!”……刚劲、浑厚、沉稳的节奏,表现出坚实、刚毅的气质,犹如要爆发的火山即将从地下喷射出能量巨大的岩浆。聂耳在创作中倾注了自己无限的情感,塑造出栩栩如生、充满生命力的音乐形象,不仅和影片融为一体,还成为当时鼓舞人民群众斗争的有力武器。
据词作者孙师毅同志介绍,《开路先锋》歌的开头及结尾的三个“轰”,是暗示要轰倒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的意思,笑声则是表现了革命人民的乐观主义和必胜的信心。在创作影片《大路》的主题歌《大路歌》之前,聂耳曾经与词作者孙瑜一起研究了如何用音乐来表现歌词。孙瑜希望这首歌能写得跟苏联的《伏尔加船夫曲》那样深沉、有力。聂耳认为在表现筑路工人们艰苦沉重的步伐同时,更应该强调青年们肩负重担,为争取自由解放而团结作战的那一种青春蓬勃的节奏和胜利乐观的信心。
聂耳写完了《大路歌》之后,一天,他兴致勃勃的来到影片《大路》的导演孙瑜的家里,不等打开包取出乐谱,聂耳就做出了工人拉着大铁滚压路的姿势,嘴里哼唱起《大路歌》来,雄壮豪放的曲调和动人的演唱,马上就深深地抓住了当时在场的每一个人,根据他拉铁滚压路的熟练动作和脸上新近增添的褐色油光,大家马上就知道了这首浑厚有力、激动人们心弦、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歌曲,是如何在劳动实践当中产生的了。聂耳为了写好影片中的插曲,曾随着摄制组到无锡鼋头渚后山的一个筑路队参加过劳动,记录过拉滚号子。《大路歌》中间部分的曲调原来显得较平直。当时在场的将要在影片中演唱这首歌曲的金焰提出意见,认为中间这一段曲调应该再升高一些。情绪才显得更加昂扬,与前后也能够有所对比,聂耳听了金焰的意见后觉得很好,马上就很虚心地在乐谱上进行修改,《大路歌》才成为现在这样完美的歌曲。
1934年底,百代公司的老板看到黄色音乐很能赚钱,打算要百代国乐队为黄色歌曲伴奏,聂耳认为不能再干下去了,11月底向百代公司提出辞职,1935年初进入联华二厂担任音乐部主任,同时为影片《新女性》作曲。聂耳创作的《新女性》组歌,是一部用革命思想表现女工的劳动与斗争生活的作品。聂耳在《新女性》中塑造了20世纪30年代初具有朦胧革命意识的中国女性的形象,“谁能做万代的仆从?谁能说地狱是天宫?谁能把欺骗当恩宠?谁能坐一世的牢笼?”聂耳要“翻卷起时代的暴风!”“唤醒民族的迷梦。”铿锵有力,愤懑激昂的歌声,正是表达了奋进的,在理想、有斗争目标的、意识到自己担负着阶级和民族重任的新时代的妇女形象。
为了演唱好这首充满新气质的组歌,聂耳曾经专门登报招考、组织了一个“联华声乐团”。经过聂耳精心的辅导和排练,1935年春节,影片《新女性》首次上映之前,聂耳指挥身穿一色工作服装的“联华声乐团”(其中还有沪东公司的好些女工)演唱的《新女性》组歌,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5年1月31日至2月2日上海左翼剧联以上海舞台协会的名义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公演。演出的剧目是田汉编剧的独幕话剧《水银灯下》和三幕话剧《回春之曲》。后者表演了南洋的爱国华侨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回国参军抗战的动人故事。聂耳在很短的时间里,为这个话剧创作了《告别南洋》、《春回来了》、《慰劳歌》、《梅娘曲》这4首插曲,《慰劳歌》是一首说白与歌唱相间的、有号召力的叙事歌曲,其余3首则都是优美感人的抒情歌曲。这几首歌表现的内容虽然与《新女性》不同,塑造的是不同的女性,表现了不同类型妇女的思想和感情,但是,她们却都具有反对压迫、剥削,反对外族侵略和勇于斗争的革命品质和革命心愿。“谁甘心做人的奴隶?谁愿意让乡土沦丧?”这是聂耳塑造的、富于责任感的、新式女性的特点。深情的歌声表达了她们有血有肉、有感情、有思想的中国妇女的典型形象。
创作这几首歌的时间紧,在演出前,聂耳还在教演员们唱歌。演出时,聂耳又在幕后弹着六弦琴为演唱者伴奏,总是那样没有一点空隙地忙碌着。
1935年3月,聂耳听说电通影片公司正在拍摄《风云儿女》。这部影片的故事内容主要是号召文艺青年起来抗战,他早就熟悉,而且很感兴趣。所以当他一听说影片中有一个主题歌需要作曲时,就赶紧跑去找夏衍。夏衍把电影剧本拿给他看。聂耳一把抢过剧本来,就找那首主题歌。原来那首主题歌写在剧本的最后一页。他看了两遍,很快地说:“作曲交给我,我干!”还没有等夏衍答话,他抓住夏衍的手又说:“我干!交给我吧!”说完转身就走了。
聂耳出门后,一溜小跑去找影片的导演许幸之。他对导演说:“把作曲任务交给我吧!”这位导演好像不认识他似的,瞪着两只眼睛一个劲儿地看他,把他浑身上下仔细打量了一番。
你们知道导演为什么一个劲儿地看聂耳吗?原来这位导演正在为影片挑选演员呢。导演感到聂耳这个青年浑身上下那股火热劲儿好像一团烈火,走到哪里就燃烧到哪里。聂耳的性格十分开朗,走到哪里,哪里就响起一阵阵欢笑和歌声。这正是他要寻找的最理想的演员啊!
聂耳有些奇怪,看了看自己身上,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导演注意的地方呀!这时导演发话了:“聂耳,除了作曲之外,还有一个任务要交给你,你干不干?”“什么任务?你说吧。”导演说:“这部影片的主人公有一个好朋友,是个富有革命理想的热血青年,至今我还没找到合适的演员,我一眼就看中了你。这个角色由你来扮演最合适。怎么样?”聂耳回答得挺干脆:“行,你看中了我就干。不过我得先把这个主题歌写出来。”
聂耳回去后,为了早点儿谱写这首主题歌,他夜以继日地工作着,几乎废寝忘食。他一会在桌子上敲打拍子,一会儿弹弹钢琴,一会儿在楼板上不停地走来走去,一会又高声地唱起来。这下可把房东老太婆气坏了,大骂了聂耳一顿,说他发疯了,聂耳向她道歉才算了事。
这天大清早,导演还在睡梦中,忽然有人敲门。开门一看,原来是聂耳。他一进门就兴高采烈地说:“好啦,老兄!《义勇军进行曲》谱好啦!”导演也很高兴,连忙说:“谱好了?快唱给我听听!”聂耳一手拿着歌谱,一手敲打着导演的书桌,一口气唱了好几遍。唱得导演眼睛里直闪亮光。
聂耳突然停下来,问导演:“有什么意见,老兄?”导演想了想说:“开头一句显得低沉了些,结尾一句应当再坚强有力些。”聂耳看了看歌谱说:“好,我一定把它修改好!”
聂耳在一生中,深受三座大山的迫害,少年时代,他眼见着帝国主义疯狂掠夺祖国的宝藏,反动势力残酷迫害,逼得他离开亲人远走他乡。在上海,到处是外国洋行,黄浦江里停满了外国的军舰,妄图独霸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了东三省之后,又在不断侵占我国的领土,在这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蒋介石仍然高喊着“攘外必先安内”。一次又一次地向人民发动军事上及文化上的围剿,无数的革命先辈和战友倒在了血泊里……聂耳在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时,他亲身经历、耳闻目睹的这些往事,又一桩桩一幅幅历历涌现在他的脑海里。使得他心情激昂,热血沸腾,按捺不住的满腔义愤,终于像火山似的爆发出来。经过将近两个月的酝酿、思考,又经过了两个星期的紧张创作和修改之后,聂耳终于成功地把他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满腔仇恨,全都完美地凝聚在这首杰出的革命战歌之中。1935年2月以后,田汉、阳翰竹、赵铭奕等革命文艺工作的领导者在敌人的血腥镇压下相继被捕。随着白色恐怖的加剧,上海的革命形势越来越紧张。4月1日,传来国民党反动派要逮捕聂耳的消息。党组织为了保护聂耳这个英勇奋发、年轻有为的战士,同时也考虑到聂耳渴望得到进一步深造的要求,批准他出国去日本,然后再去欧洲、苏联学习考察,暂时出去躲避一个时期。
聂耳到了日本后,才把修改好的歌谱寄回来。可是寄回来的歌谱,只有曲调,没有伴奏。当时贺绿汀正在忙着帮助影片《风云儿女》搞音乐,为了能及时录音,他请人为《义勇军进行曲》配上了乐队伴奏。可是伴奏谱写得太潦草,贺绿汀只好亲自动手修改。
当时在百代唱片公司工作的任光,抢先把《义勇军进行曲》灌制成了唱片。所以还没等影片《风云儿女》放映,唱片就先出来了。等到这部影片在上海刚一上演,《义勇军进行曲》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飞快传遍了全国。这歌声唱出了亿万人民的心愿。这歌声犹如万马奔腾,势不可挡!全国人民,不论男女老少,都在《义勇军进行曲》歌声的鼓舞下,奋起抗战。
《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曲,不仅得到中国人民的承认,而且也得到全世界人民的承认。当时印度广播电台对中国广播时,把《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广播开始的前奏曲。美国黑人歌手罗伯逊把这首歌曲叫做《起来!》,在美国到处演唱,深受美国人民的欢迎。1944年,美国国务院提出了一个在联合国胜利之日演奏各国音乐的曲目建议,其中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被选定为代表中国的音乐。
1949年10月1日,当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时候,天安门广场立刻响起了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这是中国人民对聂耳历史功绩的极高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