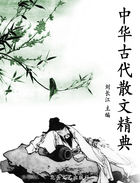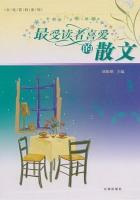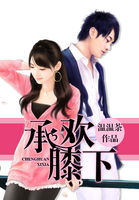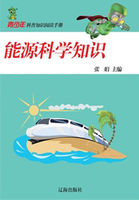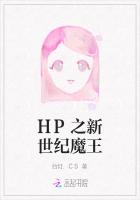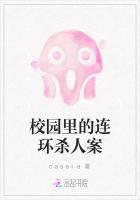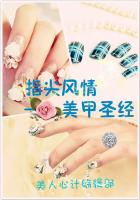风中,有一只白瓷缸儿。
瓷缸儿很破旧。掉瓷处,露出铁皮,铁皮经风历雨,便形成一块块锈痕,如同它被岁月消磨得已年迈力衰的主人。
每次经过那个路口,我都要向里面投掷两枚硬币。
守候着它的老妇人听见响声,便将头埋下,以额触地,发出“咚咚”两声。那一头已然花白的头发便在风中飘动,像一片悲怆的云、一首凄凉的诗……
我知道,她或许并不十分窘迫,或许并非生计皆无,或许就是以此为职业,像一座尚未停摆的钟表,每天依照惯性来到这个路口,如同我被生活驱使,每天要到编辑部上班一样。
然而,我终不能漠视那头白发。
那头白发,使我想起幼时的风车、鞭炮、荷包蛋和糖葫芦;想起母亲的搓衣板、旧饭盒、粗糙的双手和一脸的皱纹。我知道,我咀嚼的每一分甘甜,都有母亲的心血付出,就是在这样不断的付出中,母亲的一头青丝渐渐被岁月的飞雪染白……
那么,这位老妇人呢?风烛残年了,为什么还要出卖一个人最宝贵的东西—尊严?
我无法去破译这颗封闭的心灵。
那天,天格外冷。北风呼啸着,天公挥舞起无数条长鞭,肆意抽打着世间的万物。因要乘坐的109路电车未进站,我便竖起大衣的衣领,站在离老人不远的地方,想看一看有多少人肯“关照”那只破旧的白瓷缸儿。
牵着巴儿狗的妇人过去了,
衣着时髦的小姐过去了,
衣装笔挺的先生过去了。
每次一位路人昂然走过,我的心便一阵颤栗—一个健全的社会当然不能鼓励懒惰,但它同样不应该摒弃同情。面对着这样一位满头白发、年迈力衰的老者,人性中的善良与怜悯难道都被冷冻了吗?
终于,从蓝岛大厦出来的一对年轻人向老人走过去了。
老人把头低垂着,不知她是因为疲惫而无力抬起,还是因为木然而不肯抬头看一看这寒冷的世界?我想,那张脸如果扬起,该是什么模样?是布满了沧桑,还是写满了羞愧?是挂着泪珠,还是溢出冷漠?无论如何,那该是一张满是皱纹的脸。每一道皱纹,都是用血汗写成的一页人生履历。
男青年向白瓷缸儿里扔了两枚硬币,走出几步,又突然转回身,走近老人想俯身去看一看她的脸。女青年似乎嫌男青年啰嗦,一把拽住他的胳膊,跑向刚刚进站停稳的109路电车。
跟在他们后面的我听见了女青年的河南话。
“干啥哩!晚上的火车就回去了,咱还得到西单商场转转呢!”
男青年无语。
女青年继续唠叨:“北京这么些人,就你心肠好!你要心肠好,把她接回家,当妈养起来!”
男青年依旧无语。只是动作机械地跟着女青年走,仿佛是一具玩偶。
在电车上,女青年仍然喋喋不休,她抱怨北京的物价太贵,一副床罩竟花去五百多,一餐饭也要吃去好几十;她感叹北京的变化太快,说一上三环路,那感觉简直就如同到了国外;她盘算着新房中还缺什么,牡丹电视是必不可少的,不能再低于这个档次;电风扇很快就要被淘汰了,能不能安一台国产空调机,窗式的,也不过两三千元。当然,还有一些杂七碎八儿的东西要在北京买齐;秋天穿的毛衣,夏天穿的皮鞋,春天穿的套裙,冬天穿的大衣……
男青年还是无语,只是愣愣地望着窗外。
窗外,是林立的高楼,奔涌的车流,令人眼花缭乱的店铺匾额,还有神情各异的行人。
女青年火了,吼一声:“你是想啥哩,木头人啊!”
男青年双眼发直,突然一声长叹:“她说,她是在北京当保姆啊!我说哩,她怎不把在北京的地址告诉我!”
言毕,双手捂面,两行泪水顺着指缝簌簌滚落。
我的心头倏地一沉,眼前又浮现出风中的那只白瓷缸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