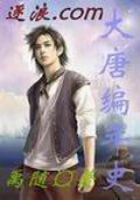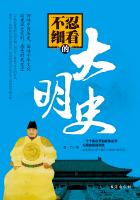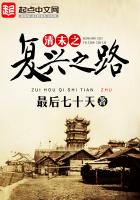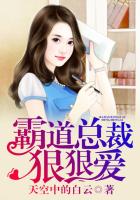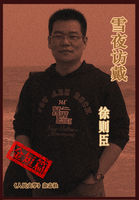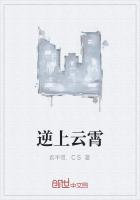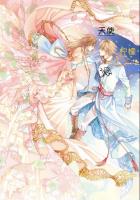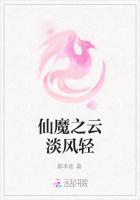白马与黄河
沙坡头南区山岗上古代曾建造有一座白马庙,修建年代史志无载。早年访之当地耆老,俗称“白马将军庙”。白马将军庙古已塌毁,现仅存遗址。当年我寻访时曾在其遗址上捡拾过一些红陶片及秦汉残余瓦片。
黄河宁夏段源于“白马”为名的地名,清代以前四见:一是中卫沙坡头白马庙,二是中卫北长滩白马浪,三是中宁白马寺,四是吴忠古薄骨律镇。以上四个“白马”地名,均出现在沙坡头区至青铜峡的黄河岸边或黄河滩渚上。
四个“白马”地名来源各有其说。
中卫沙坡头白马庙的建造,源于美利渠开挖的传说。古代美利渠口开在河边,渠道傍河而行,挖开渠道后河水不入渠。大家在万般无奈下,只好祭奠河神,请求保佑。一天,突然一匹白马从河边冒了出来,拖着缰绳,从马房滩上向东跑去。人们顺着白马缰绳拉下的印子重新开渠,美利渠终于开挖成功了,河水浩浩荡荡地流进了灌区。大家为了祭奠这匹白马,就在渠口开挖处建造了这座白马将军庙。
中卫北长滩白马浪是该村上滩黄河中的一处地名。黄河流经此地时,波涛汹涌,白浪翻滚,涛声呼啸,过往船筏惊恐,古称此地河水为白马浪,此名延续至今。
中宁白马寺的建造,源于黄河边渠道的开挖。神仙指引白马拉缰,人们顺着白马缰绳拉下的印子开渠,终将渠道开挖成功,将黄河水引入了灌区,据说这就是七星渠的来源。人们为了祭奠这匹拉缰指引开渠的白马,就在白马滩建造了白马寺。
吴忠古薄骨律镇的得名,传说源自“白口骝(白马)”的发音转韵。《水经注校·卷三》载: “河水又北,薄骨律镇城。城在河渚上。赫连果城也,桑果余林,仍列洲上。但语出戎方,不究城名。访诸耆旧,咸言故老宿彦言,赫连之世,有骏马死此,取马色以为邑号,故目城为白口骝韵之谬(韵字下当有转字,谓白口骝,转读作薄骨律耳),遂仍今称。所未详也。”这是说, 薄骨律镇城的得名,是在南北朝赫连之世,有一匹白色骏马死于黄河滩渚上。“白马”匈奴人发音为“薄骨律”,于是吴忠的这座古城便叫做薄骨律镇了。
白马与鲧
四个 “白马”地名来源的说法,时代早晚不同,但都与黄河有关。追索“白马”与黄河的关系,“白马”治水要比大禹治水早。
“白马”是大禹的父亲。《史记·夏本纪》载:“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墨子·尚贤》说:“昔者伯鲧,帝之元子,废帝之德庸,既乃刑之于羽山之郊。”《汉书·律历志·帝系》载:“颛顼五代而生鲧”。皇甫谧和《世本》都说鲧是颛顼之子。《山海经·海内经》载:“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从早期史料记载看,“白马”最早应是鲧族群的图腾,是鲧的代称。所以,大禹的父亲就叫做“鲧”,“鲧”的别名也叫做“白马”,“白马”就是大禹的父亲。
鲧是五帝时代继共工后被公众推选出来治水的贤能人物,他治水有功。《史记·夏本纪》载:“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尧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岳皆曰鲧可。尧曰:‘鲧为人负命毁族,不可。’四岳曰:‘等之未有贤于鲧者,愿帝试之。’于是尧听四岳,用鲧治水。”远古洪水泛滥,尧寻求治水人才。当时群臣四岳都推荐鲧,说鲧是治水的贤能人才,论治水,现在还没有比鲧更优秀的人才。这说明鲧有治水经验,才副众望,群臣四岳都推荐他。尧让鲧治水,想试一试鲧的才干。鲧担当治水大任后,为拯救万民于洪水,不顾自身安危,没等批准竟动用了帝之“息壤”以之堵塞洪水。《山海经·海内经》载:“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郭璞说:“息壤者言土自長息無限,故可以塞洪水也。開筮曰:‘滔滔洪水,無所止極,伯鯀乃以息石息壤,以填洪水。’”
郭璞说的 “自長息無限”的“息壤”,历代注释都说不清。“息壤”,实际上就是西北地区的胶泥土。这种胶泥土,其特性是不渗水。胶泥土是黄土高原沉积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带有胶性的粘土,流水通过沉积胶泥土的特定地域时,将这种胶泥土挟带至低洼地区,流水滞凝,胶泥土沉积。随着挟带胶泥土的积水不断增高,胶泥土的沉积也不断增高,这就是所谓“土自長息無限”的来历。胶泥土是烧制陶器,造水窖、筑堤坝的宝贵粘土,属稀缺资源,不是到处都有。《史记·五帝本纪》载:“舜,冀州之人也。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 舜是在黄河边烧制陶器,贩卖陶器发家致富的。鯀擅自挖掘的胶泥土(息壤)是舜家族的?还是尧帝家族的?史籍记载不清。《山海经·海内经》只说是鯀擅自挖掘“息壤”,“不待帝命”。历史大多是追记的,这个“不待帝命”的“帝”,不是尧,就是舜,别无他人。舜是尧帝的女婿,又继承了帝位。从舜烧制陶器,贩卖陶器发家致富来看,鯀擅自挖掘的胶泥土(息壤)应是舜帝家族的。鯀堵塞洪水急用胶泥土,他没征得“帝”同意,就擅自挖掘了舜家的胶泥土,惹下了大祸,所以史载“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舜上台后就杀了鲧,与“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不无关系。
鯀冤如海
鲧是被尧舜冤杀的治水英雄。《史记·夏本纪》载:鲧“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于是帝尧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摄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于是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官方正史说鲧治水九年,舜上台后先为“三公”,代尧巡视,认为鲧“治水无状” “功用不成”,乃杀鲧于羽山,还声称天下人都说舜杀鲧正确。
捡索史料,尧舜杀鯀罪证无据。《史记·夏本纪》《韩非子·外储说》《吕氏春秋·达鬱》等先秦史料披露,尧舜杀鯀的罪名共有三条:
第一条,舜说鲧“治水无状”而杀之。所谓“治水无状”,是说鲧治河采用了堵塞办法。舜杀鯀前,共工就用“壅防百川”的办法堵塞治河。《竹书纪年》载:帝尧十九年命共工治河;六十一年命崇伯鲧治河;六十九年黜崇伯鲧;帝舜七十五年司空禹治河。《国语·周语》说:昔共工……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有崇伯鲧……称遂共工之过……其后伯禹念之非度,厘改制量……疏川导滞。《国语·鲁语》说:“鲧障洪水而殛死(即鲧堵塞洪水被处死)”,即说鲧重复犯了共工的错误(称遂共工之过)。舜杀鯀后,大禹也使用过堵塞办法治河。《山海经·大荒北经》载:禹湮洪水,杀相繇,……禹湮之,三仞三沮,乃以为池,群帝因是以为台。《淮南子·地形训》载:禹乃以息土填洪水。《庄子·天下篇》载:昔者禹之湮洪水。《汉书·沟洫志》引《夏书》说:“禹湮洪水十三年。” 堙,本字作“垔”,《说文解字》说:“垔,塞也”,即堵塞。“禹湮洪水十三年”,说明大禹治水也用过堵塞的办法。堵塞治河的办法,舜杀鯀时前后治水人物都在沿用。堵塞治河的办法共工使用在前,鲧用了九年,大禹用了十三年。同样的堵塞治河办法,鲧用,舜就砍了鯀的头;禹用,舜同意禹继承帝位。所以,使用堵塞治河的办法实在成不了舜杀鯀的理由。
第二条,舜怕鯀“欲以为乱”杀之。《吕氏春秋·达鬱》载:“人主之行与布衣异,势不便,时不利,事仇以求存,执民之命。执民之命,重任也,不得以快志为故。故布衣行此指于国,不容乡曲。尧以天下让舜。鮌为诸侯,怒于尧曰:‘得天之道者为帝,得帝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以尧为失论,欲得三公,怒甚猛兽,欲以为乱,比兽之角能以为城,举其尾能以为旌,召之不来,仿佯于野以患帝。” 从《吕氏春秋·达鬱》透露的真相看,鯀认为尧选拔舜为“三公”有失公平(尧为失论),舜就说鯀“欲得三公,怒甚猛兽,欲以为乱”。如果鯀真想“欲得三公”而为乱的话,鯀势力强大,他“比兽之角能以为城,举其尾能以为旌”,干戈未必不起,尧舜未必能安坐天下。但战火未起,说明“欲以为乱”只是尧舜理亏心虚的猜测,查无实据,只是个“莫须有”的罪名。
第三条,舜说鯀“仿佯于野以患帝”杀之。据《吕氏春秋·达鬱》,舜说鯀 “患帝”的证据是舜召鯀,而鯀却“召之不来” “仿佯于野”。这是鯀认为尧选“三公”不公道(尧为失论),“召之不来”“仿佯于野”,他充其量是闹情绪,耍脾气,消极怠工而已。鯀身为诸侯,缺雅量,有错,但此错不至于犯下杀头之罪。以上三条理由,都不是舜杀鯀的真正原因。
史料记载,尧舜杀鯀的真正原因是鯀不同意舜继承帝位。尧想把帝位传给自己的女婿舜,鲧认为舜是个“匹夫”,说舜继承帝位不吉祥。《五帝本纪》载:尧曰:“嗟!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践朕位?”……众皆言于尧曰:“有矜在民闲,曰虞舜。”……尧曰:“吾其试哉。”于是尧妻之二女,观其德于二女。《尚书大传》载:舜贩于顿丘,就时负夏。《五帝本纪》载: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载: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而诛杀鲧于羽山之郊。共工又谏曰:“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又举兵而诛共工于幽州之都。于是天下莫敢言无传天下于舜。《吕氏春秋·达鬱》载:“尧以天下让舜。鮌为诸侯,怒于尧曰:‘得天之道者为帝,得帝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以尧为失论”。从以上记载披露的尧舜杀鲧的真相看, 鲧治水九年,尧已老了。舜是经营商业起家的,尧挑选帝位继承人时,选中了舜,并把两个女儿嫁给了他。 鯀为一方诸侯,很愤怒地对尧说:我现在治水已“得地之道”,就是说我已掌握了治水的规律,你应该让我当“三公”。鯀认为尧在挑选帝位继承人时不讲道理,用人不公,闹情绪,所以尧“召之不来”。舜上台为“三公”,代行“天子之政令”,利用职权,在巡狩中以鲧“治水无状”为理由,杀鯀于羽山,以报鯀不同意他继承帝位之仇。
不平则鸣
尧舜杀鯀冤案,世间一直为之鸣不平。《史记·夏本纪》载:“舜登用,摄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于是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舜杀了鲧,却让鲧子禹 “续鲧之业”,继续从事治水重任。舜逝世时,又同意禹继承了帝位:“帝舜荐禹于天,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丧毕,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史记·夏本纪》)。” 舜杀鲧,又让鲧子禹担当司空大任,直至荐禹继承帝位,历史的谜底到底是什么?
五帝时代属氏族部落社会,血族复仇是部落成员的神圣义务,何况舜与禹是杀父之仇。大禹如何对待舜杀父这件事,司马迁是清楚的,他在《史记·夏本纪》中说:舜于是殛之于羽山,副之以吴刀。禹不敢怨而反事之,官为司空,以通水潦,颜色黎黑,步不相过,窍气不通,以中帝心。《史记·夏本纪》载: “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一句“禹不敢怨而反事之”,一句禹“过家门不敢入”,一句“以中帝心”,反映的是大禹“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的韬光养晦。从舜冤杀鲧到让鲧子禹继续治水,再到舜同意禹继承帝位的整个过程看,舜对鲧禹父子是怀有负罪感的,舜对鲧禹父子族系进行着心理补偿和安抚。这种补偿和安抚,源于舜冤杀鲧后受到的强大社会谴责、社会呼声和社会压力。
舜冤杀鲧导致天下诸侯叛离。《史记·夏本纪》载:舜死后,“三年丧毕,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当时,舜子商均据有首都阳城,大禹辞别商均离去。天下诸侯也都脱离商均而去追随拥戴大禹为夏帝。
尧舜冤杀鲧引起社会叛乱。《山海经·大荒北经》载:鲧妻士敬,士敬子曰炎融,生驩头……有驩头之国。《大荒北经》载: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颛顼生驩头,驩头生苗民,苗民厘姓,食肉。《海外南经》载:三苗國,在赤水東,其為人相隨。郭璞注说: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有苗之民,叛人南海,为三苗国。《大荒北经》载:“有鲧攻程州之山。”三苗之君不同意尧将帝位传给其女婿舜,说了些非议尧舜的话,尧就杀了三苗之君,引起苗民反叛,跑到南方建立了三苗國。
舜冤杀鲧引起舆论谴责。公众舆论认为鲧与大禹都是治水功臣。《山海经·海内经》说“禹鲧是始布土”,将禹、鲧治水并列。《国语·鲁语》说:“鲧鄣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鲧之功”, 韦昭注说:“鲧功虽不成,禹亦有所因,故曰修鲧之功。”这是说禹继承了鲧治水的功业。《国语·吴语》说: “今王既变鲧禹之功,而高高下下,以罢民于姑苏。”这里鲧、禹治水之功业并列。《韩非子·五蠹》说: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所笑。《淮南子·务修训》说:“听其自流,待其自生,则鲧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 以上文献均将鲧禹父子治水之功相提并论,认为鲧同禹一样,也是一位功劳盖世的治水大英雄。特别是屈原,他对尧舜杀鲧愤悱不平:
鸱龟曳衔,鲧何听焉?顺欲成功,帝何刑焉?
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 伯禹愎鲧,夫何以变化!
纂就前绪,遂成考功。 何续初继业?而厥谋不同?
洪泉极深,何以窴之? 地方九则,何以坟之?
河海应龙,何画何历? 鲧何所营?禹何所成?
康回冯怒,坠何故以东南倾(《天问》)。
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然夭乎羽之野(《离骚》)
鯀被尧舜冤杀后,百姓怀念崇拜鯀。鯀逐渐演变为治水神灵,白马就是鲧的神圣形象。
《左传·昭公七年》载:“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祀之。”黄熊当为黄能之误,《尔雅·释鱼》曰:“鳖三足,能。”能是鱼类中的神鳖,可化为龙。这里说尧虽然杀了鲧,但夏、商、周三代都祭祀鲧。
《山海经》郭璞注引《开筮》说:鲧死三岁不腐,剖之以吴刀,化为黄龙。
《国语·晋语八》载:昔者鲧违帝命,殛之于羽山,化为黄能,以入于羽渊。
《礼记·祭法》孔颖达疏说:鲧障洪水而殛死者,鲧塞水而无功,而被尧殛死于羽山,亦是有微功于人,故得祀之。若无微功,焉能治水九载? 孔颖达也说鲧治水有功。
《太平广记·卷四百六十六》说:“尧命夏鲧治水,九载无绩。鲧自沉于羽渊,化为玄鱼。时植振鳞横游波上,见者谓为河精,羽渊与河海通源也。上古之人于羽山之下修立鲧庙,四时以致祭祀。”后世将黄河中波涛汹涌之处称之为“白马浪”即源于此,如中卫北长滩之“白马浪”。
《山海经·海内经》说: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周礼·夏官·庾人》说:“马八尺曰龙。” 鲧被冤杀化为龙,鲧名白马,白马也就化为龙了。
在神灵世界,鲧最初幻化为神鱼、黄龙、白龙马,一直指引百姓治水开渠。后来,鲧定形为人格化的白马将军,百姓建庙建寺,鲧以“白马”名号世代享受祭奠。
“禅让”疑云
关于鲧的史料,早期后期记述不同,诸子百家与正史记述不同,
汲冢竹简与儒家经典记载不同,总是各有因起。
《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睢》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孔子定《六经》,“断自唐、虞以下;前乎唐、虞,无征不信”,与孔子编辑旨意不符的很多上古图册典籍被其删除。《山海经》、诸子百家记述鲧的史迹来自孔子之前或孔子删诗书、定礼乐之外的淘汰资料、编外资料,其记载内容与孔子删定的诗书是有很多不同的。《韩非子》载:“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而诛杀鲧于羽山之郊。共工又谏曰:‘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又举兵而诛共工于幽州之都。于是天下莫敢言无传天下于舜。仲尼闻之曰:‘尧之知舜之贤,非其难者也。夫至乎诛谏者,必传之舜,乃其难也。’一曰:‘不以其所疑,败其所察,则难也。’”尧诛杀了不同意他让舜继承帝位的鲧和共工这二个大臣,对此,孔子的感慨评论是:尧为了实施他自己认为已经看准必做的事,就是决心要把天下传给自己的女婿舜。为此目的,尧不惜下恨心杀掉提出不同意见的人,这在一般人是干不出来的,但尧干出来了,他达到自己的目的了,这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但是,尧做到了!尧成功了!很明显,孔圣人对尧的这种做法是赞赏的!康有为读到孔子这种论调时,也感到孔子此说不妥,但出于为尊者讳,就说这则记载是韩非子编造的,康有为说:“此必韩非托古,并托为孔子之言,以自成其说(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康有为这是为孔子不讲理的说法做辩解。《山海经·海内经》载: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山海经》中尧杀鲧这条记载与《韩非子》同,但远早于《韩非子》。总不能说《山海经》也“托古”。《山海经》的原始资料大多来自远古,未经孔子删改,原始性强。《吕氏春秋》载:尧以天下让舜。鮌为诸侯,怒于尧曰:“得天之道者为帝,得帝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以尧为失论”。《吕氏春秋》这则鮌不同意“尧以天下让舜”的记载亦与《山海经》同。《吕氏春秋》写成于秦统一六国之前(公元前239年),这时秦始皇尚未焚书。焚书之前史料易得,《吕氏春秋》融汇诸子百家,兼容并包,取精用宏,书成之后,“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史记·吕不韦列传》),其原始资料的可信度很高。
对于《尚书》《史记》《论语》《孟子》等传统儒家典籍津津乐道的尧、舜、禹帝位“禅让”制度,《韩非子·说疑》认为是儒家自我宣传的结果:“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察四王之情,贪得人之意也;度其行,暴乱之兵也。然四王自广措也,而天下称大焉;自显名也,而天下称明焉。则威足以临天下,利足以盖世,天下从之。”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在今河南汲县西南的一座古墓里出土了一批竹简,史书写在竹简上,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史事,截止于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99年),被称为古本《竹书纪年》。在这部古书中,记载了与《尚书》《史记》《论语》《孟子》等传统儒家典籍不同的历史事实,如:“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放尧于平阳。”“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共伯和干王位”等等,有些内容还与甲骨文﹑金文符合。以上证明,《山海经》《韩非子》《国语》等诸子百家及《吕氏春秋》记载的尧为了传帝位于其女婿舜,不惜与舜合谋冤杀鲧是历史事实,传统儒家典籍津津乐道的尧、舜、禹帝位“禅让”制度,实际上是腥风血雨的一系列宫廷政变或军事夺权。
历史是抹不尽的,公道自在人心。鲧含冤屈死,从夏商周时代开始,他由尘世治水英雄逐渐演化为天国的治水神灵,一直受到中华各族的怀念与祭祀,可见其影响之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