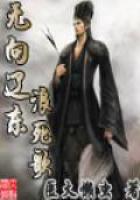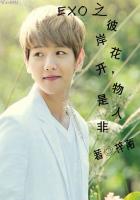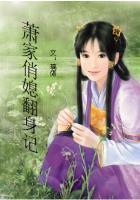“流沙”名称考
“流沙”是古人对沙漠地带一种特有自然现象的称呼。“流沙”到底指什么现象,历来争议不断。
“流沙”的早期记载,多见之于《山海经》:
(1)《海内西经》:流沙出钟山,西行又南行昆仑之虚,西南入海黑水之山。
(2)《西山经·西次三经》:又西百八十里,曰泰器之山。观水出焉,西流注于流沙。
(3)《西山经·西次三经》:又西三百七十里,曰乐游之山……西水行四百里,曰流沙,二百里至于蠃母之山,神長乘司之,是天之九德也。
(4)《北山经》:又北三百二十里,曰灌題之山,其上多樗柘,其下多流沙,多砥。
(5)《北山经》:又北水行五百里,流沙三百里,至于洹山,其上多金玉。
(6)《東山經》:又南水行五百里,流沙三百里,至于葛山之尾,無草木,多砥礪。
(7)《東山經》:又南水行三百里,流沙百里,曰北姑射之山,無草木,多石。
(8)《東山經》:又南水行五百里,曰流沙,行五百里,有山焉,曰跂踵之山,廣員二百里,無草木,有大蛇,其上多玉。
(9)《東山經》:又南水行五百里,流沙三百里,至于無皋之山,南望幼海,東望榑木,無草木,多風。是山也,廣員百里。
(10)《大荒北经》:“西北海外,流沙之东,有国曰中“车扁(轮)”,颛顼之子。”
(11)《海内东经》:国在流沙中者埻端、玺“日奂”,在昆仑虚东南。一曰海内之郡,不为郡县,在流沙中。”
(12)《海内东经》:国在流沙外者,大夏、竖沙、居繇、月支之国。
(13)《海内东经》:西胡白玉山在大夏東,蒼梧在白玉山西南,皆在流沙西,昆侖虛東南。昆侖山在西胡西,皆在西北。
(14)《大荒南經》:南海之外,赤水之西,流沙之東,有獸,左右有首,名曰(足朮)踢。有三青獸相并,名曰雙雙。
(15)《大荒西经》: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侖之丘。”
(16)《大荒西经》: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启)。
(17)《大荒南经》: 南海之外,赤水之西,流沙之东,有兽”。郭璞云:“赤水出昆侖山,流沙出锺山也。
(18)《海内经》载:西海之内流沙之中有国,名曰壑市。
(19)《海内经》载:西海之内流沙之西有国,名曰汜叶。
(20)《海内经》载:流沙之西有鸟山者,三水出焉。
(21)《海内经》载:“流沙之東,黑水之西,有朝雲之國、司彘之國。
(22)《海内经》载:流沙之东,黑水之间有山,名不死之山。”
以上22处“流沙”,从其内容看,分为两种,一种是概指流沙地貌,如多流沙、流沙百里、流沙三百里、注于流沙、流沙之中、国在流沙中、国在流沙外等;另一种是特指地名,如曰流沙、流沙之东、流沙之西、皆在流沙西。
“流沙”史籍多载,何谓“流沙”?注家纷纭,皆不得“流沙”要领,难窥全豹。
一说沙在水中,沙随水流,谓之“流沙”,此说实误。宋代沈括到过沙漠,他在其《夢溪筆談·卷三》中说:“予嘗過無定河,度活沙,人馬履之,百步之外皆動,澒澒然如人行幕上。其下足處雖甚堅,若遇其一陷,則人馬驰車,應時皆沒,至有數百人平陷無孑遺者。或謂:此即流沙也。又謂:沙隨風流,謂之流沙。” 沈括过無定河时所履之“活沙”,是河沙、水沙。沙随水流产生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沙、水混流后沙面平坦坚实,人践、车行皆不陷,俗称之“死沙”;第二种是沙、水混流后表层沙面平坦松软,下层沙浆深不可测,人践、车行其上周边晃动,践之则陷,人马、车辆往往深陷不拔至有没顶之灾,俗称为“灢泥潭子”。沈括说“或謂:此即流沙也”,非也。究其实,沈括所履之“活沙”绝非“流沙”,而是河沙、水沙地带的“灢泥潭子”。
二说“沙隨風流,謂之流沙”。《元和郡县图志》说:居延海“即居延泽,古文以为流沙者,风吹流行,故曰流沙,”沈括说“又謂:沙隨風流,謂之流沙。”这种解释,放之沙漠地区皆可,并没有说清“流沙”的地貌特征。
三说“沙流而行”谓之“流沙”。《离骚》说:“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与”,《楚詞·招魂》说:“魂兮归来!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王逸将其注为 “沙流如水也”、“流沙,沙流而行也”。此说不得“流沙”的地貌特征,未解“沙流而行”的起因。
对“流沙”地貌注释深得要领者首推郭璞。郭璞说:“今西海居延澤。《尚書·禹貢》所謂‘流沙’者,形如月生五日也。”郭璞说“流沙”的形状如同“月生五日”之形状。“月生五日”即指农历每月初五升起的月牙儿,其状弯如镰刀,称初月,亦称新月。只有身处“流沙”地带,放眼高低错落,一望无际的月牙形流动沙丘,才知这些流动沙丘恰似连绵不断的月牙儿。郭璞用月牙儿的形状比拟“流沙”的地貌特征,这样的比拟,只有到过沙海的人,亲眼观察过“流沙”地貌的人才能有如此生动贴切的比拟。郭璞对“流沙”的注释,楊慎是理解的,他说:“謂形如半月也。”具有月牙儿形状的“流沙”,晴天沙丘万籁俱静,人或动物践之则沙动如流,流水穿越沙丘则沙随水流;风天沙丘随风流扬,盖地铺天。以上谓之“流沙”地貌。
在“流沙”的注释上,袁珂先生失之。袁先生说:“郭、楊之說流沙,乃詩之構想也。”还有失之更甚者,竟将郭璞的注释理解为:东晋郭璞在注释《山海经》时说:“‘今西海居延泽,《尚书》所谓流沙者,形如月生五日也’。可见东晋时代,这个湖在枯水期是六个小湖:一个大的像月亮,五个小的像太阳。郭璞形容说一个月亮妈妈生下了五个儿子。” 此为望文生义。
《禹贡》流沙地望诸说
特指地名的“流沙”,首见于《尚书·禹贡》:“导弱水,至于合黎,馀波入于流沙。”
《尚书·禹贡》所说的 “?流沙”在什么地方,历代学者考证记述不一。
第一种说法,“?流沙”在今甘肃景泰县。
《史记·五帝本纪》载:颛顼时代道路“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对此 “流沙”,“正义”引括地志说,“流沙”在“居延海南,甘州张掖县东北千六十四里是。”据張俊民《簡牘文書所見“長安”資料輯考》换算标准,以今地度之,“流
沙”约在今甘肃景泰县毗邻地区(见《夏朝西部疆界考》)。
第二种说法,“?流沙”在河西张掖居延泽。
《尚书·禹贡》载:“导弱水,至于合黎,馀波入于流沙。”对此“流沙”,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载:郑康成曰:弱水出张掖。 《水经》云“弱水出张掖删丹县西北,至酒泉会水县入合黎山腹”,知合黎山在河西走廊。《十三经注疏》说:《地理志》张掖郡删丹县,桑钦以为导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张掖郡又有居延泽,在县东北,古文以为流沙。
《史记·夏本纪》载:大禹“道九川: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对此 “流沙”,“集解”孔安国曰:弱水余波西溢入流沙 。郑玄曰:地理志流沙在居延西北,名居延泽 。地记曰:弱水西流入合黎山腹,余波入于流沙,通于南海。“索隐”地理志云:张掖居延县西北有居延泽,古文以为流沙 。《史记·李将军列传》载:天子以为李氏世将,而使将八百骑,尝深入匈奴二千馀里,过居延,视地形,无所见虏而还。拜为骑都尉,将丹阳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张掖以屯卫胡。对李广所过的“居延”,“集解”徐广曰:属张掖。“正义”括地志云:居延海在甘州张掖县东北六十四里。地理志云:居延泽古文以为流沙。甘州在京西北二千四百六十里。“正义”括地志云:居延海在甘州张掖县东北六十四里。地理志云:居延泽,古文以为流沙。《水经注笺·卷四十》载:“流沙地在张掖居延县东北。”郦道元注释说:居延泽在其县故城东北。《元和郡县图志》载:(居延海)即居延泽,古文以为流沙者,风吹流行,故曰流沙。
第三种说法,“?流沙”在河西玉门关外。
《吕氏春秋·本味》载: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凤之丸,沃民所食。 高誘注释说:流沙在敦煌郡西,八百里。《汉书·地理志》载:道弱水,至于合藜,餘波入于流沙。師古曰:合藜山在酒泉。流沙在敦煌西。晋郭义恭《广志》说: 流沙在玉门关外,有居延泽﹑居延城。《晋书·张骏传》载:骏使其将杨宣率众越流沙,伐龟兹鄯善。《魏书·世祖纪》载:太平真君三年,沮渠无讳度流沙,据鄯善。《周书·异域传》载:鄯善西北有流沙百里,夏日有热风,为行旅之患。《唐书·西域传》载:吐谷浑西北有流沙数百里,夏有热风伤行人。
第四种说法,“?流沙”概指西方沙漠。
《楚辞·招魂》载:魂兮归来,西方之害,流沙千里。王逸注释说:流沙,沙流而行也。《尚书》曰:“馀波入於流沙”。言西方之地,厥土不毛,流沙滑滑,昼夜流行,从广(一作纵横)千里,又无舟航也。
以上四种说法中,哪种说法比较接近《尚书·禹贡》所说的 “?流沙”地望,这就需要考察接近那个时代的历史文献记载。
《礼记》四段黄河地望
《礼记》是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其中多数篇章内容源自先秦典籍,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汇编。
《礼记·王制》载: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遥;自东河至于东海,千里而遥。自东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遥。西不尽流沙,南不尽衡山,东不近东海,北不尽恒山。凡四海之内,断长补短,方三千里,为田八十万亿一万亿亩。
《礼记·王制》说“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遥”,即说流沙在“西河”之西直线距离1000多里的地方。知道了“西河”所在,就知道流沙所在。学术界通常以晋陕间黄河段(托克托经河曲至陕西潼关黄河段)为“西河”。若以晋陕间黄河段为“西河”,以“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遥”为标尺判断流沙方位,则流沙就到了宁蒙黄河段(兰州经银川至磴口黄河段)附近,这就与研究《史记·五帝本纪》《尚书·禹贡》《史记·夏本纪》《史记·李将军列传》及《元和郡县图志》等主流学者公认“?流沙”在张掖居延泽的定论大唱反调!反之,若以主流学者公认“?流沙”在张掖居延泽为标杆判断“西河”方位,则“西河”就到了宁蒙黄河段,这就推翻了学术界以晋陕间黄河段为“西河”的共识!
西河究竟在哪里?查阅史籍,先秦習慣將万里黄河分爲西河、南河、東河三段。每段黄河的地理方位古今所说不同,彼西河非此西河,彼流沙非此流沙。若知《禹贡》时代的流沙所在,须辨明《禹贡》时代的西河所在。
據譚其驤先生研究,西周以前的黄河下游,和东周秦汉一样,是流经河北平原注入渤海的。公元前 4世紀以前,黃河下游在这块土地上多次改道,冲积形成了河北平原。河北平原南界黄河,北至燕山,西邻太行山,东濒渤海。譚其驤先生考证,《山海經》《禹貢》记载的黄河下游在河北平原偏西,沿太行山麓北流。其中:《山海經》记载的黄河自今河南武涉以下北至今河北深县南同《禹贡》河,在深县与《禹贡》河分流后北流经今蠡县,至清苑县折而东流,经今安新县南、雄縣、霸县北,东流至今天津市东北流人勃海。《禹貢》记载的黄河从今河南滑县西南的宿胥口缘大伾山西麓北流,经今河北曲周县,巨鹿县北,在今青縣以東流入勃海。《漢书·地理志》记载的黄河離開太行山東麓,从今河南滑县西南的宿胥口东北流至今濮阳县西南长寿津,自长寿津折而北流至今馆陶县东北,折东经高唐县南,折北至东光县西会合漳水,此下折而东北流经汉章武县南,在今黄骅县东流人勃海。
从譚其驤先生的考证看,先秦黄河下游故道在河北平原偏西,先沿太行山麓北流,继而东折在河北平原东北流,在今天津附近流入勃海。
《礼记·王制》中出现了“恒山”“南河”“江”“衡山”“东河”“东海”“西河”“流沙”诸地名。从其记载的山川地理方位看,“恒山”即北岳恒山,古今方位同,在今山西浑源县境内。“南河”“东河”“西河”皆指黄河段落,古代黄河走线因改道多有变动,尤其是下游。“江”指长江,古代长江走线因改道多有变动。“衡山”即南岳衡山,古今方位同,在今湖南衡阳境内。从北岳恒山经南河、长江至南岳衡山,直线距离约3000里;从东海经东河、西河至流沙,直线距离约3000里。要考证“?流沙”的位置所在,首先要确认“南河”“东河”“西河”的位置所在。确认“南河”“东河”“西河”的位置所在,必须辨清先秦黄河故道的位置所在。黄河定型后的先秦故道从源头至潼关古今方位大同小异,潼关以下至勃海改道多变。
《礼记·王制》记载山川地理距离以直线计,两地之间的估算距离“不足谓之近”,“有余谓之遥”。依其记载,现以线段比例尺估测《礼记·王制》所载山川地理在现代地图上的方位距离。
《礼记·王制》记载的“恒山”“南河”“江(长江)”“衡山”是从北向南依地名顺序直线排列的。该记载首从北岳恒山开始,自北向南估算直线距离,我们也以直线估测其距离:“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此“南河”当在今河南焦作黄河一线(自西向东流);“自南河(焦作黄河)至于江,千里而近”,此“江”当在今湖北武汉长江一线略北(自西向东流);“自江(武汉长江一线略北)至于衡山,千里而遥”,此“衡山”古今同位,在今湖南衡阳境内。从估测距离看,除长江故道在今武汉长江一线方位略北以外,“南河”(焦作黄河)一线方位古今相差不大。由此看出,流经今河南焦作一线的黄河即是《礼记·王制》记载的“南河”。焦作段黄河是河北平原古黄河中的西段,不管古黄河怎样改道,河北平原上的古黄河总体上是自西向东流入勃海的。由此可知,《礼记·王制》称自西向东经河北平原流入勃海的黄河为“南河”。
《礼记·王制》记载“东海”“东河”“西河”“流沙”是从东向西依地名顺序直线排列的。该记载首从“东海”开始,自东向西直线估算距离,我们也以该直线估测其距离:“自东河至于东海,千里而遥”,考虑该记载从东向西依地名顺序直线排列的行文方式,这句话可变为“自东海至于东河,千里而遥”,此“东河”当在今山西河曲晋陕黄河一线(自北向南流);“自东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此“西河”当在今内蒙古磴口宁蒙黄河一线略西(自南向北流);“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遥”,此“流沙”当在今甘肃张掖沙漠附近。由此看出,流经今山西河曲晋陕黄河一线(自北向南流)的古黄河,《礼记·王制》称为“东河”; 流经今内蒙古磴口宁蒙黄河一线略西(自南向北流)的古黄河,《礼记·王制》称为“西河”;今甘肃张掖附近的沙漠,《礼记·王制》称为“流沙”。
纵观万里黄河的古今走线,总体上看,黄河非常像一个巨大的“几”字形。从青海黄河源头经甘肃兰州、宁夏银川至内蒙古磴口段,大致自西南向东北流;从磴口至内蒙古托克托,大致自西向东流;从托克托经河曲至陕西潼关,大致自北向南流;从潼关经河南、山东至勃海,大致自西向东流。
万里黄河以上各段与《礼记·王制》记载的各段黄河有对应关系。
从纵向方位看,南北流向的黄河有两段:兰州经银川至磴口的宁蒙黄河段位于最西面(南北流向),直线距离长1000多里,相当于《礼记·王制》记载的“西河”;托克托经河曲至潼关的晋陕黄河段位于最东面(北南流向),直线距离长1000多里,相当于《礼记·王制》记载的“东河”。从最西边的兰州经银川至磴口的宁蒙黄河段向西直线距离约1000里,相当于《礼记·王制》记载的“流沙”,此“流沙”在今至甘肃张掖附近。
从横向方位看,西东流向的黄河有两段:磴口至托克托黄河段位于最北面,直线距离不足千里,相当于秦汉史籍记载的“北河”;潼关东至勃海黄河段位于最南面,直线距离长1000多里,相当于《礼记·王制》记载的“南河”。
《礼记·王制》所载各段黄河对应的万里黄河各段名称亦见诸古代史料记载。
《礼记·王制》中“西河”对应的兰州经银川至磴口的宁蒙黄河段。
《禹贡》中的西河,学术界一种说法是在今宁蒙黄河段(兰州经银川至磴口黄河段),另一种说法是在今晋陕黄河段(托克托经河曲至陕西潼关黄河段)。《尚书·夏书·禹贡》载:“黑水、西河惟雍州。”孔颖达疏:“计雍州之境,被荒服之外,东不越河 ,而西逾黑水 。王肃云‘西据黑水 、东距西河 ’,所言得其实也。”黑水即今张掖河。按孔颖达疏,雍州地界“东不越河”,若“西河”指今晋陕黄河段(托克托经河曲至陕西潼关黄河段),则雍州地界越过了今宁蒙黄河段(兰州经银川至磴口黄河段)。若雍州地界“东不越河(托克托经河曲至陕西潼关黄河段)”,则今宁蒙黄河段(兰州经银川至磴口黄河段)当为“西河”。《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今车骑将军青度西河至高阙,获首虏二千三百级,车辎畜产毕收为卤,已封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高阙在今宁蒙黄河段(兰州经银川至磴口黄河段)北岸的狼山西端,卫青“度西河”至高阙,渡的正是今宁蒙黄河段(兰州经银川至磴口黄河段)。据此,《礼记·王制》中的“西河”当指今宁蒙黄河段(兰州经银川至磴口黄河段)。
《礼记·王制》中“东河”对应的托克托经河曲至潼关的晋陕
黄河段。
清末经学家孫詒讓依据古注将黄河分为“南河”“東河”,以其“東河”诠释《礼记·王制》中的東河。孫說:黄河“過大伾山南,至今河南衛輝府浚縣,漢黎陽縣宿胥口,又折而東北流,合漳水,至今直隸永平府樂亭縣碣石入海,《王制》所謂東河也(《周礼·正义》)。” 孫詒讓的这种黄河二分法,与《礼记·王制》的黄河三分法显然不符:一是此说没有了“西河”,二是说“東河”“過大伾山”自西向东“至今直隸永平府樂亭縣碣石入海”。孫说的这条“東河”,大致西东流向,不可能如《礼记·王制》所言“自东海至于东河,千里而遥”。孫詒讓的“東河”之说于《礼记·王制》无据,于“自东海至于东河,千里而遥”不合实际。据此,孫詒讓说的这条西东流向穿越河北平原的所谓“東河”不是《礼记·王制》记载的“東河”。
《礼记·王制》记载的“东河”位置所在。《尚書·禹貢》载:“濟、河惟兗州。”孔傳:“東南據濟,西北距河。”孔疏:“濟、河之間相去路近,兗州之境,跨濟而過,東南越濟水,西北至東河也。”《爾雅·釋地》:“濟、河間曰兗州”,郭璞注:“自河東至濟。”邢疏:“《禹貢》:‘濟、河惟兗州。’孔安國云:‘東南據濟,西北距河。’孔《傳》凡云‘據’者,謂跨之也。距,至也。濟、河之間相去路近,兗州之境,跨濟而過,東南越濟水,西北至東河也。”《爾雅·釋山》云:“河東岱”,邢昺疏云:“云‘河東岱’、注‘岱宗,泰山’者,在東河之東,一名岱宗,一名泰山。”从以上疏证看,《禹貢》时代的黄河与济水相距甚远,黄河在西北,济水在东南。济水在河北平原东南的方位比较稳定,黄河下游至入海段在河北平原的方位改道多变,秦汉时代的黄河下游与济水“相去路近”,方位大体一致。据譚其驤先生的考证,《禹貢》时代的黄河下游在今天津附近入海。《礼记·王制》说“自东海至于东河,千里而遥”,在河北平原上从天津附近的“东海”向西找不道直线相距1000多里的“东河”。所以,各注疏所说的河北平原上的“东河”绝不是《礼记·王制》记载的《禹貢》时代的“东河”,而是秦汉时代与济水“相去路近”的黄河。从今天津附近的“东海”向西直线距离1000多里的“东河”,只能是今晋陕黄河段(托克托经河曲至陕西潼关黄河段)。今晋陕黄河段(托克托经河曲至陕西潼关黄河段)才符合是孔安國等说的東河: “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東南越濟水,西北至東河”。所以,《礼记·王制》中的“东河”当指今晋陕黄河段(托克托经河曲至陕西潼关黄河段)。
《礼记·王制》中“南河”对应的潼关东至勃海黄河段。
“南河”见于《尚书·夏书·禹贡》:“?荆及衡阳惟荆州……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 荆州属《禹贡》九州之一。《尚书》记载:荆、河唯豫州,荆州北界与豫州(今河南属之)毗邻。江、沱、潜、汉为荆州四水,其中汉水发源于陕西省西南部汉中地区,洛水流经河南洛阳、偃师、巩义后北入黄河。“禹贡”时代长江、汉水与洛水不通,大禹导河治水时从陆路越洛水抵达“南河”。《禹贡·夏书》记载:“导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厎柱、析城,至于王屋。” 注疏说:“厎柱、析城,至于王屋,此三山在冀州“南河”之北东行”(《十三经注疏》)。由上可知,“南河”之名出自《禹贡》时代。从“南河”与其毗邻地名方位看,“南河”从河南自西向东流、经河北平原流入勃海,横贯中原南部,称为“南河”名实相副。?清末经学家孫詒讓說:“禹治河故道,自積石西來,至今鄂爾多斯左翼後旗唐東受降城,折而南流,入《職方》雍、冀二州境,《禹貢》、《王制》所謂南河也。” 孫說与《礼记·王制》记载不符,与南河地理方位不符。《尔雅注疏》说:《禹貢》導河自積石、龍門,南流謂之西河。至于華陰,折而東,經底柱、孟津、過洛,皆東流,謂之南河。刘熙说:“南河,九河之最在南者。”正义括地志云:“故尧城在濮州。。。河在尧都之南,故曰南河,禹贡“至于南河”是也。据此,《礼记·王制》中的“南河”当指今潼关至勃海黄河段。
史籍记载中的“北河”对应磴口至托克托黄河段。
“北河”之名,应出于先秦,是相对于“南河”而言的。
《史记·秦本纪》载:秦惠文王(前337年-前311年在位)五年,王游至北河。《汉书·五行志》载:秦孝(当为“惠”)文王五年,王游朐衍,有献五足牛者。“集解”徐广曰:戎地在河上。“正义”按:王游观北河,至灵、夏州之黄河也。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今车骑将军青“按榆溪旧塞,绝梓领,梁北河,讨薄泥,破符离。“如淳”曰:绝,度也。为此河作桥梁也。
《水经注校》载:“河水又北,屈而为南河出焉。河水又北迤西,溢於窳浑县故城东”。郦道元注笺说:“其水积而为屠申泽,泽东西一百二十里,故《地理志》曰:屠申泽在县东,即是泽也。阚駰谓之浑泽矣。屈从县北流。”紧接此经文,“河水又屈而东流,为北河,东迳高阙南。”由此可知,南河为黄河支流。北河为黄河正流,称北河。以今地言之,此段黄河自今内蒙古磴口县以东至包头西面分为南北二支,北支约当今乌加河,时为黄河正流,对南支而言,乌加河称北河。据此,磴口至托克托黄河段位于黄河流经地区的最北面,东西直线距离不足千里,相当于秦汉史籍记载的“北河”。
《禹贡》流沙地望
《礼记》四段黄河地望既清,其说“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遥”, 流沙地望一览可知。
《礼记·王制》中“流沙”对应今甘肃张掖沙漠。
《尚书·禹贡》载:“导弱水,至于合黎,馀波入于流沙。”《禹贡》时代的“流沙”,主流学者一致持第一种说法,即“?流沙”在张掖居延泽。研究《尚书·禹贡》《史记·五帝本纪》《史记·夏本纪》《史记·李将军列传》《水经注》等的主流学者皆主此说。唐《元和郡县图志》亦载:张掖郡又有居延泽,在县东北,古文以为流沙。从以上考证看,甘肃张掖沙漠符合 “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遥”的记载,据此,《礼记·王制》中的“流沙”当指今甘肃张掖居延流沙。
《淮南子·地形训》载:“西王母,在流沙之濒。”《太平御览》地部引崔鸿《十六国春秋》说:“酒泉太守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昆仑之体。有西王母石室”。从《礼记·王制》流沙地望可知,西王母之
国应在今青藏高原东北部的河西走廊。
对于“?流沙”的第一种、第三种、第四种说法,借用《王鸣盛尚书后按》之语总括其差错原委:近人谓流沙在今嘉峪关外,遂于晋魏隋唐诸史启蒙徵西域流沙以当之。夫流沙多矣,非弱水所入,岂可据以易汉志古文说乎?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遥,惟其在居延故耳!如
以龟兹、鄯善、且末、吐谷浑等国之流沙皆牵引以充《禹贡》之流沙,则距西河万里,安得云千里哉!
§§华夷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