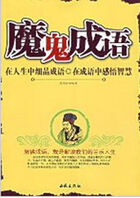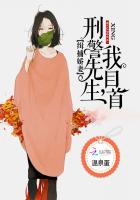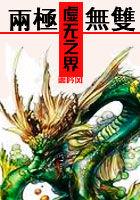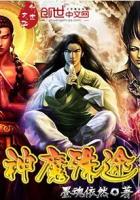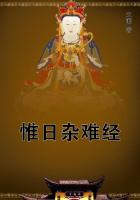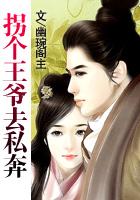谈谈明末
每个人一生,都有没齿难忘的经历。
大约一六七〇年,已是大清子民的计六奇这样写道:
四月廿七日,予在舅氏看梨园,忽闻河间、大名、真定等处相继告陷,北都危李洁非有关。事发之时,作者年方二十二岁,正是英华勃发的大好年华。在这样的年龄遭逢塌天之变,其铭心刻骨,必历久如一而伴随终生。时间过去将近三十年,计六奇渐趋老境,体赢力衰,患有严重眼疾,“右目新蒙,兼有久视生花之病”,而愈如此,那急,犹未知陷也,舅氏乃罢宴。廿八日,予种将青春惨痛记忆付诸笔墨的欲望亦愈下乡,乡间乱信汹汹。廿九日下午,群徵叔云:“崇祯皇帝已缢死煤山矣。”予大惊异。
三十日夜,无锡合城惊恐,盖因一班市井无赖闻国变信,声言杀知县郭佳胤,抢乡绅大户。郭邑尊手执大刀,率役从百人巡行竟夜。嗣后,诸大家各出丁壮二三十人从郭令,每夜巡视,至五月初四夜止。①“四月廿七日”,指的是1日历甲申年四月二十七日,置换为公历,即一六四四年六月一日。文中所叙,距其已二十余载,而计六奇落笔,恍若仍在眼前,品味其情,更似锥心沁血,新鲜殷妍,略无褪色。
之如此,盖一以创巨痛深,二与年龄强烈。从动手之始到书稿告竣,先后四五年光景,“目不交睫,手不停披,晨夕勿辍,寒暑无间,宾朋出入弗知,家乡米盐弗问,肆力期年,得书千纸。”②他曾回顾,庚戌年(1670)冬天江南特别寒冷,大雪连旬,千里数尺,无锡“一夕冻死”饥民四十七人,即如此,仍黾勉坚持写作,“呵笔疾书,未尝少废”;而辛亥年(1671)夏季,又酷热奇暑,计六奇同样不肯停笔,自限每日至少写五页(“必限录五纸”),因出汗太多,为防洇湿纸页,他将六层手巾垫于肘下,书毕抬起胳膊,六层手巾已完全湿透……须知,这么历尽艰辛去写的上千页文字,对作者实无任何利益可图——囚所写内容犯忌,当时根本无望付梓,日后能否存于人间亦难料定。他所以这样燃烧生命来做,只不过为了安妥自己一段挥之不去的记忆。
今天,不同年龄层的人,每自称“××一代”。作为仿照,十七世纪中叶,与计六奇年龄相近的那代中国人,未必不可以称为“甲申一代”。他们的人生和情感,与“甲申”这特殊年份牢牢粘连起来。令计六奇难以释怀,于半盲之中、将老之前,砣砣写在纸上的,归根到底便是这两个字——当然,还有来自它们的对生命的巨大撞击,以及世事虽了、心事难了的苦痛情怀。
倘若尽量简短地陈述这两个字所包含的要点,或许可以写为一公元一六四四年(旧历甲中年,依明朝正朔为崇祯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清晨,李自成攻陷皇城前,崇祯皇帝以发蒙面,缢死煤山。自此,紫禁城龙床上不复有朱姓之人。五月二十九日,从山海关大败而归的李自成,在紫禁城匆匆称帝,“是夜,焚宫殿西走。”③六月七日,满清摄政王多尔衮率大军进入北京。
某种意义上,这样的历史更迭只是家常便饭。之前千百年,大大小小搬演过不下数十次,一六四四年则不过是老戏新演而已。就像有句话总结的:几千年来的历史,无非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就此而言,明末发生的事情,与元、宋、唐、隋、晋、汉.秦之末没有什么不同。
作为二十世纪下半叶以后出生的中国人,我们有幸读过不少用这种观点写成的史着或文艺作品。或许,一度也只能接触这种读物。对于明末的了解,笔者最早从一本叫《江阴八十天》的小册子开始,那是一九五五年出版的一本通俗读物,写江阴抗清经过,小时候当故事来看,叙述颇简明,然每涉人物,必涂抹阶级色彩,暗嵌褒贬、强史以就。中学时,长篇小说《李自成》问世,同侪中一时抢手,捧读之余,除了阶级爱憎,却似无所获。晚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某《南明史》出版,当时专写南明的史着还十分稀有,抱了很高热忱拜读,发现仍然不弃“阶级分析”,于若干史实继续绕着弯子,闪烁其词,文过饰非。
将几千年历史限定为“一部阶级斗争史”,无法不落入窠臼,使历史概念化、脸谱化。就受伤害程度而言,明末这一段似乎最甚。这样说,可能与笔者个人感受有关,所谓知之深、痛之切。但感情因素以外,也基于理性的审视。在我看来,明末这一段在中国历史上有诸多突出的特质:时代氛围特别复杂,头绪特别繁多,问题特别典型,保存下来、可见可用、需要解读的史料也特别丰富。
明代是一个真正位于转折点上的朝代。对于先前中华文明正统,它有集大成的意味,对于未来,又有破茧蜕变的迹象。
没有哪个时代,思想比明代更正统,将中华伦理价值推向纯正的极致。同样,亦没有哪个时代,思想比明代更活跃、更激进乃至更混乱,以致学不一途、矫诬虚辩、纷然骤讼,而不得不引出黄宗羲一部煌煌巨着《明儒学案》,专事澄清,“分其宗旨,别其源流”,“听学者从而自择”④。
这一思想情形,是明朝历史处境的深刻反映。到明代晚期,政治、道德、制度无不处在大离析状态,借善恶之名殊死相争,实际上,何为善恶又恰恰混沌不清,乃各色人物层出不穷,新旧人格猛烈碰撞、穷形尽相,矛盾性、复杂性前所未见。
别的不说,崇祯皇帝便是一个深陷矛盾之人,历史上大多数帝王只显示出单面性——比如“负面典型”秦始皇、“正面典型”唐太宗——与他们相比,崇祯身上的意味远为丰富。弘光时期要人之一的史可法,也是复杂的矛盾体:明代文天祥有人视为“完人”(如《小腆纪年附考》作者徐鼒),有人却为之扼腕或不以为然(批评者中,不乏像黄宗羲那样的望重之士)。即如奸恶贪鄙之马士英,观其行迹,也还未到头顶长疮、脚底流脓的地步,在他脸上,闪现过“犹豫”之色。
明末人物另一显着特色,是“反复”:
昨是今非,今非明是;曾为“正人君子”,忽变为“无耻小人”,抑或相反,从人人唾弃的“无耻小人”,转求成为“正人君子”。被马士英、阮大铖揪住不放的向来以清流自命,却在甲申之变中先降于闯、再降于满的龚鼎孳等,即为前一种典型。而最有名的例子,莫过钱谦益。数年内,钱氏几经“反复”,先以“东林领袖”献媚于马士英,同流合污,复于清兵进占南京时率先迎降,可两年之后,却暗中与反清复明运动发生关系。武臣之中,李成栋也是如此。他在清兵南下时不战而降,不久制造惊世惨案“嘉定三屠”,此后为清室征平各地,剿灭抵抗,一路追击到广东,却忽然在这时,宣布“反正”,重归明朝,直至战死。像钱谦益、李成栋这种南辕北辙般的大“反复”,固然免不了有些个人小算盘的因素,却绝不足以此相解释,恐怕内心、情感或人格上的纠结,才真正说明一切。
矛盾状态,远不只见于名节有亏之辈,尤应注意那些“清正之士”,内心也往往陷于自相抵牾。例如黄宗羲,自集义军,坚持抗清,只要一线希望尚在,就不停止复明战斗:即便永历帝彻底覆灭之后,也拒不仕清,终身保持遗民身份,其于明朝可谓忠矣。然与行为相反,读其论述,每每觉得黄宗羲根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忠君者,他对君权、家天下的批判,是到那时为止中国最彻底的。以此揣之,他投身复明运动,并非为明朝而战,至少不是为某个君主而战,而是为他的国家、民族、文化认同而战。然而,他的行为客观上实际又是在保卫、挽救他已经感到严重抵触和质疑的皇权,以及注定被这权力败坏的那个人。这与其说是黄宗羲个人的矛盾,不如说是时代的矛盾。
在明末,这种情绪其实已是非常普遍的存在,并非只有黄宗羲那样的大精英、大名士所独有。细读《明季南略》,可于字里行间察觉作者计六奇对于明王朝不得不忠、实颇疑之的心曲。书中,到弘光元年四月止,对朱由崧一律称“上”,而从五月开始,亦即自清兵渡江、朱由崧出奔起,径称“弘光”,不复称“上”。古人撰史,讲究“书法”,字词之易,辞义所在。以“弘光”易“上”,是心中已将视朱由崧为君的义务放下——假如真的抱定忠君之念,计六奇对朱由崧本该一日为君、终生是君,但他一俟后者失国便不再以“上”相称。这是一种态度或评价。朱由崧在位时,作为子民计六奇自该尊他一个“上”字,然而,这绝不表示朱由崧配得上;《南略》不少地方,都流露出对朱由崧的微辞以至不屑。这是明末很多正直知识分子所共有的隐痛:虽然对君上、国事诸多不满甚至悲懑,但大义所系,国不得不爱,君不得不尊,统不得不奉,于万般无奈中眼睁睁看着社稷一点点坏下去,终至国亡。
虽然所有王朝的末年都不免朽烂,但明末似乎尤以朽烂着称。我们不曾去具体比较,明末的朽烂较之前朝,是否真的“于斯为盛”,但在笔者看来,明末朽烂所以令人印象至深,并不在于朽烂程度,而在于这种朽烂散发出一种特别的气息。
简单说,那是一种末世的气息。过去,任何一个朝代大放其朽烂气息时,我们只是知道,它快要死了——但并非真死,在它死后,马上会有一个新朝,换副皮囊,复活重生。明末却不同,它所散发出来的朽烂,不仅仅属于某个政权、某个朝代,而是来源于历史整体,是这历史整体的行将就木、难以为继。你仿佛感到,有一条路走到了头,或者,一只密闭的罐子空气已经耗尽。这次的死亡,真正无解。所谓末世,就是无解;以往的办法全部失灵,人们眼中浮现出绝望,并在各种行为上表现出来。
这是明末独有的气质,及时行乐、极端利己、贪欲无度、疯狂攫取……种种表现,带着绝望之下所特有的恐慌和茫然,诸多人与事,已无法以理性来解释。以弘光朝为例,在它存世一年间,这朝廷简直没有做成一件事,上上下下,人人像无头的苍蝇在空中飞来飞去,却完全不知自己在做什么。皇帝朱由崧成天耽溺酒乐,直到出奔之前仍“集梨同子弟杂坐酣饮”⑤;首辅马士英明知势如危卵,朝不保夕,却不可理喻地要将天下钱财敛于怀中;那些坐拥重兵的将军,仓皇南下,无所事事,为了谁能暂据扬州睚眦相向……他们貌似欲望强烈,其实却并不知所要究竟系何,只是胡乱抓些东西填补空虚。一言以蔽之:
每个人所体验的,都是枯坐等死的无聊。
然而,这时代的深刻性,不只在于旧有事物的无可救药。我们从万古不废的自然界可知,生命机体腐坏,也意味着以微生物的方式转化为养料和能量,从而滋生别的新的生命。明末那种不可挽回的圮毁,在将终末感和苦闷植入人心的同时,也刺激、诱发了真正具有反叛性的思想。
前面说到明代精神的两面性。的确,以理学、八股为特征,明代思想状态有其僵死、保守的一面,就像遗存至今、森然林立的贞节牌坊所演述的那样。但是,对于明代精神的另一面——怀疑、苦闷与叛逆,谈得却很不够;对于明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批判性以至战斗性,谈得就更不够。
很显然,历朝历代,明代知识分子的上述表现应该说是最强的。从方孝孺到海瑞,这种类型的士大夫,其他朝代很少见到。如果说明中期以前多是作为个人气节表现出来,那么从万历末期起,就越来越显着地演进到群体的精神认同。着名的“三大案”,看似宫廷事件,实际是中国古代政治史一个分水岭;以此为导火索,知识分子集团与传统皇权的分歧终于表面化,从而触发党争和党祸。从天启年间阉党排倾、锢杀东林,到崇祯定逆案,再到弘光时马、阮当道——确言之,从一六一五年“梃击案”发,到一六四五年弘光覆灭——整整五十年,明代历史均为党争所主导。这一现象,表面看是权力争攘,深究则将发现根植于知识分子批判性的强劲提升和由此而来的新型政治诉求。在此过程中,知识分子集团不光表现出政洽独立性,也明确追求这种独立性。他们矛头所向,是企图不受约束的皇权,以及所有依附于这种权力的个人或利益集团(皇族、外戚、太监、幸臣等)。
这是一个重大历史迹象。虽然党锢、党争在汉宋两代也曾发生,但此番却不可同日而语。明末党争不是简单的派系之争,也越过了“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事实上,它是以知识分子批判性、独立性为内涵,在君主专制受质疑基础上所形成的带有重新切割社会权力和政党政治指向的萌芽。若日不然,试看:
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
这是黄宗羲《原君》中的一句;还说:
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几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末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日:“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日:“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如果我们意识到阐述了这一认识的人,正是在天启党祸中遭迫害致死的一位东林党人的后代(黄宗羲之父、御史黄尊素,天启六年死于狱中),或许能够从中更清楚地看到明末的精神思想脉络。
在欧洲,资产阶级的崛起,使君权、教权之外出现第三等级,最后导致民主共和。我们无意将明末的情形与之生搬硬套,却也不必因而否认,黄宗羲在中国明确提出了对君权的批判,而且是从社会权利分配不合理的全新意义和高度提出的。
我们不必牵强地认为明末发生了所谓“资本主义”(它是一个如此“西方”的语词)萌芽,但我们依然认定,这种思想连同它的表述,在帝制以来的中国具有革命性。
末世,未必不是历史旧循环系统的终结,未必不是已到突破瓶颈的关口。尽管我们明知,对历史的任何假设都近乎于谵妄,但关于明末,我们还是禁不住诱惑,去设想它可能蕴藏的趋势。这种诱惑,来自那个时代独特而强烈的气息,来自其思想、道德、社会、经济上诸多异样的迹象,来自我们对中国历史的了解与判断,最后,显然也从中西历史比较那里接受了暗示……总之,我们靠嗅觉和推测就明末中国展开某种想象,私下里,我们普遍感到这样的想象理由充足,唯一的问题是无法将其作为事实来谈论。
也罢,我们就不谈事实,只谈假设。
人们不止一次在历史中发现:事实并不总是正确的,有些事实并非历史合乎逻辑的发展,而是出于某种意外。一个意外的、不符合期待的、甚至无从预见的事件突然发生了,扰乱了历史的进程,一下子使它脱离原来的轨道。这种经历,我们现代人遇到过,十七世纪中叶的汉民族似乎也遇到了。
那就是清人对中原的统治。
我曾一再思索这意味着什么。尽管今天我们会努力说服自己用当代的“历史视野”消化其中的民族冲突意味,但当时现实毕竟是,汉服衣冠被“异族”所褫夺。这当中,有两个后果无可回避:第一,外族统治势必对国中的矛盾关系、问题系列(或顺序)造成改写;第二,新统治者在文明状态上的客观落差,势必延缓、拖累、打断中国原有的文明步伐。
有关第一种后果,看看清初怎样用文字狱窒息汉人精神,用禁毁、改窜的办法消灭异己思想,便一目了然。在满清统治者来说,此乃题中之义、有益无害,完全符合他们的利益需要,不这么做没法压服反抗、巩固统治。但对中国文明进程来说却只有害处,是大斫伤,也是飞来之祸、本不必有的一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