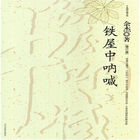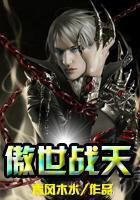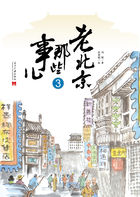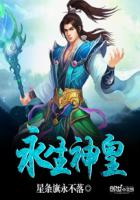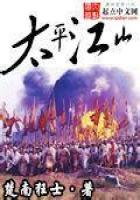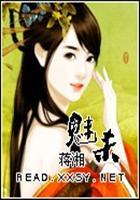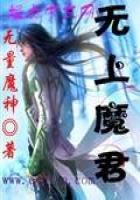巴音博罗
炊烟
炊烟是乡村的纱巾,炊烟是母亲伫立村头呼儿唤女的回音。炊烟是一首古典田园诗的韵脚。炊烟也是流传在土地深处的民间谣曲所省略的那部分。
像一幅典型的大红大绿的农民画,炊烟里的人物必然是土陶一般的质朴、木讷;炊烟里的器物必然是粗陋乃至简略,却又超越了千古时光的沧桑和厚重。同时,炊烟暗藏着牲畜们的青草气味,暗藏着无边起伏的庄稼们的苦涩、馨香和酒酿的沉醉。炊烟也蕴含着劳动的汗味与安歇的鼾声——它宽阔、明亮、河流一般流淌在村庄的四周。
太阳像一只刚出锅的金色苞米面饼子,香气四溢地挂在天边,而炊烟则是大地之神蘸着树汁一样的阳光草书的诗篇,它的主题是和谐,它的副题是宁静,它挥洒的旋律是袅袅升腾。
而月亮更似一只空而又满的民窑瓷碗,斜挂在井栏上方,如果没有炊烟这根麻绳,它如何能在千古岁月里盈盈缺缺,辉光四射?
一个人在炊烟里老了,一个人在炊烟里反复看见往昔的日子,祖先的容颜……他哭泣、忧伤,为逝去的亡灵,也为新生婴孩的稚嫩的牙齿。
花开花落,百年一瞬。炊烟是粮食的一缕香魂,缭绕在村庄上空,缭绕在青铜典籍和历史册页之间。油灯灭了,电灯亮了,犁铧打了,拖拉机来了,土炕凉了,新房立起来了。炊烟的绳索紧紧松松,仿佛人们饿了又饱,鼓鼓胀胀的腰腹——饥荒、战乱、洪涝、大旱……先人们把炊烟读了又读。当然,在新千年时的我的笔下,炊烟依然是天下苍生们的一根命脉,血液一样写在土地上空。行书,叫温饱;楷书,则叫骨架。一样凝重的古训,明明灭灭,昭示千秋万代。
唢呐
唢呐是遗失在民间的一段嘹亮无比的金质噪音。它的喉管干净、曲折,如九曲黄河穿过针眼。它纤细的身体通向粗糙的、盛装着五谷杂粮的强劲的肺——那是苦难的聚集地,是大地的忘却。在那儿,田野宽敞,阳光充沛,河流四通八达,树林郁郁葱葱,而鸟儿则把它纤巧、美丽的身体,弹跳成神灵的音符。在婚宴上,在丧期里,在丰收之夜酒盏中月亮的脸上。清郁的,深刻的,安静的,不易觉察的,它比一场疾病来得更快。它直接就抵达了人们的心灵,并把柔软的心磨砺得千疮百孔,无所适从……当抒情性质的吹奏转换成叙旧般的怀念,当呆滞的聆听者瞥见它仰天悲泣的姿态,人和乐器之间暗存的那种模模糊糊,唇齿相依的关系终于开始清晰凸现出来,仿佛一种梦境。你嗅到了它那无始无终的亡灵般的气味儿,你的灵魂便会逐渐安详,你的躯体就像一座废旧的仓库,你的血液停止了流淌……你感到它的忧伤,大喜之下的忧伤;你也感到它的快乐,大悲之下的快乐。像是永不磨钝的一根针,露出了暴烈阳光下的那种尖锐——平民意识里生活的极端部分,朴素的爱与恨的理由,也就是生存的本质,幻想的飞翔。在乡村,在四季轮回的概念里,唢呐是枝繁叶茂的桑园,泥土颜色的村落,田野间奔跑的一只狗,风俗里男婚女嫁的仪式,坟场上青了又黄的野草,寺庙里起起伏伏的诵经和香火……所以,它从一开始就取消了吹奏它的嘴唇,也取消了演奏的乐谱,律动的指尖和记录的年份。它是底层的人们一只经久不息的强健的肺,为倾诉而开花。
母亲年代的大酱
冬月里,寒霜打过枝叶,母亲坐在乍冷还暖的院子里选豆料。
整麻袋的大豆要全部摊在苇席上,像大雪封门前那金灿灿的阳光。鸡呀,猪呀,鸭呀,鹅呀都要圈好,弟弟们也不敢嬉闹造次。院子早早就被一次次清扫,连一根草棍一叶草屑也不剩。母亲蓝袄素发,系一白底碎花围裙,把圆月型的大箩筐和秫秸编的大盖帘儿一一准备齐全。
这是阴历冬月里的一个好日子,母亲一定是暗暗看过黄道吉日。但母亲不说,母亲胸有成竹面蕴微笑,只是那含笑的眉眼间含着庄穆藏着严整,这是一个令人莫名激动的日子。
母亲只选了我这个长子做她的帮手,我自然小心翼翼,因为我知晓,来年的大酱好坏香臭全在这番操作上了。
选料时要用我家最大的秫秸盖帘儿做工具。先将它倾斜到一定角度,然后用葫芦瓢舀起箩筐里的大豆,一瓢一瓢倒在直径足有一尺多的盖帘儿上,让圆鼓鼓的黄豆顺着笔直的秸秆儿缝向低处滚动。饱满成熟的黄豆粒儿就会叽里咕噜,顺势而下;而米粒和缺损残破的,不成熟圆润的就滞留在盖帘上。它们将被扣除在外,留做菜肴或用盐水腌制成咸菜,那也是乡下人爱吃的一道下饭菜。
豆料选好之后,我要赶快劈好一大堆柴,通常是抗烧抗炼的青冈柳。然后把我家头号大锅引燃。从早到晚,青烟袅袅,蒸气腾腾。我在柴禾垛和锅灶之间奔波穿梭,汗流浃背。一直到傍晚,整锅大豆全都熬成稀干相适的美丽酱色,才撤火掏灰,休憩了事。当然了,大豆是不出锅的,还要放它们在锅内闷着。母亲叮嘱家人,谁也不许掀开锅盖窥视。
第二天一大早,天刚蒙蒙亮,母亲到柴禾垛选一小捆细绒绒的茅草,回到灶房重点一把火,把锅里还在贪睡的豆子们热一下,然后趁热舀到一陶瓷小缸里。太阳刚刚爬上东边的山脊,母亲奋力挥臂,那用硬木做的杵子仿佛衣针一样在她手上灵巧地舞动着,一回一瓦盆,大约正好可成一个酱块的分量。这是凭经验和眼力算好的。捣碎,翻摔,压实,拍方方正正的一个酱块,稳稳当当放在屋中央的大梁柁上等待发酵……就这样从晨光熹微到晌午,再到日头偏西,母亲鬓角上的汗水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渐渐地,我家大梁上一排排安放起类似古代城墙的方砖一样结实、芳香、颜色暗红的酱块。
寒冬降临了,白毛风在窗棂外低低啸叫,像山野上的狼嗥狗吠。整个漫长的冬季经常是大雪封山足不出户的日子。我们全家拥着黄泥小火炉,盘膝在暖烘烘的火炕上,天南海北,讲古道今。大家似乎忘记了梁柁上沉甸甸的酱块。一直到第二年阴历四月十八,母亲才搬来木梯,净手素面,把那些“宝贝”请下来。经过一冬烟熏火燎,酱块上已尘落灰积,呈铁黑色,而且坚硬如石,但酱块里面则黄润如膏。母亲掬来清水把它们一一洗刷干净,放在明媚的春阳下晾干,然后在木墩上细细切成薄片,加上适量粒盐,重新放至陶瓷缸里。
似乎这时大酱仍处于冬眠状态,仍然没从酣眠中清醒过来。所以母亲非常有耐性,她不焦不躁,用头号铁锅烧开沸水,然后让那熟水彻底凉却,再慢慢把它们加进酱缸里。母亲小心翼翼,一遍又一遍,仿佛侍弄娇皮嫩肉的婴孩。几天之后,经过重新发酵的大酱,变得稠如米粥,色泽鲜亮醇香迷人。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是尤为关键的,稍一不慎则功亏一篑。母亲甚至像对待正要出嫁的女儿一般细致入微。每天,母亲都要选用木制的酱耙打(捣)酱,早打一百耙,晚打一百耙,不多也不少,不轻也不重,柔柔顺顺。而中午则需要打开缸盖沐晒太阳。雨天风天还要细细遮盖,不允许落进一滴生水一粒沙子。另外,母亲在缸口用细布做了一个罩子,以防乱哄哄无孔不入的苍蝇。须知,如若酱缸里被苍蝇下了蛆,那可白白忙活一年喽。
有时,母亲也在酱里放些花椒、姜、大料,但事前要用干净纱布包好。当远远地,一揭开缸盖,酱香扑鼻时,母亲会用系在腰间的花布围裙擦擦手,微合双目深深吸上一口,对我们陶醉似的说:“真香啊。”
真香!我在心里说。
……好多年逝去了,如今我们家也由乡下搬进城里,我再也没吃过那么香醇的大酱。
汗
汗是穷人的珍珠,它的蚌是劳动,它的土地是脊梁,它滚动的路途是太阳的光线。在田野里,在工地上,在那海浪一样汹涌起伏的劳动者的臂膀上,汗散发着力量的气息——健康、勃发、昂扬、宽阔……它是向上的,有一个低沉哼唱的金色号子的坡度。它引导人们团结协作,投入忘我的境界,宛如一架机器上的润滑剂,一架犁杖上套着的两头慢悠悠的黄牛——人和牲畜之间厚道温存的理解、默契,投下感人至深的阴影。汗还有锐利的镰刃。汗虽小,却包涵天地,犹如一滴海水,腥咸、湛蓝。汗的足迹是白色的——汗渍在粗布衣裳上会留下花斑和光晕。更进一步地说,汗是人体内部筋骨之间的吟唱——是一条古老的、幽暗的河流。“我认识像世界一般古老而且比人的脉管里的血液的流动更古老的河流……我的灵魂已经变得像河流一样深。”(休斯《黑人谈河流》)
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就有汗的历史。它在血雨腥风中为我们打开了叙述之门——静穆的,快活的,令人信赖的旋律,仿佛一部交响乐恢弘的乐章。它是父性的硬朗,像壮士体内的酒,散发着黯淡而雄劲的火苗。从古老的黄河源头,到幼发拉底河和尼罗河的沙岸上,汗像七彩的钻石装饰着不同肤色的人们的歌喉——沙哑的、钝重的,然而更满足的抚慰……“我坐在大地上,看着大地,看着青草,看着蠓虫,看着浅蓝的花朵。你像春天的大地,亲爱的,我看着你。”
蓝花瓷碗
在僻远的乡下,在农民家里那朴拙的灶间炕头,锅台几案,到处可见的都是那种硕大的粗瓷蓝花海碗——我整个童年时代的太阳和月亮,我母亲粗布衣襟里饱满的乳房,我记忆里最质感的优美纯净的乡下歌谣——它们在黑暗里静静地躺着。光洁的,有过豁口的,打了好几块锔子的,像那盏烟熏火燎的煤油灯,给我们一家子光亮的暖意。我曾用它盛过苞米粥、糯米饭、土豆汤、水捞的高粱米水饭;也盛过煮汤圆、粘豆包、牛舌饼和难得吃一次的白面饺子……那是一年到头三百六十五天的企盼,是一肚子苦水之后的甘醇——我生病时母亲喂我药前总是在蓝花瓷碗里盛半碗糖水,总是在蒸蒸热气的碗边嘘嘘地吹几口,而那碗里的烛光,还会映着母亲的衰颜么?当然,粗瓷的碗沿上也印着我父亲的唇印,我祖父的咳嗽,和我祖母的缺了两颗牙的悲哀的微笑……它们在漫长的岁月里碎了又圆,圆了又碎,就像清汤寡水的碗里的月光——浸过酱油的略略有些咸味的月光。它们让你的嘴巴舌头忍不住想去亲近他们,抚摸它们。在遥远的很容易让人遗忘的乡下,藏匿着它古朴浑圆的身影。一个家园因此变得更具形象,更简单,也更能把土地那宽广无边的养育之恩化解为普通的象征(我现在仍然能在碗沿上看到列祖列宗伫立眺望以及祈祷上天的身影)。当时间的变迁使蓝花瓷碗缺了又圆,空了又满,我在千年之后的某个夜晚看见的,仍然是窗棂上那只有着一个豁角的梦幻般的幻象——我祖父的,我父母的,和我自己的面容的叠影。
收割
收割使土地重新变得荒凉,在北方九月的阳光中,秋风以金质的指尖铺排下雄浑的乐章。激情的火焰,顶着每一根绵长若弦的垄沟蔓延、飞溅。镰的弯弧,马车的高歌,玉米棒子的堆积和高粱穗子的火势……温厚的土地在开阔的天空下像正在生育的妇女,敞开了她湿润而又成熟的躯体——一切都符合“质朴”的伟大意义。一切都在缓慢地流淌和汇集,像结实的、根须深埋的诗篇。
这是天地之间最古老而执着的舞蹈。几千年的农耕史并没因文明的更新和机械化的进程而有所改变。当一排排起伏的脊梁迎向酷烈的毒日,当草帽下铜色的脸膛深深俯向泥土,当丰满壮健的农妇捧起图案古朴的水罐……土地和人同时都呼吸到了醇厚而馨香的粮食气息,土地和人的血脉因为这种劳动所产生的奇异力量让融和与对接成为可能。人更像一颗颗饱满灵动的籽粒儿,闪烁着生命的品质。
但收割使土地归于安静。当浮云堆砌在天际,马车和拖拉机的车辙变得深而又深,空荡荡的田野上只剩下一片光秃秃的庄稼的短茬。这种情形将一直持续到冬季来临之后——那寒风肆虐的大地的狼藉,风雪刮走了收获的记忆,生命在封冻的河床下凄怨地诉说着。这时候即便用三弦和民歌来演奏,流淌出的也绝非欢快和浪漫。土地的哀伤将通过漫长的冬天渗入到日子的深处,农人的面孔也注定变为荒凉。
当懒洋洋的太阳在冬日积雪的山梁重新呈现,谁将眯缝的目光穿过空荡荡的原野,又一次投向更为荒凉的远方……
古庙
古庙也许是村庄的灯吧。
在北国乡下这座不足百户的小小村庄里,穿过后坡蚕场矮小的菠萝叶树来到山神庙,心情便不自觉沉静下来。风铃轻轻摇晃着,在宽敞的阳光中把声响传出很远。黑面孔的青石墙壁浸满青苔,仿佛清凉的经文。而在经年风雨中退色的匾额上的文字,又让那个面容安详,衣着和附近农人没啥区别的老僧更加和蔼可亲。
不知是谁燃起了香火,诵经的声音在屋檐下悠扬地缠绕着,像雨水滋润田野的庄稼。一个接一个的红尘中的人跪在地上,叩拜那衣衫褴褛的神,让晨钟暮鼓和木鱼激起心底的涟漪。也许善恶轮回,是人世间最朴素的哲学;也许花朵的香气让古老的美得到了慈悲性的赞颂;也许此刻那徜徉在穹窿上的一朵白云使芸芸众生相信,缥缈的天上也有注视的眼睛。
古庙在村庄的后面,千百年来已把村庄中每一户农家的变迁了然于胸。平整的青砖上那只巨大的香炉里的香火千年不灭,就像庄户人绵绵不绝的血脉。而庭院角落斜挂的那张蛛网,则在悄悄收集那些断断续续的故事。
我每次回乡下老家,都去古庙转转。古庙是村庄的灯吧,我想。有时即便在大风中明明灭灭,但是它依然靠浓浓的香火味道把远远近近,藏在大山褶皱中的农人吸引过来,向那些土里土气的传说中的神灵祷告着,使贫寒的生活重新获得温暖。
不要说乡下人愚呆,也许一块石、一头青牛、一条纠缠在一起的麻绳就成了他们生命中难解的问题。有时,也许一个微笑、一阵微风、一声鸟啼或一款月光就成了平生最幸福的事。他们会牢记一辈子的。他们那活在尘土中沙粒一样的细节,就像茂密的草丛里一只激跳出来的松鼠,凌空抓住了一枚香脆可口的松果。
当夕阳西下时,我看见那个慈眉善目的老僧正蹲在院外篱笆里的田垅侍弄菜蔬,他仿佛听见谁的一声低唤便直起腰身,拍打下手中的湿泥,挎着一筐刚摘下的新鲜的茄子或芸豆回到院里,那儿,又有一个眉清目秀的小僧为他打了一盆清水,当老僧把筋络纵横的双掌覆到水面上时,一轮又圆又大的月亮正痴痴与他对视着。
阿弥托佛——他双掌合十,轻轻叹了一句。
(原载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