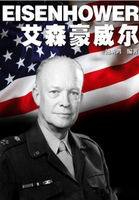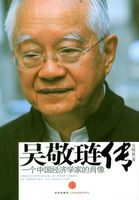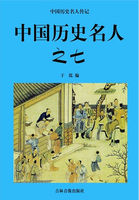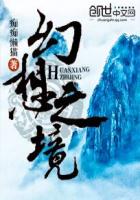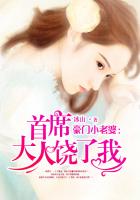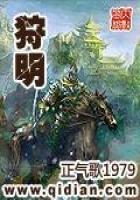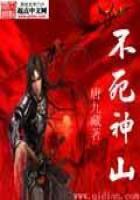引言:我与“三剑客”
1982年,《高山下的花环》以其黄钟大吕的音响报道了新军旅文学最早的潮汛,同时也昭告着一代军旅文学新人的迅速崛起。旋即,这批年轻的军旅文学弄潮儿和老一辈军旅作家一起开始向新时期文学大潮集团“冲浪”。一时间,军旅文学大纛下战将如云,捷报频飞。
整整十年过去了。
而今,军旅文坛虽然并未偃旗息鼓,但也早已没有了往日的红火闹猛;它和整个新时期文学一样,都渐由凌厉浮躁转向了沉静平和。当初那支大呼猛进的文学新军也由一个大致整齐的“方阵”而拉成了一条“散兵线”。就像马拉松长跑进入了艰苦相持的中程阶段,少数真正具有潜力和素质的顶尖选手脱颖而出,成了一马当先的佼佼者。而在这中间,莫言、周涛、朱苏进无疑是最为人瞩目的三位翘楚。
我称莫言、周涛、朱苏进为“新军旅作家三剑客”。
“三剑客”中,或如朱苏进以“耐力”见长,起步稳健,匀速行进,占据了前锋位置就当仁不让;或像周涛以“后劲”取胜,逐渐加速,后发制人,后来而居上;或者干脆就像莫言以“爆发力”而得逞,突如其来有似天马行空,留下一道奔影绝尘而去而让人难望其项背。如果说莫言的方式是不怕热闹,越热闹越刺激,越刺激越来劲,于百舸争流大潮奔涌中水涨而“船”高的话,那么朱、周的方式则是耐得住寂寞,愈寂寞愈自信,愈自信愈沉着,在几经潮涨潮落之后水落而“石”出……总之,各有各的绝招,却都以独特的艺术才华和创作实绩先后跃上了新时期军旅文学的巅峰,并且毫无愧色地步入了当代中国优秀作家的行列,为新时期文学的繁荣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而且,他们三人的创作又非常巧合地涵盖了几种最主要的文学样式:小说、散文和诗歌。或者再扩大一点视界,从大文化的角度看,他们三人也各有其典型性:莫言是一个乡村生活的新浪漫主义者;朱苏进则是新型军官阶层理想的代言人;而周涛呢,他可说是马背民族与汉民族双重文化背景熏陶出来的歌手。因此,选定他们三位进行一番平行展开式的比较研究,做一点传记和心理批评,探讨一下他们的创作道路、个性及风格,客观公允地评价其过去,心平气和地分析其现状,实事求是地指出各自的优长和局限,其意义恐怕就不拘囿于“三剑客”本身或者青年军旅作家群体乃至一般军旅文学运动的范畴了。
当然,我之所以比较自信地敢来评说他们三位,还有一个私下的原因,即作为朋友,我对他们都比较熟悉—我和朱苏进同为原福州军区的炮兵,相识有近20年的历史;莫言成名前后,我们同窗两年,也可算得是朝夕相处了;与周涛见面最晚(1986年),却也是气味相投,一拍即合,倾盖如故,相见恨迟—“熟知”就带来了解和关注,睹其文思其人,见其人想其文,互为观照和印证,就有可能做到像古人所说的“知人论世”。譬如,据我观察,这三位的个性都是卓尔不群而又迥然有异,周涛是直率狂放,朱苏进是孤傲矜持,莫言则奇诡莫测……
举一个小例子。
约五年前,当我最初认定“三剑客”时,有一次亲口把这个看法告诉了周涛。他听完之后,立马眼放精光,郑重地伸出一根手指,在我的鼻尖上方一点一顿地说—“我非常赞成你这个看法!”当即令我心中大呼:“除了周涛,谁能这样?若不这样,又怎是周涛?!”
我没有就“三剑客”问题和莫言、朱苏进交换过看法。但这并不妨碍我推测一下他们的“即兴反应”—
莫言可能会撇一撇嘴,撇下两个字:“狗屎!”
朱苏进则有两种可能,或者矜持地笑而不语,或者舌尖轻轻一弹,吐出一个反问:“是吗?”—是吗?信不信由你。
但是,你却尽可以据此回忆一下你所认识的“三剑客”其人,或者你所曾读过的“三剑客”其文和那字里行间蹿动着的那一股子“精气神”。
现在我想的是,面对这样的“三剑客”,我们的讨论有没有可能变成一件既富于意义而又不乏情趣的事情呢?
试试看吧。
莫言:爆炸在1985
相比较周涛、朱苏进,莫言更年轻,起步也更晚,成名也更晚。但他的成名方式是“爆炸”型的,他以强大的爆发力在1985年竞相攀登文学高峰的拥挤山道上突然蹦了个高,一下子就冲上了制高点。他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漫不经心地就撼动了整个文坛。《透明的红萝卜》在1985年第1期《中国作家》发表时还悄无声息,并没有引起什么轰动效应,但它在“圈子”里却顷刻间不胫而走,为李陀、阿城等诸多有识之士所津津乐道,并被视为一个重要作家诞生的重要信号。年底,张洁在联邦德国答记者问时郑重而欣喜地宣布:如果说1985年的中国文坛发生了什么大事的话,那就是出现了莫言!
支撑张洁这一判断的当然不止是一个《透明的红萝卜》。继此之后,莫言连续推出了《金发婴儿》、《球状闪电》、《白狗秋千架》、《枯河》等一批中短篇佳作。在这一系列农村题材作品中,他坚持以冷峻严谨的现实主义为基调,以宏阔丰厚的民族文化为背景,糅合点染外域现代小说艺术的多种色彩,狂放不羁地为中国农民写意抒怀,向人们提供了一幅北中国农村生活的内容丰繁厚重、形式新颖斑驳的立体画轴,使他在1985年的小说新潮中异军突起,标领风骚。他于同年第12期《人民文学》上发表的中篇小说的题目就极富寓意—《爆炸》—既为1985年出现的莫言现象做了一个总结性的命名,又为1986年即将到来的莫言高潮做了一个谶语式的预言。
1986年对于中国当代小说来说,无疑是一个和1985年具有同等分量的重要年份。它的重要性不仅表现为一批优秀小说成果的持续丰收,更表现为对传统小说策略的深入反叛和颠覆。《红高粱》就是这场小说革命深入发展中一枚瓜熟蒂落的硕果。尽管就我个人的喜好而言,无论过去还是今天,我都更加珍爱《透明的红萝卜》、《白狗秋千架》里的那一分清新纯朴和自然天成,但是我仍然清醒地看到,《红高粱》才是更重要的。《红高粱》具有多重的意义。一方面,以《红高粱》为发端,标志着历史战争题材的新的战线的开辟,直接引诱了一批没有战争经历的青年军旅作家写出自己“心中的战争”(如乔良的《灵旗》,苗长水的“沂蒙山系列”,张廷竹的“国民党抗战系列”),并以此和“当代战争(南线)战线”、“当代和平军人战线”鼎足而三,最终形成了新时期军旅文学的基本格局和全面繁荣。另一方面,《红高粱》以当代意识和审美理想之光烛照历史,通过对生命伟力的张扬和对民族精神的呼唤,为今天我们重铸民族性格提供了一种参照。这种对民族历史母题重新开掘与处理所产生的积极影响,远远超越了军旅文学的既定范畴。还有一点也许更现实也更“有用”,即从小说的纯技术角度看,《红高粱》的出现适时地为开始有些疲惫的小说革命运动注入了一针兴奋剂,使之焕发出了新的活力。这不单单是说《红高粱》找到了一个传奇故事、地域文化与外来技巧三结合的成功范式,而更在于莫言在这个范式中将他此前作品里已初露端倪的“灵活多变的叙述方式、随意开放的结构方式、披头散发的语言方式、奇异超人的感觉方式”做了一次非常极端然而又十分和谐的集中展示。或者反过来说,正是由于《红高粱》才使莫言的小说风格更极端化从而也更个性化了,《红高粱》将莫言塑造成了一位凌厉狂怪的小说革命的前锋。这位前锋对中国小说界造成的震荡与冲击是严重而深刻的,他在《红高粱》里所贡献出来的崭新的审美经验对当时的读者和作家们来说都有“挡不住的诱惑”,以致一时间很少有人能完全抗拒莫言或不谈论莫言。
当然,再换一角度看,1986年的中国文坛正迎着八面来风,各种外域现代小说艺术之风把我们已经紊乱的“风向标”吹得旋如转篷,不少小说家因此心慌意乱心无定数而随风飘荡。当此之际,莫言既得风气之先而又毫不动摇地坚持“根本”,敏锐及时地将外域现代小说艺术与民族本土文化做了一个巧妙的沟通和“嫁接”。所以,更恰切地说,莫言只不过是适逢其时地起到了一个中介或桥梁的作用。他成功在此,贡献在此,影响亦在此。譬如他对福克纳铺排恣肆执著纠缠的语言文体的领悟,用现代意识与技巧处理乡土题材的“邮票意识”的移植,对博尔赫斯幻象形式下超验性体验方式的把捉,对西蒙崇尚的生命感觉(或曰生理感觉如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嗅觉以及“通觉”)的张扬,对马尔克斯充满魔幻色彩的颓败家族历史主题的追寻,等等,都为他的同行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再说得具体一点,甚至可以这么认为,正是因了莫言对“感觉”夸张变形的极致运用,才启迪了一大批中国作家,打开了他们钝化已久的新鲜陌生的感官世界,进而丰富了他们对外部世界和人类自身的感知方式与审美方式。但是,天才的仿效可以化为神奇的创造,拙劣的模仿却永远只能是东施效颦。从这个意义上讲,莫言骤然间散发出来的奇异强光在照亮一批人的同时也灼伤了一批人(包括莫言的自伤)—“伤”之于对那样一种极端夸张的语言方式、感觉方式甚至是一种公式化的叙述视角(如“我爷爷”、“我奶奶”)的套用和滥用。但无论如何,在整个新时期以来的小说进程中,莫言的冲击力和影响力都是罕有其匹的。我这样的判断等于指出,莫言是新时期军旅作家中的天之骄子,更是新时期小说革命的杰出代表。
莫言:高粱地里的精魂
新时期以来,在广阔的乡土题材上用力最勤收获最丰的主要有两类作家,一是所谓“右派”作家,二是所谓“知青”作家。(试想想,从高晓声的“李顺大”、“陈奂生”到贾平凹的《浮躁》、张炜的《古船》,其间其后有多少佳构!)这两类作家不管其时代遭际多么迥异,以及由此所决定的创作的价值取向和审美风范多么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熟悉当代中国的农村和农民,原因就是他们都或长或短地当过一段时间农民。这一个共同点同时也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他们都仅仅是当过农民,他们原本都还不是农民。他们过去不是农民出身,今天也早已跳出了农民的圈子,和农民拉开了相当的距离。因此,他们对农民的回忆与审视、剖析与塑造,就难免会带上一些“局外人”的视角与眼光。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莫言和他们区别开来了。
莫言是农民。(当然,广义而言,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是一个农民的汪洋大海,往谁家上溯三代两代,又有多少人敢说自己不是农民呢?但我这里是就狭义而言。)莫言过去是地道的农民出身,今天仍然和农村保持着血缘的、亲情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他在一间黑黝黝的土炕上呱呱坠地,到他“满脑袋顶着高粱花子”步入现代军营,其间整整20年光阴,他在山东高密东北乡那无际无涯的高粱地里嬉耍长大,耕作与收获(他小学五年级辍学开始习农)。这是一份沉重的人生履历,也是一笔丰厚的文学矿藏。仅以此而论,莫言在当今一大批来自土地又跳出土地最后再去反观土地的“乡土作家”(不仅仅是“右派”和“知青”两类)中也显得是富有而独特的。他不是在高粱丛中采花酿蜜的蝶和蜂,也不是在高粱地里孵过一两窝蛋的候鸟;他就是一棵高粱,是从那块土地中长出来的,他就是一粒土坷垃,和那片土地融为一体。或者干脆说,他就是受孕于那块高粱地的日精月华风霜雨露孕育而成的一个精灵、一缕游魂。他生长于斯,飘荡于斯,吟唱于斯。对于发生在这土地上的一切的一切,他都“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他的全部的歌唱就是这块土地全部的苦难、光荣与梦想。
如果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这块高粱地对莫言的精神影响甚至可以说是先定的。这主要指的是“非典籍文化”(非文字文化)的浸润,是北中国那块特定地域所独具的乡风乡情、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民间艺术、神鬼传说、生产方式和生产景况等共同组构的文化背景所形成的定向遗传。也就是说,那儿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个传说、一首民谣、一窗剪纸、一台村戏、一声号子、一缕炊烟、一点鬼火、一头牛犊、一条猎狗……都与当地的历史、人生具有某种别样的关联,它总是精心地保留着恒久的以往,并始终不渝地培植着未来,对这方水土上的人们像“润物细无声”的春雨般年复一年地进行着文化的浸淫与渗透。莫言作为一个受动体,还远在他成为作家之前就开始承受着这种文化的潜移默化,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领悟,一种天人合一的“胎教”,一种艺术创造的超前训练。他日后的文学母题、风格、情调和景观的形成与凸显,都不过是那种深长的文化积淀的外化罢了。“汪洋血海般的红高粱”和那“苦涩微甘的薄荷气息”浸透了莫言的灵魂,它们总有一天会在莫言的眼前辉煌起来,从莫言的心灵中荡漾出来,而成为莫言艺术世界一种悠长的情调和氛围。莫言深爱着这片土地,无论它是美丽还是丑陋、辉煌抑或暗淡。这是莫言文化的根之所在、艺术的魂之所系。明乎此,我们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在1985年蜂拥而至的外域小说大师中,莫言特别地对福克纳和马尔克斯这两位“小老头”情有独钟?—福克纳的“邮票说”对莫言的启迪是显而易见的,而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和马尔克斯的“马孔多小镇”对莫言营造“高密东北乡”的参照意义同样是不言而喻的。①从这个意义上说,莫言拥有这样一块饱藏了独特文化意蕴的“高粱地”是上苍对他的恩赐。
莫言是幸运的。
莫言又是不幸的。
说他幸运,是说他作为数千年来中国农民文化(即乡土文化,主要是“非典籍文化”)的天然产儿,因了高密东北乡那块高粱地的摇篮的滋养而发育得特别的健壮。说他不幸,则是说他作为当代中国农民的一分子,其现实生存景况的窘迫和艰难给他童年和少年的心灵烙下了无数痛苦的印记。莫言出生的50年代后期,刚刚从封建制度下解放出来的中国农村又陷入了政治风浪的颠簸,从“大跃进”、人民公社到批“三自一包”、割“资本主义尾巴”直至“三查”、“四清”、搞“文化大革命”,农民在政治上反复被愚弄,经济上不断被剥夺,发家致富的梦想终成泡影。在这种情势下成长起来的莫言自然难逃厄运。还在少年时期,他就遍尝各种野菜,未及成年便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其间种种惨痛的经历在他早期作品(如《枯河》、《白狗秋千架》、《筑路》、《透明的红萝卜》)中都有着最真切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