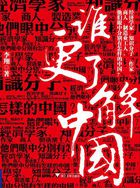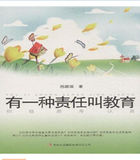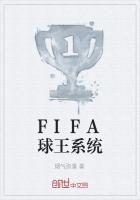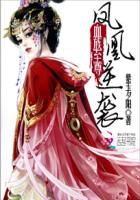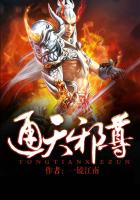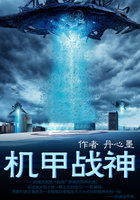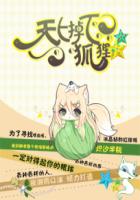正如有的学者指出:“中国近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规范、问题意识、理论框架甚至叙述话语,基本上是从西方引进的,是西学东渐的结果。”张国刚:《二十世纪隋唐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148~170页。族群研究就是在广泛吸纳西方的族群理论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的基础上兴起和发展的。同时,国内大量的族群研究,除运用人类学理论外,同时也在民俗学、历史学、文学、社会学、政治学、统计学等学科理论的背景下完成的。上述这两个背景让我们在未来的研究中要面对这样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协调好以西方文明模式发展起来的族群研究与中国本土化解释体系之间的关系;二是如何将多学科的理论方法更好地应用于中国族群研究。与这两个问题相关的,是我们可能要坚持在两个方面继续做工作,一是族群的实地调查和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出版,如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编辑出版的《瑶族双寨》等四本民族调查报告(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和即将出版的《贵州荔波水族》等六本民族调查报告集等,虽然人类学系的师生为此辛苦劳顿,但却造福学界,遗泽后世;二是对于国外族群体论和研究的相关著作的翻译出版,尽管近年来的翻译著作中有许多令人遗憾的问题,但我们还是要看到它们对于国内学术界发展的积极影响,特别是对青年学者的开阔思路和增强问题意识起了很大作用。
族群研究的魅力来自于其以人为本的学术关怀。传统中国的变迁虽然快速,并取得瞩目的成就,但同时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群也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变故,从环境污染到诚信衰微。这都促使我们今后的研究,要更着重与具体人群的活动,关注人群,把人的活动放在历史与现时舞台的中央。族群研究,应保持人类学学术研究的人文关怀。
我们所要继续的族群研究,还要加强应用实践性。族群研究的应用实践领域从主题上讲非常广泛,涉及人地关系的调适、自然资源的保护、社区综合发展、移民、妇女生活状况等,应用实践所涉及的地域从阡陌乡村到都市。自2000年以来,我主持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中国族群研究中心与世界银行合作的一系列项目,同时也与绿色和平组织等国际NGO以及中国政府合作了一些应用项目。这些项目涉及农村的项目涵盖了江西、安徽、云南、广西、贵州、湖南、四川、甘肃、新疆、黑龙江、青海、宁夏、重庆和西藏等十几个省市,所关注的主题主要是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妇女、移民等方面。任何研究都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以理论来指导实践,在实践中发展理论,才能使研究充满活力和发展空间。
解构中国少数民族:去东方学化还是再东方学化
潘蛟
自1990年代以来,分析中国的民族识别,解构中国政府对其境内少数民族的构建在西方业已成为中国研究的一个知识增长点。与此话题相关的专著和论文接二连三,先后被拆解的已有回(Gladney,1991)、彝(郝瑞,2000)、壮(Kaup,2000)、苗(Schein,2000),瑶(Litzinger,2000),维吾尔(Gladney,2004)等少数民族。至于什么时候会拆解到像藏、蒙古这样的民族,或是否已认为没有必要再逐一拆解余下的49个少数民族,不得而知。
大致讲,上述解构风潮的进路有二:(1)揭示这些民族内部在语言、文化、社会经济和地域分布上存在的差异和非连贯性,由此揭示,尽管中国政府/民族学家声称他们按照斯大林的民族定义科学、客观地认定了中国的少数民族,但这些被识别出来的民族却没有一个符合斯大林的科学的民族定义。(2)分析这些人群演变成民族的历史或过程(ethnogenesis,或ethnicprocess),由此指出,在被中国政府认定成单一民族之前,这些人群既没有统一的族称,也没并共同的族群意识,从而也不像是西方学界一般所称的单一族群(ethnicgroup或ethnos)。
由此进而推及的结论是,中国的少数民族是中国政府通过民族识别发明创造出来的。无论是斯大林的民族理论还是西方的族群理论都不能解释中国少数民族的存在,因为这些理论都忽视了国家对于这些少数民族的构建(Gladney,1991,p.76)。
民族既不是超自然的上帝创造的相互分离的人群,也不是自然形成的不同人们共同体,它不过是近代人们在这个充满异质的世界上所作的同质政治构建;是民族主义发明创造了民族,而不是民族生成了民族主义,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学界在民族主义研究中形成的主流观点(格尔纳,2002;凯杜里,2002;霍布斯鲍姆,2000;安德森,2003)。
民族政治是一种同质政治,民族建设(nationbuilding)过程是一个在充满异质的现实中进行同质梳理、归类和构建的政治过程。这个同质构建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制造“他者”的过程,因为只有在想象、构建“他性”和“他者”的同时,“我们”的同质性才得以浮现和确立,从而民族政治也是所谓的“他者政治”,即,一个民族的构建、团结和存在需要不断想象和制造“他者”,否则它将涣散、消解于它内部包含的区域、阶级、性别、年龄、偏好等异质之间的张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Williams(1989)指出,所谓少数民族实际上是民族国家在想象、构建其自身同质性的过程中挑剔出来的杂质,制造出来的“他者”。在民族建设过程中,主流人群推论的或真实的共同世系和文化制式被当作了立国的根基,弘扬光大这种世系和文化成了国家生存和奋斗的目的,具备这种世系和文化特性的人群成了支撑这个国家的脊梁。
与此同时,那些在世系和文化有别于主流民族的人群则被异类化(alienated),被当作有碍于这个民族国家同质整合和进步的杂质。面对这种情况,这些被异类化的少数人群或者会起来诉求自己的民族国家,或者会竭力证明自己也是良民,也曾在历史上为这个国家抛撒过血汗,自己的传统和文化不仅不会有碍于,而且会有益于这个国家的整合和进步,并借此来诉求国家的政治承认。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少数民族会来竭力装点、发扬自己的传统。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民族虚荣,倒不如说是为了摆脱自己遭受的民族歧视。他们实际上是被迫通过发扬自己的传统来证明自己不仅无碍于,而且有助于这个国家的文明和进步。然而,在主流人群看来,这些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无论怎样被装点和发扬,至多也不过是一些可以用来点缀这个国家的花边和羽毛而已,它们永远不可能是可用以构筑民族国家大厦的基石和砖瓦。据此,Williams认为,这些少数民族装点、发扬自己的传统文化实际上是在被迫向这个民族国家偿还一种他们不曾亏欠而且也永远无法偿清的债务。
看上去,近年来对于中国少数民族的解构始于上述主流理论的指引,终于对它的确认。但在我看来,这些解构的意涵与其说像是在于确认上述民族理论,不如说像是在坐实(reifying)对于“威权中国”的想象和指控。对于中国案例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也与上述理论形成了抵牾和挑战,他们好像没有太大兴趣。例如,对于存在于Williams的“少数民族欠债说”与新中国领导人的“汉族还债说”(周恩来)之间的反差,他们不仅不曾做过分析,甚至根本就没有注意。对于上述民族理论的搬用也有些跑偏。例如,在Williams的理论中,那些少数民族毕竟仍是能就其遭受的“异类化”做出回应的行动主体,但在这些中国专家的笔下,中国的少数民族却是几乎任凭国家构建的客体。虽然一些人也声称应该把中国的民族关系看做是一种动态的对话和商榷过程,但在他们述及对话和商榷中,却只有1949年以后的少数民族识别,没有1949以前少数民族应对中华民国建设而产生的政治承认诉求;只有国家的民族政策对于中国民族景观的塑造(少数民族人口在全国总人口所占比率的起落,等等),没有少数民族自身权利诉求所促成的国家民族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只有主流人群通过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猎奇或“内部东方化”来对自身的确认和构建,没有少数民族通过强调自己与主流人群的文化差别或“自我东方化”来对国家特殊政治安排的诉求,等等。
应该指出的是,他们解构中国少数民族政治构建,并不是因为他们觉得没有民族识别也就就没有中国少数民族。与此相反,在他们看来,如果没有民族识别,中国的少数民族至少会是400多个而不仅仅是55个。在他们看来,中国55个少数民族的构建过程本身也可以被看作一个族群灭绝过程(Gladney,2004,pp.9,205-228;Hattaway,2000,p.xi)。在西方自由主义看来,由自己来定义自己是谁,这应该是人的基本权利,而国家通过所谓“科学客观”的民族识别来否定400多个人群对于自身的认定,这正是威权政治的具体表现。而且,中国的民族识别实际上既不科学也不客观。如果说它的确也有什么特点的话,那也就是它把人们的出身、家系、血缘当成了认定民族身份的依据(Gladney,1991;2004),而这也正是所谓的“族裔民族主义”(ethnicnationalism)的主要特征。
“族裔民族主义”的所指出于它与“公民民族主义”(civicnationalism)的对举。一般认为,公民民族主义发源,并主要流行于莱茵河以西(包括英美)那些资本主义发展较早,资产阶级较成为成熟的国家,因此在早期的一些民族主义研究文献中(Kohn,1944)也被称作“西方民族主义”(Westernnationalism)。它倾向于把民族看做是自愿生活在共同法律之下,被同一立法机构所代表,能对自己的政府做出安排的人群(凯杜里,2002,p.7.Smith,2000,pp.5-26)。这意味着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政治意愿来选择自己的民族归属,能够自己定义自己是谁,因此也被称作“志愿的民族主义”(voluntaristnationalism),或理性的,良性的,自由的民族主义(liberalnationalism)。与此不同,族裔民族主义把民族看做是具有共同起源/祖先从而也具有共同文化的人们共同体。这意味着一个人的民族归属是生就的,不可选择的,从而也是封闭排外的,因此,与“志愿的民族主义”并置,早期的一些研究者也把它称作“有机论的民族主义”(organicnationalism),或非理性选择的民族主义。早期的研究者认为,这种民族主义发源、流行在莱茵河以东,即,中欧、东欧以及稍后的亚洲和非洲地区,因此,与“西方民族主义”对举,也称之为“东方民族主义”。由于这些地区大都是在帝国贵族和半封建地主统治之下的农业社会,它的民族运动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主要是由少数城市精英牵引,因此它具有“尖啸、极权和神秘主义”(Smith,2000,p.7)等特征。
参照上述理论,把中国的民族识别称作族裔民族主义的构建,这显然是意指它具有“有机论”,原生论,神秘主义,极权主义,非理性,非公民社会性,非自由民主等性状,而这些性状似乎也是由中国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或由它的神秘的东方性决定的。
然而,在今天,采取社会发展阶段论来说事似乎早已过时,取而代之的是文化决定论。这也就是说,在今天,一些人更愿意把发生在中国的事象归因于中国人所持的“人观”或中国文化特性,而不是归因于它实际所处和必须应对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情状。
值得注意的是,自199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对于中国民族观念的论断也有一个戏剧性的转变。在这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传统中国被认为是一个奉行天下主义或文化普世主义的国家,即,它不以种族/血统/出身为政治畛域,信奉的是“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是怀”之类的儒家普世主义。即便不时也有夷夏之辨,但那也仅仅是把夷夏之间区别看作“礼”或文化上的差别,而且认为夷夏之间的界限并不是不可化解和转换的。因此,发生在近代中国的种族或民族主义至多不过是从西方搬借过来的利器或糟粕。
然而,自1990年代以来,这种看法受到了挑战。例如,DruC.Gladney(1992)把支撑中国民族识别的话语称作“族群民族主义”。他认为,尽管中国的民族主义话语是经由日本传入的,但它杂糅进了“家”、“族”、“人”、“人民”“土地”、“本地”等中国人固有的观念(2004,p.xii)。FrankDikotter认为,种族主义在中国实际上具有相当深厚的传统。比西方种族观念糟糕的是,传统中国倾向于人类起源多元论,习惯于把夷夏之间区分看做是人与禽兽之间的差别。西方的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迅速播撒开来,主要是因为它与中国人注重家系和血缘关系等传统相契合。总之,把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文化差别血统化,种族化,把不同的民族想象成具有不同遗传特性的生物学实体,这在中国有十分久远的传统。然而,当人们在不断清算西方种族主义造下的种种罪孽的时候,却忽视了中国和东亚的一些国家一直在把种族化的归属感当作起民族认同的坚实基础(Dikotter,1997,pp.2-5),以致这些国家至今仍有许多鼓励种族歧视和违反人权的官方政策没有得到清除。例如,黄帝被当作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中华民族仍被当作永不褪色的黄种;借助优生学剥夺公民的结婚生育权利(甘肃);对黑人留学生的歧视和群殴(南京),等等(Dikotter,1992;1997,pp.1-33)。由是观之,把家系、血统当作民族识别的依据更是可以被当作“把民族种族化”的有力指证。
简言之,把中国民族识别当作族裔民族主义建构是与近年来对于“中华种族主义”的指控是相呼应的。除了坐实对于极权中国的想象和指控之外,解构中国少数民族还有坐实对于中华/东亚种族主义的想象和指控之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