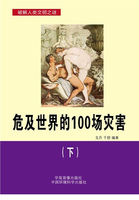众人离了邺都,虽是各怀心思,但都想尽快远离邺都,虽不同心,却是同力。
吴鸭嘴、陈氏兄妹、柳家二仆都熟悉路途,大家群策群力,晓行夜宿,一路上虽舟车劳顿,柳刚柳城也有些傲慢无礼,好在有柳琪居中调停,虽有些摩擦,但都无伤大雅。众人行进速度却是丝毫不慢,才只三日功夫,已经到了太行八径之一的滏口陉。
刘广平看此地山高沟深,滏口古道蜿蜒曲折,连接着并州和冀州。据柳琪说,这里是有名的兵家必争之地,他虽然不通历史,但是看这地势,放眼前去,一条羊肠小道出没于层峦叠嶂之间,与前两日所行的大道坦途截然不同,他也觉得十分险要。不过他无暇想这些,令他更欢喜的是,终于远离了京城,心里绷紧的弦终于松了下来。
吴鸭嘴看他有些松懈,小心的提醒着他:“此去河东,不过是走了一成半的路程,且是最易走的路途,接下来山高路险不说,太行山上更是盗匪山贼出没之地,咱们要做好准备。”
柳刚却得意洋洋地接过话来:”对你们来说自然是难走,可对我柳家来说却处处是通都大邑,我家主人在沿途郡县皆有朋友,早已经修了几封书信,只要交予他们,自然有人护送我们,你们若是想走的容易些,可得好好求求我家小姐。”
柳舒妍为人倒算宽和,不似寻常贵族仕女骄横无礼,这几日虽然多在马车之内,但偶然相见,对刘广平的部下也算彬彬有礼。虽然一面对刘广平,却总是冷言冷语,把他当成登徒浪子,刘广平看见嫌隙已生,自己在宫中给她留下的形象已经不可磨灭,也只能徒唤奈何。现在听说大家要分道扬镳,真是正中他下怀。
于是接过话头说道:“既然如此,咱们就此分道扬镳吧。”
柳琪展开地图,详细的看过,才思虑重重的说道“此去并州,碰到的第一个郡便是上党郡,此处距离上党郡还有两百多里山路,六七日的脚程。一路上还需刘兄的人马保卫,方能安全抵达。”说着白了柳刚一眼。
陈元芳更是不屑:“这太行山,路险沟深,你们这马车是行不得的,只能下车步行,我怕你们家的娇小姐受不了,到时候哭鼻子,就只能抱着你们家的宝贝书信哭了。”
柳刚这一上来就讨了个没趣,他面子上过不去,他在柳府也算老家人,寻常奴仆都要给他几分面子,陈元芳这样大小的丫头,到他面前大气都不敢出,如何能受得了这点气,正要教训她。
忽听得车里传来银铃一般的悦耳声音。“我这几天在车里憋闷的很,正想跟姐姐说说话呢。”只见车帘一挑,柳舒妍从车里探出身子,慵倦的伸个懒腰,笑吟吟的说道:“姐姐可不要嫌我烦人,我在马车之内可是憋闷坏了。”
柳舒妍一出马车,顿时艳光四射,一众男人都看得眼睛直了,陈元芳一看是她,想起来自己和刘广平在宫中被她撞见,不由得脸上飞起了两朵红云。
柳舒妍却不理会他们,款摆柳腰,行至陈元芳身前,伸手挽住陈元芳的手臂,喜笑颜开的奉承道:“我这几日只在车中听见姐姐的声音,就猜想姐姐定是个大美人,看来我猜得一点也不差。”其实她早已认出来陈元芳就是那个与刘广平行“苟且”之事的宫女,但她故意不点破。
陈元芳见她没有认出自己,心里一块石头这才落了地。她本就心性单纯,又是直来直去的脾气,柳舒妍既肯屈尊放下身段,她也顿时就把刚才的怒气抛到了九霄云外,又看柳舒妍生的俊俏可爱,登时就喜爱上了八九分,于是挽住了柳舒妍,女人的友谊总是来得迅速,两个女人这就说起了体己话。
柳琪和刘广平却都在心中不由得暗自赞叹,此女把握人心的手段真是炉火纯青。
几人在滏口关休整了一日,弃了马车,又买了几头毛驴,供几个妇孺乘坐,众人备好干粮衣物,这才进入了太行山区。
刘广平和乌鸦嘴带着挑选出来的精壮在前面开道,其余的十来个人由陈元芳带领,护送几个孩子和柳府中人。
柳琪看身侧一边峭壁如刀,一边深谷幽幽,远处山峦起伏,太行山果然名不虚传,不由得叹道:“太行之路能摧车,今日一见果不其然。”
柳舒妍骑在毛驴之上,装着胆子,探身网身侧的谷底看去,谷底之中,似隐约可见牛马的白骨和车辕的残骸,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行旅客商埋身山谷,足见太行之路行路之难。她赶紧收回目光,不由得吐吐小舌头,细细品味着柳琪刚才所吟的诗句,叹道:“太行之路能摧车,只是平平七字,却道出了多少艰辛。若不走过这样的道路,自然不知道这七字的艰难,今日身临其境,哥哥吟出这样的诗句,足见才华横溢,但妍儿细品这句,当是上句,请问可有下句?”
柳琪老脸一红,这诗句本是白居易的诗,可是这本是唐代才有的诗句,出现在晋代,只好硬着头皮冒认了。他厚着脸皮说道:“确实是我所作,下句却是若比卿心是坦途。”
柳舒妍不由得羞红了脸,长久以来,柳琪对她的爱慕之情,她蕙质兰心,怎么会不知道,但是他们本是同宗,虽然没有血缘,在这个时代却是礼教大防,这种感情是她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她微微有些愠怒,但还是忍住没有发作,细细思索片刻,说道:“虽然此句也是不错,不过终究过于小家子气,实在不好,妹妹虽无才学,试着对一句,男儿驰骋若坦途。”
柳琪也是聪明人,看她脸色不虞,在妹妹两字上故意加重了语气,猛然省得,自己无意吟出的刚才那句,虽是由衷而发,却是过于唐突了,不禁也有些尴尬,柳舒妍故意对这一句,是想让自己收回不切实际的想法,建功立业,他想解释,又怕越描越黑,只好说道:“愚兄才智短浅,还是妹妹对的好。”
柳舒妍也不应答,只把脸别过去跟陈元芳说话。柳琪也觉得无趣,陈元芳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也有一搭没一搭的应着柳舒妍,饶是柳舒妍聪慧,也没了话题,一时气氛有些尴尬。
行得半日,队伍渐渐出了狭道,路途虽已宽阔,但依旧崎岖不平,柳琪打眼望去,前方群山高耸,奇峰插对,也是险恶去处。
这半日他和柳舒妍还是没有说话,气氛依旧尴尬,忽然柳琪听见几声呐喊,所乘骏马惊了一下。就见一个半大孩子从前方匆匆跑来,边跑边喊着:“有强盗,有强盗。”
众人一听大惊,柳琪勒住缰绳,问道:“到底怎么回事》”
那孩子听得柳琪发问,喘着粗气回禀到:“前面有一伙强盗拦路,刘爷让我通知大伙做好准备,来几个人,把武器拿到前面。”
当初大家为了避人耳目,把武器都驮在几个走骡背上,伪装成货物模样,只有刘广平乌鸦嘴和陈元礼带着佩剑。
柳琪一听,赶忙命人取下武器,送到前面去。
刘广平率领二十多名刘家军正与百八十个强盗对峙。这伙强盗虽然都穿得衣衫褴褛,手里拿着明晃晃的刀枪,有几个没有武器,也拿着头镰刀之类的农具,为首的一个强人,虽然不高,但是十分结实,是个车轴汉子,两臂肌肉虬结,头上裹着半蓝不绿的头巾,上身穿着蓝绸短襦,显然是抢劫得来的,下身跟群盗一样,穿着一件满是窟窿辨不出颜色的裤子,手里提着把钢刀,正嚣张地叫着:“快放下财物,俺张铁须可以饶你不死。”
这时刘广平才注意到这贼首,三十来岁年纪,一脸连鬓胡子,须黑如铁,虽然装束可笑,这一脸黑须倒是给他平添了几分威严,他旁边还有一个三十来岁的秃子,说是秃子也不是秃子,只是已经谢顶,只有周遭还有些头发,头顶几乎是个光蛋,胡须也只有上唇稀疏几根,脸色黄白,有些瘦削,给人一种奸黠的感觉,他手里没拿着武器,刘广平推测应该是强盗中军师一流的人物。
刘广平和乌鸦嘴刚才已经偷偷让一个孩子回去报信。这时候见强盗人数众多,自己这边孩子居多,而且手无寸铁,只能想办法拖延时间。
他不知道这个时代强盗怎么称呼,只好硬着头皮学着影视剧里的样子,在马上拱拱手,向张铁须施礼:“好汉,在下久仰大名,今日一见名不虚传。我们都是买卖奴仆的商人,这财物都换成了这些小奴,实在没有多少钱财,还请好汉放过我们吧。”
那张铁须瞪圆眼睛,怒喝道:“休想骗老子,妈的你们都是客商,怎么会没钱,再装没钱都把衣服脱光,老子一刀一个,都砍了煮汤锅,也给兄弟们开开荤。”
他这么一说,手下的强盗顿时眼里都放光了,一个个眼睛绿油油的,跟饿狼一般。.
吴鸭嘴一看激怒了他,赶紧假装害怕,陪着笑脸说道:“大爷,大爷,消消气儿,这买卖是我们四个人的,还有一个在后面,钱财都在他那里,容我们商量一下可好?”
张铁须牛眼圆睁:“他妈的,还想哄骗老子,来人呐,给我把他们都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