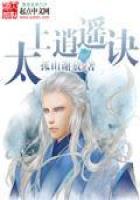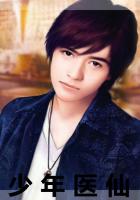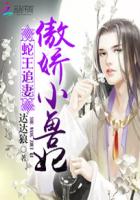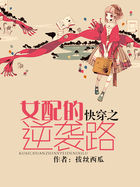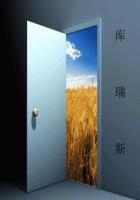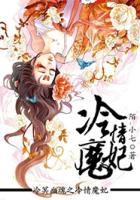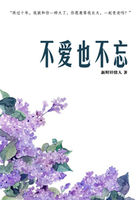纤指轻弹,如百年前江南郡的传世美女西施于若耶溪浣沙,比那水波更潋滟;玉唇轻启,真如一莺儿清鸣,曲调悠悠,余音袅袅,好似能绕梁三日不休。
一曲踏歌谣不长,钱莺儿声情并茂地唱完已是泪流满面。
李顺也是如此。
本以为这踏歌谣曲调平凡,措词也不甚押韵,不像是传闻中他那个才情皆无双的娘所作出来的曲子,倒更像是那乡间民妇随口一来的小曲。
只是听完了钱莺儿口中所唱后,李顺才明了为何老头子每次听完这首曲子都会老泪纵横。
佳人深情唤人共鸣,就如同公子器所说一千人心目中有一千首乡里巴人,这钱莺儿所唱的踏歌谣,用尽深情,勾起李顺的心弦,触动了男儿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的那根敏感神经。
都说当年老头子艳福无边,有些好手段,勾走了天下第一美女,让不知多少男儿掩面落泪。
可谁又知道是那天下第一美人先行看上了老头子,做了此曲踏歌谣,以向自己心中如山男儿传达心意。
天下第一美人,不过是花花头衔,终究还是女子。
女子的心肠,纵使不是人人都能如阳春白雪般将自己心中爱意肆意焕发,遇见了心爱的人,总会透露出无数的暗示。
这些暗示之中,无一不是深情款款,才有的李顺难以体会到其中情感的踏歌谣,老头子听了却是能够忆起当年的佳人情深而情难自已。
这便是唱的人不同,听的人也不同带来的差异。
没有那种刻骨铭心的经历,又怎懂其中深情;没有佳人如耳边倾诉低唱,又怎会唤起心中共鸣。
今日见着了钱莺儿,李顺方才明白,自己原本听不出什么意味的踏歌谣,原来也可以深情至厮,心中不禁生起对那海沽石烂天荒地老的崇往。
年到十五,情窦初开。
李顺听钱莺儿所唱的踏歌谣,仿佛回到了那望江阁,看到了母亲一手撑着半边脸颊,笑脸盈盈地凝望着老头子,低唱那踏歌谣。
曲音落地落人心,秦淮河的涓涓河水终要东入海,而佳人的心意终会到达心中男儿的心底,便有了一段人间佳话,也有了一段人间悲剧。
但无论是佳话还是悲剧,在其中的都是不变的深情。
无论是什么曲子,要传达的都逃不脱一个情字,李顺悟了这曲中情,也想起了李非鱼。
宇文馥说鱼儿不记着谁的好,也记不住谁的坏。
李非鱼不是鱼,她念着自己待他的好,也有一双慧眼,看得出若是自己一意钟情于她,她逃不脱,所以选择了顺从。而且,顺从的服服帖帖,几乎已把自己代入到了妻子那般的角色中。
但李顺知道,这种顺从并不是因为她有心于自己。而是她明白这世上,有些人的喜欢,就是枷锁,霸道地让人无从抵抗。
那日花前月下,李非鱼突如其来的臣服,便让李顺明白了,她的情意在于识时务,而不是喜欢。
若是喜欢他,又怎会在涿州城中翘首以盼那卢和裕。
从那日开始,李顺便知道李非鱼不像表面那般有见地,实则是个甘于顺从的人。
顺从,才会跟着他和老常一路去丰京;顺从,才会到了涿州城就迫不及待地相见未婚夫;顺从,才会从皇宫出来后就失了往日娇贵,变得温顺如绵羊。
这种顺从,李顺能够理解。
这世上,人分三六九等,有人高高在上,有人匍匐于地,除了夫子,怕是谁都逃不脱这种顺从。
自己也是服从于这种顺从中,李顺才不认为李非鱼姿态换得如此之快,是什么违心的大罪过。
毕竟这世上,讲究门当户对,大多数的有情人都是靠媒妁之言结成连理,怕是婚前连面都未能见上一面,谁知道对方是怎样的歪瓜裂枣。
他李顺长得不差,地位也不差,论起门当户对来,足以配得上李非鱼。
只是,这其中,总是有那么些不对味。
李顺离了丰京后,数日不见李非鱼,就出了他和李非鱼的局,也渐渐想明白了。
这种不对味,源自于用一种近乎强扭的手段得到了李非鱼,即使今后不离不弃不散,李顺也害怕她不是出于真情实意。
看不明白佳人的心意,这不是李顺想要的。
听了钱莺儿唱的踏歌谣后,李顺更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两见相欢,彼此有情。
唯有彼此倾心的情感才称得上是真正的长相厮守,相濡以沫。
他和李非鱼显然离彼此倾心甚远。
前有阳春白雪对自己倾心,但自己对她终是没有达到那情爱的地步,更多的是将她视为知己;后有自己对李非鱼倾心,却是不知她会何时才能够也对自己倾心。
两两相思相恋的情感,终究还是没有那么容易寻觅到,李顺心中嗟叹。
钱莺儿一曲唱完后,珠泪撒满了瑶琴,红着眼眶望向前方同样眼中带泪的李顺。
踏歌谣便是女子对如意郎君的阐述爱意之曲,钱莺儿没有经历过那种情爱,也能懂得其中情意,唱得又是投入,借曲抒了心中情,才会这般伤感。
但李顺的脸色上有些愁烦,这可不是这首曲子中应有的情感。
钱莺儿知晓李顺一定是有着什么样的故事,才会有这般的心情,不知怎的心中有些黯然。
“好,好,不赖,果然是乐魁。”沉思良久,李顺才从曲音的余韵中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失态,连忙换了笑容,对钱莺儿竖了个大拇指。
李顺的不赖,就是极好。
钱莺儿破涕为笑,对着李顺微微颌了颌首,以示对他夸赞的答谢。
曲已经听毕,自然是好吃好喝上场,李顺有心事,面对着钱氏诸人觥筹交错的奉承,回应的是有些失神。
只是他贵为钦差,纵使失了尊重,钱氏的人也不敢露出半分不悦。况且,大家都知他突然变了个人,是因为一曲踏歌谣,定然唤起了他某些心事,也不多做计较,也无从计较。
李顺吃得散漫,钱氏的人也跟着吃得散漫,唯有钱雀儿时不时地望向钱莺儿,心中若有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