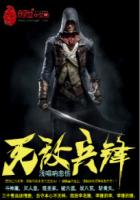“可怜的孩子,要不先躺下歇一歇吧,这样坐着该越发想吐了,都这么久了,老天,怎么就不见好转呢?”迎江客栈内,杨夫人一脸担忧地坐在秦雪仪的床前,不时拿手中的湿帕轻轻擦拭着少女苍白沁着汗珠的小脸儿。
自打晚饭前,穆云天一行人来到客栈,她就一刻不离地陪伴在秦雪仪身边,擦洗换衣,清理秽迹,一遍遍不厌其烦地温言开解,到现在已经整整两个时辰。
刚刚呕吐完的秦雪仪一脸憔悴地靠在印着云纹的秋香色大靠枕上。若有可能,她宁愿自己马上死去,整整一个下午,从马车上到这里,她都不知自己还能坚持多久,闭了闭眼,秦雪仪虚弱地开口:“杨夫人,我好些了,多谢您和杨掌柜的关照,折腾了这么久,您也乏了,先去歇着吧,只怕这会儿想吐也没有了。”
“也好,若能睡着,不如小睡一会儿,睡醒了说不定就想吃的了,这人只有吃饱了肚子才能战胜一切是不是?我过一会儿再来看你。”杨夫人叹口气,端着托盘慢慢出了屋子。
这里是青水城最大的客栈——迎江客栈,同样也是穆云天的私产之一,只不过却不是明面上的,杨掌柜是穆云天从北疆战场带回来的少有的心腹之一,三年前,穆云天从北疆战场奉调回朝,除了封官,赏赐也是没少得的,那些明面上的财物都造册入了公中,私底下,穆云天也是留了后路的,除了这两家客栈,在盛京他还有两家收入不错的酒楼跟布庄,再算上母亲窦氏留下的陪嫁,穆云天的私产并不少。
“夫人,还是吃不下吗?”四旬左右,身材略微有些发福的杨掌柜,见自家夫人又将粥饭原封不动地端出来,一贯波澜不惊的脸上也现出一丝凝重。
“是啊,小脸儿白的跟纸儿似的,怪可怜的。”杨夫人将托盘放下,为自己倒了杯茶,“那边还没传来消息?”
“大概快了,将军叫他办完事先回盛京,这么大的事,总要知会侯爷一声,另外,也要先安排下周姑娘的住处。”杨掌柜抿了口茶说。
“哼,一群不自量力的杂碎,区区十万两就晃花了狗眼,真是不知死字怎么写,还有,那个凌峰是怎么回事?他不是大言不惭地说收服这帮人只是时间问题吗?怎么这么快就死了?”杨夫人说话向来喜欢直来直去。
“夫人稍安勿躁,李毅正在挨个儿排查,想来就快有结果了。”
“蒋爷,这是严副将刚传回来的。”李玖将一张字条递给蒋聪。
穆云天房中
“爷!赵荣家里已然人去屋空,据邻里说,三天前的晚上,他突然带了两个人回来,结果一夜之间全家老少六口俱都不见了,屋里值钱的也都带走了,严明他们还进了那房子,的确是空的,连炕上的席子都被卷走了。另外,严明还查到,青水城新上任的知州宋大人同衡城的知州本是同宗。”
穆云天负手而立,高大的身影配上室内闪烁不定的烛火,让人倍觉森冷孤傲,闻听蒋聪的汇报倏地眼中射出一道厉芒,头也不回,声音好似来自深谷的绕音,绵邈幽邃:“给陆先生传信儿,叫他密切注意萧家的动向,另外,把宋文茂的底适当透出去一些,也该让那些老大人们喝点粥了,一切在我回京前办好。”
“是。”蒋聪应完见穆云天没说话,了解主子的他便没擅动,通常这时候穆云天都是有下文的,果然,静默了一会儿,穆云天再次开口,语气明显低沉了许多:“那边怎么样了?”
蒋聪闻言一愣,随即扑通一声跪下,满面愧疚地回道:“还是吃不下东西,刚刚连喝的水都吐了,益草堂的大夫已经开了压惊的方子,可这药,怕一时还喝不下。都是奴才的错。”
“回京后自领二十军棍,下去吧。”
“是,奴才谢主子恩典”蒋聪磕头后起身,缓缓退出屋子。
“你小子,怎么不看路的?”
“对不住,我一时,唉!”只顾低头走路的蒋聪,没想竟撞在从外面匆匆进院的李毅身上。
“爷罚你了?”李毅挑眉问。
“嗯,这样我心里还好受点儿,唉!都怨我!我那会儿只想着出去帮忙……”蒋聪这会儿肠子都快悔青了,自己怎么就那么不长脑子,“周姑娘定是一个人怕极了才跑出去的,我真是头猪!”蒋聪使劲捶了下脑袋。
“这会儿后悔有用?还是赶紧办好爷交代的事是正经。”李毅话不多,却每每切中要害。
“我这就给先生传信儿去,你那边都落实了?”一说到正事,蒋聪立刻严肃起来。
“嗯,不过又审出了点新线索,据一个小头目交代,三日前随赵师爷前往山寨的人里,有一个姓谢的并不是衡城本地人,而且武功高强,一挥手便重伤了他们寨主的结义兄长,只因那位仁兄极力反对义弟接这趟买卖,而且,听那人的描述,我倒觉得此人很像萧家那位……”
“三日前?这么说赵荣是离开山寨后直接回的家?不对,这不是重点……”蒋聪一脸不可置信地瞪着李毅,“你是说那位卓先生?不该这么明显吧?”
“他自然是易了容的。”李毅说着往主屋去。
“那你怎么能肯定是他?”蒋聪不服气了,奈何人已到了门口。
“爷,李毅求见。”
“进来。”
秦雪仪将自己蜷成一团缩在被子里,虽然早已疲倦到极点,但她就是不敢闭上眼睛,整整一个下午,她强迫自己不去想,可做不到,一闭上眼就会看到那恐怖的画面!那个深刻残酷的修罗场,那些死状凄厉的尸骸,太可怕了!直到那时她才知道,死,其实真的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一个人连死都是一种奢望的时候,那场景惨—不—忍—睹!
“为什么?为什么?”马车上,她不止一次地哭着问身边的男子,“为什么不能给他们一个痛快?为什么那么残忍?为什么老天要制造如此深刻的仇恨?为什么人和人之间非要拼个你死我活?为什么……”然而每次迎接她的都是那个男人默默无语的陪伴,没有安慰,更没有任何辩解。于是她不再哭,不再问,可这样的后果便是如现在这般,一遍又一遍抑制不住的狂吐,食物吐没了接着吐苦水儿,什么都没了,干呕也能呕得昏天黑地,眼泪横流。
“我要死了吗?”秦雪仪不想哭,她自认不是个脆弱不经事儿的,可泪却无论如何止不住。如果一个人的成长,是要经历如此残酷的死亡,她宁可不要,什么穿越女无敌,自信万人迷,那不过是编来给闲人解解闷罢了,真正的战争拼的是血,别人的血!高门大户看着雕梁画栋,锦衣玉食,可她秦雪仪有什么?除了这具身体,她在这陌生的古代一无所有。身份?她敢大声说出来吗?没有家族,没有父母,她只是一个弱女子!一个别人动动指头都能叫她粉身碎骨的小人物,她又凭什么相信自己会活得比人家强?
下意识地,秦雪仪的手又摸向了那块挂在胸前的凤凰玉佩,入手的温暖令她心底微安。
“你知道吗?我今天很难过,那些人我不知道是不是该死,但他们好惨,惨极了!我真怕自己有一天也会同他们一样,完全掌控不了自己生死的滋味,真的会是生不如死!可是,眼下不去那里又能怎么办?在外面,更难不是吗?”一圈一圈,蹭摸着可爱高贵的小凤凰,秦雪仪喃喃地诉说着。不知过了多久,就在她终于支持不住而微微合眼的一霎,忽然感觉手指一痛,还不等她做出什么反应,一道紫光猛然从玉佩里挣脱而出,电光火石之间便射进了她的眉心。待秦雪仪睁眼时,看到的只是自己被划破一条红线的手指,甚至连血都没再流出。
“奇怪,怎么会划破的?”没照镜子的她并不知道,此刻正有一道诡异的血色符文缓缓隐入她的眉心深处,很快,大量的信息像被牵引着有序地涌入秦雪仪的识海中,虽没给她带来一丝的不适,可秦雪仪还是不悦地皱着眉,因为不论她如何抗拒,那些东西竟都好像终于回家般兴奋跳跃着叫她推都推不开,身体渐渐飘忽,神识仿佛到了一个神秘的世界,远山近树,碧水湖泊,数不尽的植物生机勃勃,百花争艳,各色水果挂满枝头,翠艳欲滴的叫人不禁口水直流,迎风而过,尽是各种清香,空气格外的新鲜,让秦雪仪惊讶之余忽然生出一种久违的思乡之感,连她自己都无法解释,
意识转过一片竹海,眼前出现一座园林式的住宅,石子漫成的甬路依次通往各种去处,院内亭台楼阁,小桥流水,处处雕梁画栋,巧夺天工,每一间院落都是一处独特的景致,秦雪仪如同恢复记忆般,熟门熟路的摸到主屋那三间雅致的书房,满室的墨香让人分外心安。近乎两百平的空间,四周全部是书架组成的墙壁,各种书籍被分门别类收置于固定的区域,让秦雪仪大吃一惊的是,在这古典风格浓重的房间里,居然摆着一套代表着现代气息的真皮沙发!天!这儿原来的主人到底是何方神圣?这么大的手笔,应该不是简单的穿越人士能搞定的吧?像她,可就什么都没有的。再看其它,宽大的檀木桌椅,名贵的古董花瓶,花瓶里的鲜花好像昨天刚摘下似的,处处透着奢华神秘,如此妙处,自己不是在做梦吧?
刚有此念的秦雪仪,一个激灵,神识便被重新打回到体内,再看自己,仍旧躺在客栈的床上,手里,依旧是那块摸了不知道多少遍的玉佩,“怎么回事?刚刚难道是幻觉?可是,是不是太真实了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