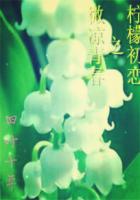院子里的迎春花瓣与柔静春风争相追逐,纷纷落下,夙昕出去的这么一会儿工夫地上已经一片黄媚。枝头迎风轻摇,几片瓣花摇曳欲坠,却生生攥住了枝头不肯轻易落地。
她突地认为自己便如那几片顽固的黄色花瓣,不肯轻易顺应天意。
几片花瓣终是敌不过季节的变换和春风的抚慰,萧萧然,在空中打了几个旋,落下。夙昕轻叹一声,走到盛着乌龙茶叶的草板前。
草板已被花瓣覆盖,瓣瓣嫩黄遮掩了乌绿的乌龙茶叶,盖住了乌龙的光华。草板上,落花占了上风!
夙昕眼前一亮:花儿生在树上,便同所有花朵儿一般无二,从无任何出彩别众之美;然而落在了草板上,竟遮掩住了名贵的乌龙,凸显了明丽的黄艳嫩美。或许,进府为妾亦不失一个绽放春华的良机……
转念想到惠阳公主的刁蛮性子,她皱着眉使劲摇了摇头。女人善妒不可怕,女人善妒又掌着实权才可怕!每日在公主眼皮底下生活,就连吃饭喝水都会噎到吧!她现在连那驸马的面都没见过,就开始被厌恶了……如果被驸马多看两眼,多说上几句话,这位醋坛子还不扒了她的皮?
她禁不住打了几个颤,稳了稳心神。好一会儿才恢复正常。
抛开杂念,夙昕蹲下身,心细地挑出落花,卷起袖子继续揉捻起来。
人一旦忙碌起来便容易忘却烦恼。几个时辰过去,园子里风力渐强,空气中多了几分凉意。夙昕未觉,整个人沉浸在劳作当中。
正将那试婚的烦心事忘得一干二净之时,锦兰跑了进来,在她的身侧蹲下。
夙昕瞅都没瞅,径直道:“怎地,你的活儿忙完了?今儿怎么这么快!”
“嘿嘿!”锦兰先是咧着嘴笑,见她并不理会,便扯了扯她的衣袖道:“太后传你是为何事?我这儿担心着呢,急忙就把活都干完了。”
被拉了衣袖,夙昕停了动作,心情恢复了许多,笑着伸手抹了锦兰的脸一把:“是担心啊还是八卦啊?”
“啊!”锦兰惊叫一声,用手一摸脸蛋,“黏黏糊糊的!你个大胆丫头想毁我的容吗?”
“怎么可能毁容,美容还差不多。”夙昕真心一笑,如阳光般璀璨,尽管她生得不是极美,却是清秀可人,尤其一笑,阳光般摄人眼眸。
锦兰随意抹了几下,又凑近了身子:“好夙昕了,什么美事?说于我听听吧!”
夙昕的笑容转瞬便黯淡下来,悠悠地叹了口气。这话该从何说起……究竟算好事还是坏事真不太好说清楚。
“是坏事吗?前段日子咱们夜里不睡,耍闹的事儿让太后知道了?”锦兰的声调低了几分贝。
她摇摇头,无奈地笑笑,既有一丝为难,又含一抹安然:“前几日你提及惠阳公主出嫁之事,我只当跟自个一点关系没有呢……”从来不管身外事,一心办好眼前活,此刻她也被这繁琐的皇室旋风卷了进去。
锦兰眨眨那对小小的核桃眼,听得更加认真。
夙昕不愿多绕弯子,苦笑道:“试婚格格一职落在了我头上。”烦恼于事无补,倒不如坦然面对现实。
锦兰一呆,水灵灵的眼珠瞅着夙昕,意欲询问真假。
瞥了锦兰一眼,见锦兰的可笑摸样,她眸子里透着丝好笑,转过身去继续揉捻乌龙茶叶。
“夙昕,你是唬我的吧?”见她不说话,锦兰终于相信了,揉了揉脸蛋,笑了起来,“这是美事呢!”语气羡慕不已。
连锦兰也羡慕她,可又有什么好羡慕的呢?即便于他人来说是千金难求,与她却是无甚欢喜。费尽心机,安稳难求,那样的日子,只要真真正正的过了就会知道不值吧?
她叹了口气,道:“太后的懿旨还没下来,此事……说不定还有转机,你可别给我去到处乱嚼舌根子。”
锦兰点头如捣蒜,突然神秘地压低了声音:“你可知那驸马是何人?”
夙昕一愣,她还真没在意过这些。从始至终她都在想着将来的日子可能会如何如何,真没念想过那个极可能成为她夫婿的男人究竟是个怎样的人物。如若是一良人,她去了倒也不算亏得太多,好在心里能得些安慰,就怕是那凉心薄情的风流子……
锦兰见夙昕一会脸红,一会嗔恼的样子,忍不住刻意逗趣道:“听说这驸马爷可是个痴情的种,你去了不一定能受宠。不过男人的心多是易变的,倒也保不准……”
这一打趣并未起效,才一会儿,夙昕已神态自如了。
锦兰正说得上瘾,突然被夙昕打断:“这位驸马是怎么的人?”她终是好奇的。
她才问了一句,锦兰立马一筐罗话语往外倒:“驸马是新科状元,满腹经纶,文采斐然,更难得的是相貌出众,可比潘安,我曾远远瞅过一眼,真真是个比女人还漂亮的男子呢!那么美……”
眼见锦兰有向花痴靠拢的迹象,她好笑地转移话题:“这么说……是公主看中的驸马?”
锦兰痴了片刻,又恢复了本来摸样:“是呢!那日状元郎奉皇上之命进宫为珍妃作画,在御花园跟公主就那么撞见了。公主只瞅了一眼就惦记上了,连珍妃在旁边也不顾了,频频与状元郎示好。据说,那场面羞红了不少宫女的脸儿。状元郎前脚刚一出宫公主就跑去求皇上赐婚。太后知道后发了脾气,教导了一番妇德,但是根本没用,倒是最后太后也顺了公主的意。”
“咳咳!原来是这样啊。”锦兰向来有夸大事实的本领。她,并不全信。
“哎!你是没救了,连这都不知道,每次说与你听的新鲜事儿全从另一只耳朵里飘出去了。”锦兰一副恨铁不成钢的凄婉面容。
夙昕失笑:“有你在,我还记那些作甚,有什么需求直接问你便是了。”
“你若是嫁了状元郎,即便做妾,却也值了!”锦兰信誓旦旦的样子,倒是透着几分真情实意。
夙昕撂下手里半卷的乌龙茶叶,思虑道:“你说那准驸马是个痴情的,难不成他对公主也是一见钟情?”
锦兰翻了翻眼珠,一副高深莫测:“痴情这事儿整个皇宫知道的估计不超过一巴掌,而我恰恰就知道。”卖弄一番她继续道:“状元郎喜欢的另有其人!”
两人说得兴起,连墙外突然有几个人经过都未发现。墙外之人听了这句“另有其人”时脚步则停了下来。
夙昕好奇的表情让锦兰很是受用,笑了几声道:“状元郎心仪之人乃是吏部侍郎章玉庭之女章子鸢。传说状元郎还是平民的时候两人便相识了,章子鸢不但不嫌弃他的平民身份,更是拿出自身的首饰变卖帮他度日购书。说起来这也是一段京城佳话,在章子鸢的鼓励协助下他终于考中榜首状元。正准备迎娶呢,状元郎却被公主看中了。不得已之下,好好的侍郎嫡女却以侧室的身份进了门。”
听了这话夙昕只觉麻烦,已有一位侧室,还是心爱的女子,若是公主嫁过去,还不准得多热闹呢!宅府中事说不定比她想象中更乱杂不堪。这样的一潭浑水,谁想去谁去,就算是良人,她也不去!
公主那刁蛮的性子能容得下掌着驸马心的侧室?想那位痴情的章子鸢倒也可怜,好不容易守得云开,却见不得月明。
“哪个贱婢?!好大的胆子!”院墙外,一声厉喝传来,熟悉的声音骇得夙昕一楞,锦兰则直接一屁股墩在了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