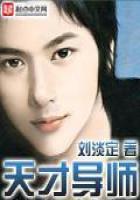昨日准备面试,竟忘了更新。
^^^^……………………………………
可陈琬的如意算盘打得忒早了些,这深宫大院,哪里是她想去就去说留就留的。跟着陈瑕到得陈家帐外,刚要挑帘进入,这帐帘却从里被人撩起,但见流光寒着一张俊脸走出来,见到陈瑕,他微微一颔首,就当是打过招呼,对陈琬则是完全忽略,竟像是未曾看到她一般。
不管世人怎么看待刘钦同流光,陈琬总对他俩抱着谨慎态度。不知为何,这流光总让她感觉不像是耽于儿女情长的人。
刘钦同他是焦不离孟,可那两仪殿也不是谁人都能进的,方才刘钦身边没有流光的身影也是可以理解的,可这流光此时却从陈家帐内出来,这叫人好生疑惑。
陈琬刚要开口,却被陈瑕拉住了衣袖,轻咳一声算作提醒。
流光此人出身高门,又曾是武将,对一般人等皆是不屑一顾,不过是看在陈瑕同自己境遇类似,颇有心心相惜之感,一来二去竟也有些点头之交。
待他走远后,陈琬不解地问道,“他到这里来作甚?”
陈瑕显然是晓得内中缘由,却是闭口不谈,顾左右而言他,“天色不早了,你今日若是不想被外祖母‘挽留’,就要早些动身才是。”他说着,单手在陈琬腰侧轻轻一推,就把陈琬整个推入帐内。
说来也巧,陈琬刚进帐,墨珠也刚好要出来,陈瑕用力稍重,陈琬脚下不稳,眼看着就要跌倒,墨珠眼疾手快地将她接住,抱了个满怀。
陈琬刚上山时,总被山上的半大小子们戏弄,她在京中有诸多同龄男孩担待谦让着,到了琅琊,师傅男女一视同仁,也不帮她说话,往往便是大师兄出面来调解。
她后来便黏着大师兄,整日得空便往他那里去。她那时年纪也不小了,十二岁的小姑娘,抱起来沉甸甸的,大师兄却不嫌,外出只要她喊累,便会将她抱在怀里,被师傅说教了几次都不肯放手。
陈琬想起前情旧事,不免感怀,转念又想到这墨珠已变成这番模样,心里莫名生出一股厌恶感,忙推开了他,站直了身子,掸了掸衣袍。
陈夫人走上前来拉住陈琬的手腕,将她拉到自己眼前,她上下打量了陈琬一番,不免心惊:陈琬发髻早散,只用一根腰带将头发绑起,朝服外衫大开,里头的内衫也是凌乱不堪,又见其眼周红肿,面色不佳,活脱脱一副被人欺辱的模样,忙道,“可是那姓陆的同你过不去?”
陈琬扯扯嘴角摇摇头,“并没有同我过不去,我只同我自己过不去。”她说着便甩开了娘亲的手,自去寻了一帕子擦脸,胭脂铅粉悉数全卸下,又将帕子丢在脚边,走到晋安侯案前同他相对而坐,也不顾父亲勃然大怒的眼神,抢了他手中的锡酒壶“咕咚咕咚”尽数喝尽,“啪”地将酒壶重重砸在案上,挑衅地看着自己的父亲。
晋安侯劈手夺下自己的酒壶,喝道,“你这是做什么?”
她打了个响亮的酒嗝,双手撑着两颊,眨巴眨巴大眼,故作单纯地问他,“您把我嫁给陆修,您有什么好处?”往日在琅琊,师傅明文禁酒,陈琬从来就没有沾过酒液,此番也是她活到这般年纪第一次喝酒,酒嗝过后只觉得满面烧热,脑袋晕眩,意识却清晰得紧。
陈夫人忙上前同栖霞两人要将陈琬扶起,却被陈琬一把挣脱开,倾着上半身,直视着晋安侯,“您说呀。”
她嘴角咧到最大,笑容灿烂宛如六月阳光,眼中却流下泪来,顺着面颊渗入衣领,“你们一个两个,都把我当什么人了?我原先以为,自己安安分分地,自然没有人算计揣度,哪想到哪想到……”她顿了半晌,猛回头瞪了陈瑕一眼,“我原以为兄长你是我这边的,没曾想你也这么听父亲的话,同袁靓真是天生绝配!”
她说得口不择言,晋安侯脸色越来越难看。陈瑕大跨几步拉起陈琬,怒道,“珞珈!”
陈琬睁着醉眼望向他,“难道我说的不对?”她还要说话,早就站在她身后多时的墨珠一记手刀劈在她后颈,她登时便晕过去,陈瑕松松地揽着她的腰身,让她伏在案上,解了自己的外衫披在她肩上。
帐内几人正无言相对,帐帘却被人挑起,一青衣打扮的中年男子打着黑油纸伞进得门来。明明今日是大好晴天,这打着伞进门……
晋安侯忙叫桂宝看座,虽不是在家中,可既有人来报丧,礼数也应当齐全。
中年人是山东周家来的,果真就是为了贤太妃来报丧,他也未久留,语气平静地交代完毕后便打了伞离去,倒叫陈家人不是不滋味。
原本按本朝的律法,后妃去世,若不是深得帝宠,又不是储君之母,只需娘家稍作操办,近族吊唁便可,停留七七四十九天后便进到西郊皇陵入陪葬室。朝廷中除却礼部宗正寺等,再无干涉了。
周家与陈家往来不深,贤太妃过世,若是按常理来讲,陈家最多只需派人前去吊唁,再无他事,可周家去正式派人来报丧,再不济,晋安侯也得要在出殡时在道路设坛祭奠。
贤太妃所出不过三子,皆是碌碌之辈,在九个皇子中,实在算不上出挑;周家虽是名门望族,可近几年在朝中的权势渐渐下滑,不过仗着昔日光辉撑门面,晋安侯实在不想同他家深交,思量良久,对陈夫人道,“周家往日同咱们并无多大来往,不过他家既到了礼数,咱们也不能缺。”
陈夫人会意道,“我今日便去她蓬莱殿中吊唁。”
“只可怜了圣人了,今日分明是万寿节,却摊上了这档子事儿。”晋安侯伸着手由桂宝替他穿衣,低头又看到闷头昏睡的珞珈,不禁叹了口气,“光长年纪不长脑子的东西,也不知她是真傻还是装的。”
他似是在说陈琬,眼神却从陈瑕的面上飘过,陈瑕忙低垂了首。墨珠若有似无地瞥了他藏在身后紧攥的拳头,几不可闻地发出一声嗤笑。
陈琬醉酒沉睡,自然不知早发生了什么变故,她睡得沉沉,中有人将她抱起也不知,待她醒转睁眼,才发现到了一处陌生房间。
她拥被而起,望着雕花床顶出了会儿神,又将自己身上的锦被掀去,却见自己已被人脱了朝服,换了白色绸衫,伸手在脸上一摸,竟也是卸了妆容清清爽爽。她定了定心神,正要出声喊人,一转头却看到拔步床塌下坐了一人,吓得她差点叫出声来!
“你是谁?!”
那人转过头来,似笑非笑,口中道,“才见过面怎么就不认识我了?”不是别人,正是陆修的妹妹陆佳,一身男装打扮,腰佩短剑,从身后看,活脱脱便是一青年男子。
陈琬惊得扶住床栏,皱眉道,“这是何处?”
陆佳站起身来,坐到陈琬床边,一手拉了陈琬的手腕,正色道,“侯爷要将你送回府中,却被承欢公主拦下,得亏我兄长提醒过我,说公主并非良善,你又同她顶撞,担忧你在宜春宫会受委屈,便叫我在武德殿旁设了伏,把你劫了出来。”她说完又换上了大咧咧的笑容,多少惊险的场面只轻描淡写带过。
陈琬用手扶额,闭了眼不语。她早想到承欢公主不会轻易让自己出宫去,哪里料到陆修也想到这点儿上去了,还叫自己的妹妹把她带出来!
陆佳以为她宿醉头疼得紧,转头就要叫人,被陈琬抬手制止了,“你只要告诉我,这是哪里?”
看着屋里的陈设,竟还是像在宫里某处,可就不知是在何处……
“这里?你倒是可以猜猜看。”陆家这会儿还有空同陈琬猜枚,促狭地眨眨眼,“反正不会是东宫里头啦。”
陈琬推开她下到地上来,在屋内转了几圈,陆佳的视线便一直跟随着她转,末了,陈琬走到窗边,倚靠着窗台,长叹出声,“你把我弄到这里作甚?”
“这里才不敢有人来啊。”
凌烟阁,宫中的禁地,有哪个胆大包天的敢来。陈琬自那日被刘钦警告过后,特特地问过元氏,元氏本有兴致同她细讲,未料到承欢公主推门而入,不了了之。可就算这样,陈琬还是知道了这凌烟阁本是太宗为专宠一后妃而造,哪想到**那后妃断不争气,早早地便在**争斗里断了命,投井而亡。
那后妃葬身的那口井,就在凌烟阁。
陆佳走到陈琬身后,指着那被繁花掩盖的古井,“宫里的没几个是好人,日里亏心事做太多,夜里便怕冤鬼上门,也不知这井里到底埋了多少人呢。”她说得轻巧,陈琬很是认真地看了她一眼,赞同地点点头。
不过,这凌烟阁既是太宗皇帝时期建下,承欢公主又对它讳莫如深,叫人不得不在两者之间做联想。
陆佳拉了陈琬的手复又到床边坐下,侧头打量着陈琬,“你是什么打算?”
“……”陈琬当然知道陆佳暗指何事,此时却不得不装糊涂。
“我兄长那般品貌,虽说年纪是大些,配你还是绰绰有余,他素来面冷心热,你若真嫁给咱们家,我父母也不会亏待你,到时候你我加上刘钦,也可一处说话。”
陆修此人,陈琬从此前几次交往下来也了解小半,他未到而立之年便登上高位,断不可能是什么面慈心善之人,也不可能耽于儿女情长,可论说要做夫妻,他年岁长些,又懂得揣摩他人心思,应是知冷知热的,是个绝好的夫君人选,比之其他,好上太多。
陈琬垂首,不发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