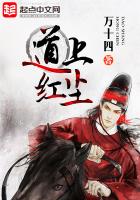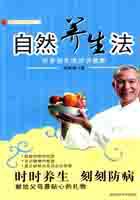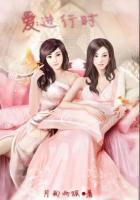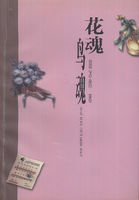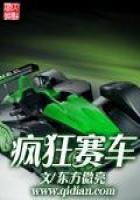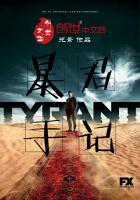“原来您是延安人啊,难怪长的这么高大强壮呢。咱们陕西人能打,可惜现在很多人走上了邪路,跟着流贼,让人痛心啊。”祝家良跟周康石套近乎。
“是啊,谁叫咱们陕西穷呢。连年大旱,朝廷有没有粮食来赈灾,老百姓没有饭吃,自然容易受到一些野心家的鼓动。所谓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一旦当了贼,就很难回头了。对了,祝大哥你有什么打算啊。”周康石试探道。
“还能有什么打算,我有一房远亲在云南昆明,现在我无家可归,只好打算先去投靠他了。可是已经有十几年没有联系了,不知道他还在不在。唉。”祝家良叹息道。
“这样也不是个事啊。对了,你说的毛褐是什么东西啊?可能是我孤陋寡闻。”周康石突然想起他家是织户,开了个毛褐作坊,自己还真不知道毛褐,难道也是布匹的一种?
“毛褐就是用动物的毛,主要是羊毛织成衣物,是西北一带的主要过冬衣物。由于西北多游牧,自古就有用牛、羊、骆驼等等动物毛‘捻毛为线,织褐为衣’的传统,经过千百年的改良,终于从唐朝开始,咱们的毛褐就开始成为贡品。大概从国朝初年,由于江南的棉麻纺织技术的传入,咱们兰州的毛褐也采用经纬相间的纺织技术,产量大增。而兰州城也是大明最大的毛褐产地了,最鼎盛的时候,有百家大作坊,数以万计的工人在作坊里干活。”祝家良似乎还在回忆自己家里鼎盛时候的辉煌。
“按你这么说,既然是贡品,那应该普通人就穿不起了,怎么还有那么大的市场?”周康石有些不解。
“不是这样的。在古代,毛褐因为工艺不过关,所以基本上是老百姓穿。到了唐朝,因为皇家崇尚胡风,毛褐就流行起来了。后来从西域引进的山羊,采用山羊的内毛织成的各种色彩绚、质感不比丝绸差的毛褐,这种精致的毛褐又叫绒褐,因为兰州所产绒褐质量最佳,所以也叫兰绒。在国朝,士大夫们非常喜欢兰绒,是比丝绸还贵重的礼服。连皇宫都有专门的兰绒制造作坊呢。
兰绒是高档货,用绵羊毛织成的普通衣服还叫毛褐,也叫粗褐。但是这中毛褐比棉衣实用,更加保暖。是西北不少民众过冬防寒的首选。相比较而言,毛褐产量更大一些,而绒褐产量低,但更赚钱。”这是祝家良的老本行,所以说起来头头是道。
毛褐原来真的是羊毛织成的衣服,有高低两档。如果自己开个毛褐作坊,应该还是有很大的赚头的。明末,小冰河,天气寒冷,连广东都连年下大雪封山。丝绸肯定是不保暖的,棉布还凑合,但最保暖的还是羊毛了。这个毛褐的市场容量很大啊。关键是既有高端市场的兰绒,也有面对普通老百姓的毛褐。
这东西关键是成本低,西边就是康区,要多少羊毛就有多少,而且去收购羊毛的话,肯定便宜。蒙古人和羌藏人养羊主要是获取肉类和奶,对羊毛需求并不太大,自己可以大量低价收购。毕竟羊毛嘛,他们又不能全部用完,用完了还可以长出来,听说绵羊一年可以剪三次毛,产量极大。
好象英国就是通过毛纺织业而发达起来的,如果自己也大力发展羊毛产业,说不定能促进四川康区的资本主义萌芽呢。
“那么这纺织毛褐兰绒,是不是也跟江南的棉纺织布差不多?”如果是的话,那就可以规模生产了,产量就可以上去。
“正是,基本就是按照织布机改造而成的。绒褐织机跟布机基本没有区别,叫平机;粗褐则是由地机织造,也没有大的区别。产量很高的。”
“那你会都会织造这些毛褐和兰绒不?我说的是整个织造的过程.能把兰绒染多少种颜色?”周康石起了招揽之心,急切的问道.
“小人家里从事毛褐织造五代了,家里开毛褐作坊也有三代了.对于织造了如指掌,毕竟是要靠这个吃饭的.至于色彩,火红、松花、桃红、石青、油绿、纯白、深褐、紫黑、杂色等等,我都会.”祝家良大喜,看来这个周康石是想让自己替他开作坊了,这比到云南去投靠那个不知道死活的亲戚要强得多,于是赶紧拍胸脯说都会.其实他还真的都会,并没有撒谎.
“可惜在这里没有平机和地机,不然我想让你帮我开个毛褐作坊,可惜啊.”周康石叹了口气道.
“小人跟平机和地机打了二十多年的交道,对它的构造也是十分熟悉的.只要有木匠,我能教他们把平机和地机做出来.小人愿意为恩公效力,把毛褐作坊建起来.”祝家良自然不想放弃这么好的机会,连忙表示机器不是问题.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看来对方确实有真才实学,是毛褐业的专业全才.最近自己是不是踩到狗屎了?连在山上雪地里拣的都是一个专业人才,而且此人还能为自己创造大笔财富.
“你觉得在建昌卫建个毛褐作坊有前途吗?”周康石询问道。
“建昌这个地方现在也不是很太平,就看恩公要建多大的作坊。如果是小作坊的话,还是有些前途的。但如果是大作坊,就怕没有太多的羊毛。毕竟现在建昌城外四十里就不太平,可能没有足够的原料。”祝家良分析道。
“原料不是问题,你不知道我跟康区的蒙古王子关系非浅吗?要多少羊毛就有多少羊毛。按照你的看法,多大作坊才能算得上大作坊?”
“一般而言,整个作坊有一百人的雇工,就可以算是大作坊了。当然,恩公是做大生意的,雇三四百人来生产也不是不可能的。”祝家良轻轻的拍了个马屁。
“那么一百人的毛褐作坊,需要几台平机和地机,一年能生产出多少匹毛褐或者兰绒?”周康石需要的是量化的数字。
“一般四五十台就可以了。如果是专门生产毛褐,每七天可以产一匹,这样一天总共可以产七匹左右。所以估计一年可以生产出两三千匹。如果全部织造兰绒的话,大概可以生产七八百匹。”祝家良稍微思考了一下就得出了答案。
“那么一匹普通毛褐价值几何?而一匹兰绒有价值几何?”周康石需要知道一下行情。
“毛褐跟质量稍好的棉布价格差不多,一匹六七钱银子。而普通兰绒一匹可以卖五两银子,做工精细的能卖到上百两呢。”
毛褐的价格竟然这么低,一个一百人的作坊,一年忙到头,才有两千两银子的销售额。按照每个雇工每天十文钱,一天工钱就是一两,一年就是三百多两,加上原料、设备折旧,顶多赚个一千两银子了。不划算啊,不过如果是兰绒就要好一些,估计比毛褐要多赚一倍。
看来在明末搞实业远远没有搞商业赚钱,雇佣一百个人,也只能赚一两千两银子。
“那兰州那么多作坊,肯定大多是生产兰绒的了,应该很少生产毛褐的了?”周康石问道。
“正是,生产毛褐哪有兰绒赚钱。所以织造毛褐的很少,怎么,恩公,你是想多织造毛褐?”
“还没有想好。在兰州,一个雇工每天工钱是多少?”周康石知道江南那种长工每天大概十几文钱吧,不过东家一年需要给五石米。但江南是大明经济最发达的地方,物价也高于全国其他地方,所以不具有可比性。
“只要六七文,加上一顿饭,大概就十文钱就足够了。”祝家良很佩服周康石,难怪生意做的这么大,看来也是经过精打细算的,每一个环节都仔细推敲。
跟自己想的差不多,建昌卫的生活水平应该跟兰州差不多,甚至还要差点。
“在兰州,羊毛的价格贵吗?”周康石继续问道。
“织造兰绒的山羊毛还是比较贵的。至于绵羊毛,很便宜的,最多占成本的一两成。”
这就好,兰州那里的畜牧业应该还没有康区的发达,康区的羊毛应该比兰州的更便宜。要不自己先开个作坊做做看毛褐和绒褐。一样一半吧,绒褐赚钱,毛褐就做给自己的士兵和家丁们在冬天防寒。这个东西要想赚钱,就要提高效率,规模化生产。
如果在建昌建一个大的毛褐作坊,吸纳当地数千人来给自己做工,也算对建昌卫有所贡献了。虽然没有暴利,但还是可以一试的,反正一个巨大的原料产地就在旁边,自己就来做这个实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