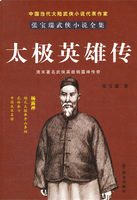在父亲的横眉冷对和母亲的再三规劝下,叶文希还是将屋里的东西来了个乾坤大挪移。
李家的房屋是两层的,外表也比叶家的那所房子耐看些,打扫过卫生,铺上被铺,叶文希已经将家从隔壁迁到了李家的二楼。
“有本事以后再莫踏进我家屋门了!”对儿子的另立家室,叶理习惯性地不平。
结果马上叶文希就踏进了屋门,笑脸相迎着,“爸爸,两瓶老酒,您老收好。”
叶理的脸上还充斥着怒气,手却没有商量地接过了那两瓶回雁峰大曲,“死伢子就会来这套!”
彭兰香见父子俩握手言和,心里再高兴不过了,喜滋滋地张罗饭菜去了。
……
“哑巴。”要找到哑巴不难,他出没的地方不多,随便找几个小孩子就能轻易问到。
“哑巴”显然还记得这个曾经请他吃个“大餐”的少年,咿咿呀呀地对着叶文希笑着,却无法表达出内心的语言来。
“走,带你去吃东西!”叶文希可以确定“哑巴”的听力不成问题,神智也不是问题,要不怎么一说吃东西他就这么兴奋呢?
照样给“哑巴”打包了一只烤鸡,要用人,就必须先收心,这是叶文希老早就明白的道理,几只鸡算不了什么,据说三国时某个双手过膝双耳及肩的龌龊男为了收买人心,甚至连自己的儿子都不惜摔打呢,这不得不让人怀疑那个和他老爸一样出名的儿子是不是那个龌龊男亲生的,那时可没有亲子鉴定这玩意。
上次被父亲知道了自己请“哑巴”吃饭,结果遭到了一顿“毒骂”,这次叶文希学乖了,先拿了酒孝敬叶理,拿人手短,喝人嘴软啊!以后大家想搞保持某方面的形象,可千万别因一点小恩小惠的而酿成大错啊!
把“哑巴”领进了李家大门,叶文希告诉他以后睡房屋里时,“哑巴”咿咿呀呀地哭了起来,要不是叶文希拦着的话,“哑巴”都能给他下跪了!
可是叶文希好劝歹劝,“哑巴”就是不愿意住进来,或者说是不敢住进来更合适点的,他招招手,将叶文希领到了李家的房屋后的一间低矮棚子前,那是李家以前喂养猪的地方!
当“哑巴”咿咿呀呀地笑着指着那地方示意他以后睡那里就好了时,叶文希的心差点绷碎!心酸酸的,鼻子抽抽的,眼睛涨涨的,强忍着没让自己留下泪啊。
“你狗日的倒对农村的房屋结构蛮了解啊,还知道猪栏一定是在屋后的。”用笑骂掩饰着自己的窘况,对叶文希的叫骂“哑巴”却是乐呵呵地接受了。
“我们不住这里,我再给你找个地方。”猪栏哪是住人的?
叶文希这次没把“哑巴”带到李家堂屋去,给他找的是以前李家用来堆积材木的柴房。柴房里面早就空了,还算干净,面积也挺大的,“你以后就住这里吧,我再给你张罗被铺啊!”
把这事和母亲说时,母亲除了神色上的不快,没有什么其他的表示,对儿子和一个“疯子”牵牵扯扯地她是不待见的。
而叶理除了几句怒骂就没有别的了,他老人家对自己的儿子“沦落”到与“疯子”为伍是心痛不已啊!要不是之前叶文希一切表现正常,他早就把儿子送到乡医院检查去了,他真怕初时的那次中暑将儿子的脑袋也给整坏了呢!
不乐意归不乐意,夫妻俩还是磨蹭着给叶文希腾出了一套老旧的被铺出来。
两条长板凳,几块宽长的木板,一床老旧的草蒿巾,一床破旧的棉絮,一块老旧的床单,再加上一床老旧的棉被,这就是“哑巴”所有的窗上用品。
虽然简陋,可“哑巴”已经乐得脸上开了花,常年在外流离,现在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窝”,他的兴奋已经溢于言表了。
对于“哑巴”的道谢,叶文希还是欣然接受的,“你先就在这住吧,以后条件好些了,再给你换,说不得到时还给你娶了房媳妇呢!”
“哑巴”仍只是咿咿呀呀地摇头,反对的态度极为坚决。
“不急不急,呵呵。”见“哑巴”那手足无措的惊慌样,叶文希心里笑开了花,这疯子还不好意思呢。
……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叶理现在也不和儿子吵了,只逼着他“交待”。
叶文希咬着青菜梆子,含糊不清地回答着,“什么意思?还能什么意思?见他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就帮一把呗,何况他还有手有脚的,我承包的那天大的山头我一个人搞的过来不落?”
叶理笑眯眯地看着儿子,抿了口酒,“我早就知道你个兔崽子没什么好心眼,人家残疾人的主意你也打,你就不怕天打雷劈啊?做好事列,过几天去烧把香吧!”
父子俩贼贼地笑着,旁边的彭兰香舒了心,这俩老小子不闹腾了就是福啊!
“前几天去县里,琪琪他爸爸说什么没有啊?”叶理开始关注起儿子的终生大事来,在钱和香火之间,他没有选择,或者说只有一个选择。
“说了很多。”叶文希扒了口饭,“还不是问我些想法,把他女儿嫁到我们家吃苦了呗。”
彭兰香这个时候终于插上了嘴,“老人家的心里不就一个想法嘛,自己已经年纪一大把了,还图个什么奔头?真盼着享清福啊?还不就希望能看着子孙后代安安乐乐地过日子?我也不太乐意见你一个劲折腾,不如老老实实地读书,再老老实实地找个轻松点的工作,把琪琪娶过去后,俩口子好好打理好小家就可以了。”
彭兰香的话勾器了叶理内心里的无限遐想,放要酒碗正要感慨一番时,被见机快的叶文希打断了,“哎,事已如此,不如既来之则安之,既然当了农民,捧了这个饭碗,就得把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抛掉啊,别捡不着西瓜又丢了芝麻啊!”
叶理见儿子说来说去就是拿话堵着自己的嘴,只将那酒碗端起,用纯正的胡子酒将满腹的牢骚沉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