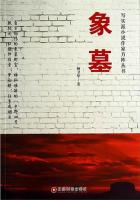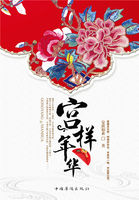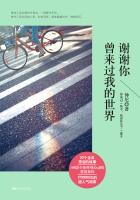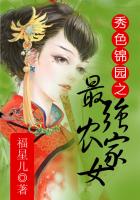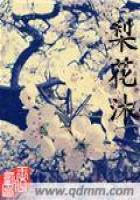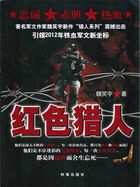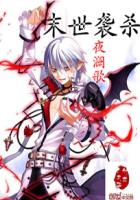抢运水泥
愁云惨雾的孩子们被安排在洞外工地备料筛沙子,就是把沙子里的石块和杂物分离出来,筛沙子可能是隧道建设中最轻松最简单的活了。孩子们一动弹就明白他们的这身装束是什么也干不了,纷纷脱去那累赘的雨衣雨裤,支起二三个筛网干了起来,一个筛网也就是容下三四个人干活,加上指导员又在场,一个个争着表现,插不上手的孩子靠着山崖或倚或坐。
军代表万涛歪戴着个安全帽来到了工地,他已经到隧道里转了一圈出来。军人里面,孩子们也就是对他最熟。当他和指导员拉呱的时候,大多闲得无事的孩子们自然围了上去,从万代表的口中,孩子们知道,这次大塌方是在隧道进去的30米处。
“完了,这下卡了脖子了!进度要受影响了,不过,邓营长在亲自处理塌方,他在成昆线上是出了名的处理塌方的专家,那时候他还是连长,我还是他手下的战士……”万排长跟孩子们侃起了“大山”。
山里的天气说变就变,本来就没有怎么晴起来的天,竟然飞起了雨丝,山风说来就来。一位4个口袋的军人从营部跑了下来,冲老万招手,过去说了些什么,只听老万说,一定要有车。那军人说:好吧,调两台车。说完便匆匆走了,老万又跟指导员说了些什么。宣布任务才知道,要下雨了,要孩子们去把山下码头上的水泥运到山上洞口边的水泥蓬里。那一袋水泥是50公斤,100市斤,孩子们初来乍到,哪有那体魄承担那样的重量,累死也没有几个人背的上来,万排长清楚这一点,所以坚持要营部的调度派车,这样孩子们的任务就不是背水泥而是装卸水泥。
老万让指导员带着筛沙子的孩子留在上面准备卸水泥,他带着其他孩子顺着石庙废墟边上的小路直奔山下码头。船上的水泥如果直接卸下来装车,就节约一次体力搬运,那车辆的调度就要非常及时,因为船也想加快周转,比如今天船要运伤员去医院,水泥是突击抢卸下来的。石庙沟的码头是公路和江边开出的一块沙子地,那码头上的沙子估计是经常运沙料时遗留下来的,大约有几吨水泥堆在江边的沙子上。老万和孩子们刚到一会儿,那“解放牌”就“轰隆隆”地开过来了。这种“自力更生”造的车,那声音是“一流”的,也经得起折腾,就是方向盘太重。在这里开车真要水平和力气,简易公路是在峭壁上凿出一半,然后用凿出的碎石填出一半,所以公路是一半实一半虚,一半硬一半软,也没有什么回旋余地,一转弯就是180度,方向盘要打死,要不就窜到江里去了,这样的事已经不只一次发生;最怕大水一来,虚的软的都冲到江里去了,车开在那半条道上,真像在“栈道”上开车了。30多年过去,那也是用“钻爆法”而且是用“钢钎和炸药”干出来的,曾经车来车往走过千军万马、运出个襄渝铁路来的公路竟成为汉水山壁上的一抹乌痕,连一只羊也走不过去了。
“解放牌”尽量倒到离水泥垛近一点,但也有十几米远。老万安排两个个高一点的孩子到车上去接水泥包,自己和另外一个大一点的孩子在水泥垛边上往孩子们的肩上放水泥包。这时带了雨衣来的正好把雨衣披在头上,雨衣这一下可派上了用场,免得一头一脖子的水泥灰。孩子们自然形成队伍,一个个用肩背去接那水泥包,有几个个小的腰都压弯了,好像不是背过去,而是半驮过去。轮到江西了,江西能不能背动那100斤看来是没有把握,他的体重才有77斤,正好是秋初积背回的石炭的重量,他确实有点勉强地走过去,“班长啊,还不快一点!”那老万早看出来了江西的为难,就话里有话地说,江西咬了咬牙把肩背送了过去,江西背着水泥往前只走了两步,就一个趔趄,差一点向前栽倒,水泥包从他的头上甩了出去。没有人笑,两个孩子去抬那甩在地上的水泥往车上搬,江西似乎在强忍着泪水,他悄然地又排在了队伍后面。公鸡过来把他挡在后面,背完水泥的孩子排队时都很友善地让过他,插在他前面,这样江西和那水泥垛永远是等距离,不用再去“甩水泥包”了,这真让江西感动;尤其是大山,自江西甩掉水泥包后,每次都要老万往他的背上放两包水泥,好像要帮江西背一袋似的,江西感动地看着他,他就给江西挤眉弄眼,江西几次都想笑出来。但江西不知道“冤家”周东会怎么看,会怎么想,会不会幸灾乐祸?幸好他在洞口筛沙子,抢着“表现”,没有下来。
3天后,江西被免去班长“职务”,江西如释重负,他想起被“打倒”的父亲经常自嘲说的一句话:无官一身轻。
邓营长不愧是治理塌方的高手,他带领一帮老兵一边从正面一点点往前拱,弄出一点空间就用大木头顶住,排架的横梁竖柱都是一抱粗的大木头,一根挨着一根,密密匝匝,木头之间又都用扒钉钉死。俗话说:立木顶千斤。走进那抢险出来的巷道里,就像走进全是千年巨树的森林,密不透风。谁进来了都会想:这样“固若金汤”,不要说是塌方,天塌下来都能顶住。另一组织突击队从左边打一个侧道过去,24小时不停地往前打,侧道的高度为两米,戴安全帽的大个也可以轻松走过去,宽度也是两米,正好过一台矿车,一个半圆形的弧度,打了一个星期,打出20多米,又打回到了主巷道上,然后一面继续往前打,赶进度,一面往后打,两面夹击塌方区。
这样从时间进度看一点都没有耽误,只是多花了一些人力,多打出一个侧道。那侧道又为这一段提供了双轨,加快了这一段的“出渣进料”的速度,没准那侧道将来还可以当铁路工的工具间用。更让人称道的是邓营长决策从左边打侧道,而不从右边打,从道理来说右边更接近山体中间,岩层更坚固;还有邓营长怎么知道打了20多米后就能绕过塌方区,这是巧合,还是他的经验所至,反正“与地斗”,他赢了,他的嗓门更高了,什么时候他都敢叫敢笑敢骂,这也许就是打隧道的铁道兵的性格,试想在风枪声里,在隆隆的开山炮中,你的嗓门能不大吗!
大概半个多月后,“卡脖子”的地方已经打通,学兵四连的学兵们终于被派到了“掌子面”上干活。虽然雨衣雨裤不穿了,但脚上的长筒胶鞋和头上的安全帽是少不了的,“趟水护头”这在隧道里最起码的,这个习惯大多数人坚持到最后。初次进来的时候他们是异常地小心,基本是把洞壁上悬吊的每一块石头都看过了,敲过了,才放心埋头去干活。
又过了半个月,孩子们完全掌握了掌子面上的施工技术,基本不用军人指导,可以独立施工了,而且按照个子大小,身体强弱,反应快慢等进行了分工,打钻的打钻,扒渣的扒渣,推车的推车……。孩子们也老练了,也变油了,也没有那么提心吊胆了,干的热起来,连安全帽都取了下来了。正在修筑的襄渝线像一根红线,把汉水北面的青山像碧玉一般串起;两边的山影都倾泻在汉水里。真不知道是绿水染青了山,还是青山染绿了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