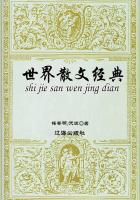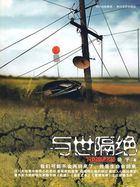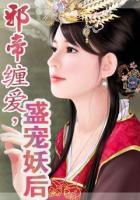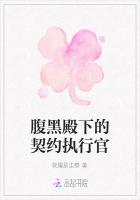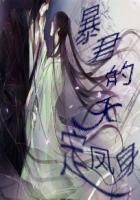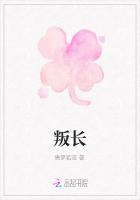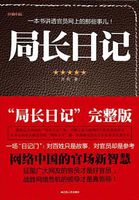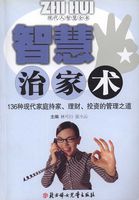恰若青石街道上难免有凹凸的娘印,正如浪飞涛打的浅滩边总是有受侵蚀的礁岩,正如碧若深海的空中总是有丝缕云霞的纠葛,正如滚滚汤汤的史河之中总是有被研碎的残骸一般,我,在夜半无人时,自言自语,自感自伤。
生活,有时不得不在过于高涨的情绪之中加一点杜冷丁镇痛并目,镇静。笑着看天,看云,看我身边的每一个人,到头来却发现无法昧着良心在这夜半无人之中对身边自己的灵魂绽放一次哪怕违心的笑,可悲吗?或许仅仅是无味到麻木。
有时会向往《喜马拉雅星》中的那个传奇。在印度,人们将天神看成一个褪袱中的婴孩,它天真地沉睡着,梦中缔造了一个世界,一个由简单到繁杂到匪夷所思的世界。也就是说,世界万物,林林总总,仅仅是一个天真的婴儿的梦。如果有一天,它翻身睁开惺松睡眼,开始啼哭,世界便会于这一刻起消失并且从头开始,陷人天神梵天婴儿的另一个梦境。人类从爬行开始,重新来过。
相较于世界时空无限的理论,我似乎更倾心于这种幻想。毕竟,在一个孩子的梦中运行着的世界,更天真,更温暖,更会溢满希冀,也是可以重新来过的。将这些条件加在一起,就是理想、梦幻与希望的殿堂。
在难以找到自我生存价值的今天,我想到了逃避。但由于本人能力与经费的缺乏,再逃,范围也仅仅是一个狭小的空间,叹曰:打不起我连躲都躲不起。
生活呀,你要我如何应对?
不由自主地在消极中沉沦,以至于找寻不到活着的理由。记得初中时语文老师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人,为什么活着。”于是乎全班同学讨论纷纷,诸如为人为民为国家,为天为地为世界者不胜枚举;为己为乐为忧愁,为志为心为生存者也可圈可点。
但最终,老师不予评论,只道:“对于某种客观事实总没有讨论之必要性,活着了便活下去,什么都不为,便什么都为了。”她这一番话讲得波澜不惊,我却久久地回味着,每当我再次向自己提出同样的问题时,窃来回之也无妨。
活着,本就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正如余华所写《活着》,由一辈子的纷纷扰扰到头来归于一片死静。这静,的的确确是死所造就,却又仿佛含了八分哲理味道。于是这个问题又深一层,深到我揽臂难及徒叹空余。
草叶活着,吐纳空气与阳光,便是活;
树林活着,盘根错节一片土地,便是活;
小屋活着,吐人吸进一方缕烟,便是活;
溪流活着,叮嘱吩咐一瞬间,便是活。
活着依旧被诊释成为最为简单的生存方式,仅仅是为了活而活着,就像水有了鱼而懂了什么是泪;山有了风明白什么是凉;
暗夜里有了星星,才发觉什么是盼;瀑布上空架上一道彩虹才知道什么是瑰丽绚烂。活着就是去发现去有所感,活着就是去追逐繁盛背后的清冷,漠然身旁的沸腾。
不觉之中,已在笔尖开导之下走出阴影,畅然而来。不得不说,书写通常也是一剂良药。当你身心俱疲时,给你镇静也给你安然。恬淡的心境,夜半,一点一点地走出阴暗的地牢。在前面,是明天的路。一路走好。
2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