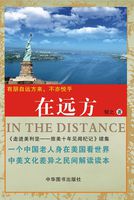想一品《霸王别姬》是许久以前,甚至是许多年前的梦想了。然而也许当一个人认定某件事将会是他的梦想之后,就当真把它奉若神明,认定那便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了。子是,尽管我已不再有机会在这个老片过期永不上映的年代坐在大银幕前品味,我也不再有兴趣自寻这场戏了。
然而越是长久的酿品越是醇厚可味。很偶然,我在网上翻到这一页。于是,京戏、霸王、程蝶衣,这一场古老的过时的邂逅,震动了这个季节的孤寂。
如果说看过《无极》之后会大加感慨其商业的浓重味道,那么在看过《霸王别姬》之后则会大为疑惑陈凯歌的作品为何都会如此之长(3h)?进而要加上解释:长但并不冗。这一切都很自然,极完整,有始有终地像一次最深层的吐纳。只是当你生出那最后一丝气体之后,全身仿若又有新血液了。
京戏、猫王、程蝶衣。这三个人或事物是那么近,又好像是千里万丈地远隔。霸王属于历史,京戏属于艺术,而程蝶衣只是原原本本的一个虞姬。
“多年来我随大王东征西战……而今四面楚歌,把那生灵涂炭。”转身,泪眼迷蒙,乌江之畔。他用一曲清歌洗了自己一辈子的希望与迷茫。打从小豆子中鲜血浸出来那一句,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开始,他的奢想便全是一个虞姬。而虞姬为何而存在?只在于乌河之畔葫王宝剑之下那一声”去了,那一朵血莲绽放。段小楼一句“我是假霸王,你是真虞姬”将这一层迷乱点破。是然,程蝶衣不疯魔不成活,自是作了女娇娥,那便是一辈子如虞姬一般地从一而终。他痴为谁狂为谁?不尽是为了那童年时的大师哥,戏台上的楚霸王,更是为戏本身,为京剧的唱、念、做、打,一字一句一音韵而狂热痴迷。
诚然,这只是一场戏,若人生只演一场戏,又未尝不会是一场曲终人散的悲剧。他苦撑着一回又一回地品这场悲剧,只为了某一天可以得到一个答案虞姬为何要死?一次又一次,在台上,他为楚工挥泪,为箱王饮颈血,不如说是他为自己的一生吞咽着泪水,为自己的命运支持着最后一句念白。程蝶衣,不是虞姬。虞姬不会一次又一次地选择生与死,而程蝶衣的苦泪却将熬成一帖浓药,烧着人心久久难愈。
除了程蝶衣的一句句戏词外,时常回荡在耳边的自然是那位西楚霸王的一句“妃子请了”。段小楼演绎的西楚描王无疑是一个英雄,然而在这部戏中段小楼本身是令人不解的。他仗义,打从他还是那个叫小石头的小戏子起便是了;他无畏,与国民党残兵相斗,血把那脸谱的吊眉稍部染成绛紫。然而,其后呢?解放后的他为了所谓的端正风貌,将京戏变成了不伦不类的现代戏;
文革时他为了保全自己,在“牛鬼蛇神”的重拳之下将蝶衣的日伤一一揭开。他也曾斥责蝶衣为日木人唱堂会,却到后来连对自己妻子的承诺都如弃草芥。我若是蝶衣,我也会鄙视他。然而我若是他的妻子菊仙,我会将这种无骨的人在心中永远埋葬,权当作从前的猫工已在乌江自勿9而去,余下的只是个馅上媚下的高力士罢了。可菊仙没有。刀卜个曾经的青楼女子而对一切,一语不发,含泪,着嫁衣,自缴而亡,像一朵自始至终盛开的杜鹃,火一样,焚成了另一个虞姬。
其实当蝶衣在那场贵妃醉酒的旋舞绽开,这个人物的悲剧就已显露无遗了。台上人影不见,只余了一位贵妃;灯光,任它灭了又亮,她只是径自地舞着,仿佛天地之间便只有这一场戏。
如若这场戏恰在这个黑幕之下结束,则只是程蝶衣一个人的悲剧。然而这场戏勉强并顽强地演了下去,这便成了京戏的悲剧,亦是那个不为人知的义众所周知的年代的悲剧。
程蝶衣,就这样为了一个虞姬痴狂而迷醉。直至风烛残年,他才知“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却已应是人生写尽。
他最后引剑,低唱,自尽。于是灯光褪去,画而上只余了箱王栩栩的吊眉脸谱,眉梢耸立,兀自抽动着岁月的痕迹。
程蝶衣终于走了,然而此刻他已不再是虞姬,而是一个原原本本的蝶衣。
京戏是京戏,杨王是描王,虞姬却是程蝶衣。
昆曲《牡丹亭》惊梦一折,究竟惊了谁的梦?不得而知。然而,在闪烁着泪水的背后,那双迷失多年的眼睛,忽而被惊醒。
唤一声我是谁,四顾而茫然。
短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虞姬,然而若是明智,切莫忘了,要唱好自己的程蝶衣。
2007.10女讲得出动听而脆弱的誓言,但这句话于他是蜜,于她是毒。
没有硝烟的战场,漫着鹤顶红与毒蝎子混合的味道,洁自的毒粉藏在素手一指的甲缝中。那种致命的弹力,令厉帝真正地拜倒于婉后的石榴裙下。
“世间有比这还毒的东西吗?”
“有。”
什么?
是人心。
人心,是鹤顶一点砂,是蝎尾一弯勾,当它狂舞并无限地膨胀时,谁也无法确定它不会含着笑给你致命一击。
太子不会杀人,这并不是他剑术不精。他父亲传给他的剑术与越女剑贴身格斗的优势令他有着天生杀人,杀敌人的条件。然而他不会,因为他不够狠。帝王是定然要有坚如磐石的心的,因为在无形有形的撞击中,帝王必会与人相争。这时,轻则斗王位,重则斗生命。
“你愿意让出王位,臣妾愿与您归隐山林。”婉后娇媚地诱惑,皇后是要联的命吗?厉帝这样回答。
厉帝这时是一个真正的帝王,他有足够的占有欲与狠心。然而当他饮下那半杯婉后递来的毒酒后,他说:“你奉的酒,怎么能不喝”其实,他在说这句话时,即使不死,也已经不配做一个帝王,他的心已经被女人侄桔,成为奴隶。
《夜宴》中或许有太多不真实,但最真实的是欲望。人们如兽如洪如火如风的欲望,将太多人烧成了焦骨,也焚毁了太多人的希望。人有欲望并且不断使之成长为一种庞大的力量,这件事个不可怕,甚至从某种角度讲正是这种推动力使瞒珊的历史一次又一次跃过难越之渊。然而当一个人的欲望将他自己控制并且完全令他找不到方向时,这个人变成了一种由气体灼烧的气体拼成的物质。这种物质的命运会有两种,一是燃烧并自炸,二是炸毁身边的人。婉后将这两种结局囊括并创造性地加上了第三种结局一一失去全部的爱。
婉后如何死,这并不重要。如果片中真的将事实一一婉后的侍女凌儿抛出绳剑刺死她时的狰狞面目展现于剧尾,这部戏便是死戏,如舞者的面具中看不到真实的动人。而恰恰是一柄绳剑,一潭浊水,一片灰白的天,使这段历史没有被完全收尾,而是载了更多表情,未来,成败。
想杀婉后的人太多了,要杀婉后的人太多了,能杀婉后的人太多了。因此,不必仅仅将抛剑人当成凶手,世界的目光可以成为绳者。她的命运,必然会毁于欲望,希望婉后死了,当年纯真的婉儿会回来。
200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