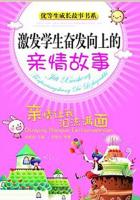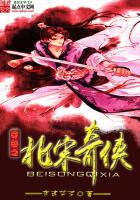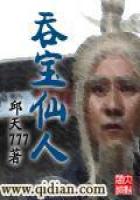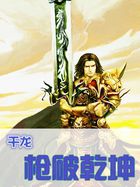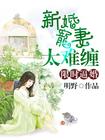其次,是承认社会现实存在的合理性,并在这种承认中,表现了一种对个体生命必然要被消损的深隐的内在的绝望。对社会现实存在的合理性的承认,我在前面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论说。这样的一种承认,在王蒙的小说中是普遍地存在着:历史中所形成的种种社会问题总不能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一下子就给以解决吧,既然不能一下子给以解决,其就有着现实存在的合理性吧(《春之声》《风筝飘带》);西方的科学知识在最初进入中国时,总是先从表层的生活层面发生影响,由于缺乏深层的社会结构作支撑,所以,也就往往必然地会以某种变形形式率先出现吧(《活动变人形》)。王蒙自言:经过了“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我已经懂得了‘凡是存在都是合理的’的道理,懂得了讲‘费厄泼赖’,讲恕道,讲宽容和耐心,讲安定团结。”其实,他早在写《年轻人》时,就懂得了这一道理,只是在经历了八千里、三十年之后,这一认识是更加坚定了。正是因为承认社会现实存在的合理性,王蒙小说的批判锋芒从来不是指向个人,尤其不是指向个人的道德品质,同时,他也不是指向某一个社会问题,某一种政策抑或某一种路线的失误。他的批判总是指向一种生成机制,指向一种不可避免的历史运行中的必然,要而言之,他的批判从来不是指向有形的具体,而是指向无形的必然,从而使这种批判外表温和却具有一种更为深刻的内在的批判力度。这是他比与他同时出现的及其后在新时期大量出现的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的小说都更为深刻的地方。当那些小说非常激烈地指斥路线的失误或者当事人品质的败坏时,虽然从表面上看,对社会现实对人的缺陷的指责分外尖锐、激烈,但隐含在这后面的,却也是认为这些弊端是可以通过批判而给以消除的希望,骨子里对社会对人生还是抱着一种理想化的态度。但王蒙的小说不同,在看似温和的后面,却深隐着一种认为这一切都是难以改变的绝望。面临着这种绝望,在步入无形的“无物之阵”时,鲁迅的态度是坚决地义无反顾地“举起了投枪”,但王蒙不同,他更多的是讲宽容讲理解讲妥协,他曾作过一篇反鲁迅之意的文章,叫作《论“费厄泼赖”应当实行》。与中国文化人对鲁迅的推崇相反,王蒙很少表示对鲁迅的赞同,他也并不完全认可鲁迅。他曾用其特有的方式表达了这一点:“文坛上如果有一个鲁迅,那是非常伟大的事,如果有五十个鲁迅呢?我的天!”王蒙之所以不大赞同鲁迅“反抗绝望”彻底批判不与现实妥协的精神,仍然是为他的双重身份双重立场中的坚持社会现实性,坚持社会的可接受性、现实的可行性所决定的。
再次,是呈现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及因之构成的人之生存的荒诞性。社会现实中种种的不如人意处,其产生的历史原因与现实原因,都不是人们在理性上所能一一给以认识清楚的。当人们从社会反映论的视角来归纳王蒙小说的主题时,往往对其作品所揭示、概括的社会内容及其意义发生争论,从最初的《年轻人》,其主题是否是反对官僚主义之争,到其后的对《春之声》《风筝飘带》的多主题、社会生活面面观的概括,再到《杂色》《活动变人形》的题旨的争论,无不如此,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此。社会历史是在如恩格斯所说的由“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组成的“总的合力”的作用下形成的,而作用于社会历史的运行的种种经济、政治、文化等等的多种因素,又不是我们能够一一认识清楚的,所以,恩格斯要用“力”这样一个抽象的名词来概括这些因素。王蒙的小说,在揭示与人相对立的外部世界时,正是对这“总的合力”的形象的整体展示,因之,也就不能用作为人对外部世界的某一认识成果的某一种理念来给以概括。正因为王蒙小说中的外部世界是不能用思想、理性给以清楚的认识的,所以,人生存在这一世界中,人的命运就不是人能够自己给以把握的了,并因之呈现出某种“荒诞性”:《最宝贵的》中的主人公蛋蛋,本意是真诚地参加革命,但却因之而出卖了真正的革命者;“季节系列”中的钱文,率先真诚革命,但在其后却被不革命者所改造;“天生革命家学生领袖”郑仿,在回想自己在反右运动开始及其以后年代的经历时,不可思议地感到自己走马灯似的变换着各类“人不人鬼不鬼”的角色:“一个每月十八大吊的准罪犯,一个堂舅家的食客,一个被分析的一塌糊涂又能随时把一切人分析个体无完肤的口舌如刀的改造者,一个改造的‘上游’,一个大跃进民歌的作者,一个犯了错误才发掘出诗才的新生活的歌者,一个偷大蒜的罪犯,一个被赦免的流氓,一个小寡妇的未婚夫,一个墓地上的逍遥客,一个猫头鹰的知音,一个初夏夜的田园风光的领略者”。《活动变人形》中的倪吾诚,在“历史”的“活动”中,变形为“老干部”“汪伪人员”“学者”;《蝴蝶》中的张思远在“老张头”“走资派”“张部长”中迷不知其所以,而重新有了“我为蝴蝶,蝴蝶为我”的感受。人在对外部世界与对人自身的迷失中,无法认清自己命运的走向,掌握自己命运的浮沉,人所作出的种种努力,却恰恰是对自己所预定目的的悖离,如此,人对外部世界所付出的努力就在忽然间失去了价值依托:人的努力毫无效果,人也不知自己努力的结果会是什么。当你感到了这一点,你还能对自己付出的努力充满信心么?
第四,退守自身。既然社会现实虽然总是不如人意但却又具有现实存在的合理性,既然外部世界是不可认知的并因之形成了人的存在、努力的荒诞性,基于上述对人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认识,就导致了王蒙是以退守自身来在个体生命与外部世界的不平衡中以求取平衡。这种退守是以下列四种形式来体现的,其总的价值指向,是沿着刘世吾所体现的价值向度给以展开的,是将生命的个体价值高于生命的社会价值的。
完善自我。既然看清楚并认可了个体生命之于外部世界的有限性,那么比较现实可行的做法就是完善自我,并尽力做到自己作为个人所可能做到的一切。如前所述,刘世吾赵慧文是这样,《风筝飘带》中的佳原则更为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点。佳原曾经经历了社会对自身的不公正:做了好事却被大家乃至受惠者所误解,不被表彰反而受到了惩罚,但他对此却毫无怨言。面对连人之生存最基本的吃、住、年轻人恋爱、治安都不能有所保障的社会现实,面对社会的特权、不公、是非颠倒、黑白混淆,作者却通过与素素的对比,写出佳原并不满足于应该说是合情合理地忿忿不平、埋怨与指责,而是首先完善自身,用知识充实自己。虽然个人所具有的这知识并不能在外部世界得到实际的实现,获得社会价值,但在佳原也就是王蒙看来,个体人生的价值、幸福也就在于此了,也就在于个体生命自身的健全了。用佳原对素素的话说:素素的社会地位可能不及中国驻阿拉伯大使,但她的人生价值却因此可以与中国驻阿拉伯大使相等。于是,对外部世界的实际改造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自己如何感知外部世界,是自我的完善,是“境由心造”,不是靠实际地改变外部世界,而是靠退回内心,从而获得个人的幸福。既可以不与外部环境发生冲突又可以使自己获得心灵的安妥,还可以使环境因自己的努力获得有限度改进。于是,不如意的外部世界就不是那么让人难以忍受的了,人有了一条自己应对外部世界与人自身存在的可行通道。
用逍遥的态度将人生审美化。既然外部世界是不可知的,人因这不可知而处在“被抛”状态,目的也随之变得虚无缥缈可有可无了,那么,从关注目的及其如何实现,转而关注过程及如何体验过程,从以目的为人生本位转而以过程为人生本位,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一种选择了。王蒙在他的另一部代表作《杂色》中,写尽了此种人生姿态。《杂色》如果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一个被命运偶然地抛出社会的可有可无的人,骑着一匹可有可无的马,去到一个遥远的无足轻重的地方,做一件可做可不做的事。面对历史、现实时空的辽阔久远,任何个体生命都是渺小的,命运都是无常的。于是,在这种渺小、无常中,人能做到的就是领略、体验个体人生之路上的各种风光,用这样的一种领略、体验的姿态,才能发现、体验到个体生命的存在。意义、价值、美,就在这领略、体验中而产生。读这篇作品,总让人想到周作人的《乌篷船》,周作人也是看到了目的的虚无,不再去计较如何达到、实现目的的功利,从而用一种审美的眼光浏览人生沿途的风景。
个人性的物质生活、世俗生活。既然消解了对外部世界的梦幻又时时地感觉到了自身努力的虚无,那么,最直接的就是回到看得见摸得着的个人性的物质生活世俗生活中来。王蒙的小说对个人的物质生活世俗生活有着足够的尊重:在《活动变人形》中,他写了物质生活如何制约着人的精神生活,在《杂色》中,他写了食物对主人公旅途的不可或缺,在“季节系列”他多次浓墨重彩地写了在京城在边疆钱文的日常世俗性生活,写了浪漫的“刘芭”如何成了“事儿妈”,写了物质、世俗生活对几对青年人基于精神、理想而缔结的婚姻的解构,写了正是注重个人性的物质生活世俗生活的钱文的妻子,较之钱文等人的从“恋爱”到“失态”“踌躇”再到“狂欢”的与实际生活脱节的精神的三番五次的折腾,有着更多一份的清醒。也正如某些论者所指出的:王蒙在作品中“大量地运用躯体性、物质性的意象”从而构成“对于人的日常生活与常识理性的肯定”。也正如某些论者所指出的:王蒙在作品中写了钱文“对有别于理想状态的现实生活,有了新的理解,新的评价……世俗的琐碎生活,忽然升值了,成为他在‘文革’中最为可贵的记忆,成为他生命中永远的怀念”,成为“他的后半生意义重大的不平常只因为太平常的日子”。这与其说是王蒙对钱文的描写,莫如说是王蒙的夫子自道,个人性的日常的物质、世俗生活,之所以成为“意义重大的不平常”正是因为其“太平常”。正是通过这些描写,王蒙写出了物质、世俗生活在个体生命中的意义,写出了脱离个人性的物质、世俗生活的革命、崇高、精神神圣的虚伪性,并由此体现了王蒙在其“后半生”对于革命、精神、崇高与个人日常性的物质、世俗生活关系的重新思考。王蒙在后来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中,注重个人性的物质、世俗生活在人文意义中的构成作用,正是他这一重新思考的延续,只是他的这一思考,更多的是面对过去的历史,较少面对市场经济大潮下物欲泛滥的现实。
幽默与反讽。论述王蒙小说中幽默与反讽的文章已经很多。就人生价值指向而言,则体现了王蒙在面临绝望退回自身后的面对外部世界的主观的精神姿态:在王蒙那里,幽默是内庄外谐,泪尽则喜,是人面对自己无法改变的外部世界在精神上战胜对方的智力优越感的显示,同时,幽默又是人与外部世界得以和谐相处的一种方式“你能什么东西都声讨吗?未必是好办法,也不可能。那么,我们通过幽默,既表达了人们的愿望,又表达了一种宽容”。正是在这样的可以称之为“黑色”的幽默中,王蒙既体现了对外部世界的决然批判的否定态度,又让我们在其中看到了刘世吾对外部世界“就那么回事”的嘲讽态度的影子,也可以看到其后王蒙在对王朔的赞赏中,是有着其内在的认同的。
对于王蒙小说中所体现的个体人生价值指向,我们可以认同,也可以不认同,但作为一个时代给我们留下的价值标记,却是值得我们不断地给以重新审视的。
从“山药蛋派”到“晋军后”——山西三次小说创作高潮之再审视
自上世纪40年代以来,在60余年来的中国小说创作中,山西的小说创作,曾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以成一、李锐等人为代表的“晋军”群体,以张平为代表的“晋军后”创作,三次规模不等、程度不同地影响过中国文坛。这三次影响,“山药蛋派”的小说创作,因其时间的沉淀,已经成为具有“史性”意义的话题,“晋军”及“晋军后”的小说创作,则现实意义更为突出。但无论其“史性”意义还是其现实意义,二者之间却又是血肉相连一脉相承的。山西小说创作之所以能够如此,有着其内部与外部的各种各样的原因所在,值得我们花大力气给以一次次地认真的探讨,本文的写作,就是基于此的一次努力。
一在上述山西小说创作对中国文坛的三次重要影响中,“山药蛋派”的小说创作无疑是其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程度最深的一次。
让我们先从根据地文学说起。根据地文学形态相对于国统区、沦陷区文学形态而言,是一种全然不同的文学形态,并直接地影响、开启了其后的共和国文学。宽泛地说,根据地文学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学形态,自井冈山红色苏区始,至建国之日终。但姑且不说红色苏区的文学尚不成熟,既以抗日根据地及解放区的文学而言,尽管其时比较着名的抗日根据地及解放区多达十几个,但不论哪一个根据地或解放区,从真正体现了根据地文学形态、创作实绩方面给以考察,都无法与以“山药蛋派”小说创作为主体的山西根据地文学来一争高下。
不错,陕甘宁边区是根据地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根据地文学的中心,但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具价值的,却是在文艺思想的冲突方面,在五四文学谱系进入根据地之后的演化方面,如对王实味、萧军等人的批判,如丁玲文艺思想的转变,如《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等作品的出现等等。当然,贺敬之等人的《白毛女》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柳青的《种谷记》欧阳山的《高干大》等确实是陕甘宁边区根据地文学的丰硕成果,且这些人的创作,在建国后,在根据地文学与新中国十七年文学的一脉相承上,也仍然属于体现实力、实绩的代表性作家,特别是柳青,他的那部《创业史》,堪称是根据地文学与新中国十七年文学一脉相承下来的集大成者,但在根据地时期,上述这些丰硕成果,毕竟是归属在赵树理的“方向”“旗帜”之下的。
不错,孙犁等人的创作,确实体现了冀中区根据地文学的成就,但在创作队伍的阵容方面,那还是不能与山西根据地其时已经成形的“山药蛋派”的创作队伍相比的,且孙犁在建国后的50年代中期,即已经基本上停止了自己的创作,以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的文学创作,在新中国的文学格局中,其分量也是不及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的,就是说,在体现根据地文学对新中国文学的影响上,冀中区的根据地文学是不能与山西根据地文学相比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