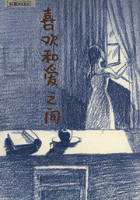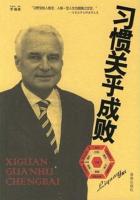敦煌,去城十里有座鸣沙山,沙山下一片泉水,叫做月牙泉。
早在尧的时代这儿就生活着三苗人,先秦时还有羌人、月氏人。别看大漠连天,这方风水盛哩!W唐以下,名门辈出,张家、索家、曹家、阴家,累世簪缨,旺族传代,至今莫高窟功德洞里泥塑壁画尚存着这些家族的痕迹。
现在这方仍有不少曹氏阴姓的,就不知道与那古时候的姓氏有啥因袭没有,只晓得解放前阴家人在这达是有名的地主大户,曹家几代贫穷,为阴家雇工扛长,拉胳骑养马。直到“土改”阴家才败落了,曹家的老人当了贫协主席,儿子孙子当了村长乡长的。这阴家桥的地名也改为曹家桥公社。这公社管辖着五六个村子,可说是日月清平,沙海子绿洲麦禾黄黄。
可是这一年,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娃子!赶紧往沙山上跑!把那口袋粮食抱上一!”
叫……大水……
没了腿,再淹到腰。千百亩麦田秋苞谷,全没了田禾梢儿。水面上只露着一排排杨树冠和一家家房屋顶,还漂着些个死尸活人。
鸣沙山沙坡沙梁爬满了人,爬上去又滑下来,沙顺腿窝流淌。一时间果然听到那“嗡一嗡一”的沙山鸣响。老的小的,分不出哪村哪队,捂脸哭嚎,谁家的婆姨扯裸着胸膛,奶着娃子。
这时,只见曹月泉衣裤全湿,挂满泥沙,一步一滑由山下爬上来。背上背着个七八岁的,胸前挂着个刚断奶的,两个娃子都不是他的,他没有这么碎小的。
人们啾着,也不作声。
他仍向上爬,腿兮兮个不听使唤了,呼呼喘着粗气,扑通一下跌倒,两臂又撑起身,脸颊上水还是汗,粘着沙粒。
他静静地啾啾黑锅底似的一片老少,啥话也说不出。背上、脖子上吊的娃也忘了放下身。
呆愣了半晌半晌,才有人发出声音月“月泉一,唉,月泉……”
转眼山下,一片汪洋,家家泡在水中。往北啾,中关村、沙井村、城关村,唯独月牙泉村在最南端,地势最低。
仿佛这会子人们才得些空闲,悄悄议论,党河水库决堤了!
这党河水库就在敦煌县城西去五十里处,每年从祁连山来水两亿九千万立方米,全县农田水利全靠它,当年数万民工在那达建坝筑堤花了小十年工夫,咋会说崩就崩塌了哩!听说敦煌城三分之二已在水里了,县委县政府了……水,的的……他脊背上、脖子上仍吊着娃子,直到那些娃子的亲娘跌抢上来,哇一地一声痛嚎。
“月泉,你自家咋不去管顾……”那女人哭说,“你家容容,和她娘咋样他啾了一眼,已辨不清自己的家在哪达。
曹月水扯着他的丫头小乔,不远处站着,“唉,你看看,你看看……”只是这样哭说着。他的两个儿子一个也没有让出来,让他们在院里死守,说:屋塌你们就随着一达里死!屋若不塌,院里的木板、木条少一根,我回来也要你们的命!此时他叫了声月泉,抱怨地流着泪说修个妈日的水库哟!早有那工夫,不如在咱家门前拦条坝!”
曹月泉像没听见他说的话,只抬起手在小乔丫头那湿溜溜的头发上捋了捋。沙山坡上,几片破羊毡,碎娃子坐在毡上,边上晾着一簸箩馍馍。曹月泉蹲下身,再也站不起来了似的。仰脸瞅瞅众人,只说了一句没啥。水,坦个几日就退毬了……”
果然,几日后水退了,许是地处沙山自有它的福处,多大的水也能吞下肚去。日怪,月牙泉村的房屋在水里泡了这多日,竟也没像县城那钢筋水泥的建筑那么易塌易落,大部分完好如初。塌落的,不几日也抢修起来,曹月泉拨了专款,购砖买瓦,组织民工。曹家桥公社各村的田亩,那泥浆、板结龟裂的土地,不日也全面地清理整饬,不分哪村哪队,大拖拉机十几台,见地就耕,见田就犁,往日的地埂子地界一道儿也不剩了。妈日的那田亩,添了几分水力、肥力没啥不好,平展展一望无际。曹月泉多时不回家,干到日落西山,方才把件汗垢厚得像铁片似的衣,肩头一搭,去了公社大院。
当曹家桥公社各村各队的救灾工作已全部结束,这汉子却在一日大早,离开了地处中关村的公社大院,永远离开了。出了院门沿公路向南,向他早先待过的月牙泉村走去。
他被撤职了,不再是曹家桥公社书记了。身披着那件藏青色呢子中山,里了的。那件,麻袋片差不多,早没了毛毛,尽管平时穿它很爱惜,公社级的干部都披这么,去县里,就。
朝南走,望着了沙山,沙梁子长长的,峰刃刀似的,难怪这山有名,晨曦中瞅它格外清亮,瞅得人眸子发酸……打从土改,他爹就在这沙山下奔劳,不多久,他接了爹的手,领导村上的老少,垦田,骆驼拉犁,锨把子挖坑栽树,沿公路这些如今老高的白杨都是那时候栽的。田,一块块都得栽树围起来,防沙挡风的,粮食才上去了。后来还修渠,建水库,就是那决了堤的水库,国家投资才八百万元,还不够买些钢筋水泥,劳力全部是义务派工,曹家桥派去的民工人数最多,开山炸石,凿岩挖洞,那掘进泄洪洞的三大队就是他带的队伍,他,脱光了身膀,站在石洞的泥水中,顶上时有坍塌,他没有被砸死,后来还让他做了整个水库工程的副总指挥……发大水后,县委陆书记下台了,曹家桥这杆旗咋能插得稳哩!陆书记也革命一场,辛亥年间他爹便参加了祁德隆领导的闻家圈起义,起义败落,死里逃生逃到敦煌,才给他起名叫陆鸣山。土改那会子陆鸣山便是这儿的工作队队长,斗地主分田地都是他领着干的,直干到六十年代做了县委书记。说发水在的,防指挥部三地打请示他,他终不同意放水,说放了水,来年天旱咋办。他是让旱情给“旱”怕了。当他连夜乘飞机赶回来,敦煌已是一片汪洋。说仅县城一处造成的损失就达三千六百万元。可谁没个闪失啊,这时候就没人念他年年四乡察看旱相,建水库修水渠,主渠五十公里长!全县二十多万亩耕地水利配套……曹月泉尚未踏进村口,公路上遇见曹月水。
这木匠又去干私活了!领着他的两个儿子,大森和二林,各自身上挎着工具箱。嘿,妈日的,他活了!
早先,曹月泉不论是当月牙泉的大队支书,还是做公社的第一把手,曹姓人没个敢胡乱跳弹,大家一心扑在集体的田亩上。而曹月水跟月泉不是一个爷的孙子,妈日的这木匠的品性不知像哪位爷!偷偷摸摸净干私活,曹月泉整治过他,可仍改不了离村进城。有几次去他家,他那斧子刨子来不及往墙角角里塞躲,那时月水的女人还活着,嘻嘻笑迎上来,“月泉兄弟来了,快坐。”柳树下坐下,瞅瞅他那一院高高大大的宅子,说是“他爷留下的”,嘿,曹家的哪位爷也没置下这样的屋!哼,吃喝着渠水不知道水是哪达流来的!可也不能总板起脸训斥。木匠忙把酒杯摆在柳树下,兄弟俩喝着聊着,“月水呀,你不能队里的活苗青麦黄不管不顾……”‘‘呵呵,是哩,是哩。”他也应承着。
此时,月水的两个儿子老远见他走过来,仍习惯地往爹的屁股后头躲,月水说:“躲啥,朝前走!”直走到曹月泉脚跟下。
大森、二林低头抬头地叫了声“叔”,问候着:“叔回家了?”
“嗯,”月泉答应一声,眼睛啾着月水。月水也啾着书记。曹月泉下台的风声早就吹到了村里。两人半晌没有做声,那眼眸子反倒潮漉漉起来。
书记想,许是我这多年管束他错了!也怪难为他,女人去了,自己带着俩儿一女。现今,大水后他的活路正逢时。曹月水想,月泉兄弟也够委屈,苦了小半辈子又回村了!许是我带累了他?真的,见他下台,他心里挺不好过,便主动带着两个儿子去他家修缮房屋。回去吧,兄弟,回家看看你的门窗,我都给你换成新的了。不是我曹木匠帮你修修,你连个像样的窗户都没有!
末了木匠干咳了两声,说回来就回来,没啥了不得,好在你还是咱村的支书嘛!唉,天时地利,天随地转,听各处吵吵说,就要分田单干哩?”
曹月泉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曹月水大院一日比一日红火,庄外十里能听见锯声、刨声。
院中一棵老柳树,得三人合抱,郁郁葱葱,叫作啥“左公柳”,说是上世纪左宗棠率军讨伐俄国人和叛贼阿古柏时,路经此地留下的种子。锯台刨案就搭在老树下,大森二林扯着锯,小乔丫头提罐罐熬木胶,收拾收拾零碎,曹月水则大刨子花刨子来回倒手,精工细作。
曹木匠最拿手的活计就是古式门窗,廊檐帷子套拱斗。敦煌远近找不出第二个人。门一折四扇,门上镂窗,窗棂上叠套山水花鸟,如那四屏画儿。河西道上大凡文物保护单位修复个古刹旧庙的,都跑到他这儿来订货,一副就是好几千元。敦煌城乡私人造屋,上梁立柱,唯买到一副曹月水的拱斗,那屋廊檐。
除了古式,新式也做,青年娃子们结婚用的大衣柜、嫁妆箱,农家屋里摆设的米面柜、炕柜,那个做工,拉进城不愁销路。
曹月水家干木活历史悠久,说是明朝祖上便修建过嘉峪关城楼,在那木工坊做班头,不知真假。而他爷他爹盖阴家大院盖出了名却是人所共知。当年,劈里啪啦一阵鞭炮响,四乡八寨的豪绅都来观望阴家大院落成,吔!老远先啾见院门楼,盖得比瓜州城的古牌坊还神气,门楼正中一块匾,镌刻着“耕读传家”四个字。月水的爷爷披红挂花站在门楼下,阴家的爷一旁抹着喜泪珠儿,说曹爷呀,马过留鸣,雁过留声,这牌楼也是你木匠家的碑哩……”进得大院再瞅,那座上房,光石台阶就七八层,登上廊前榭,四根廊柱撑着探头屋檐,檐角高翘,檐下铜马叮咚,檐上龙飞兽走。时逢夏日,燕子啄泥,在斗。
噢,这座宅院不是别处,正是现在的曹月水大院。
嗞一嗞一,刨声锯声响着,在那廊檐子间回荡。
木匠朝俩JL子喝一声墨线瞅端,斜了狗日的!”
这已是发大水后的第二年了,这宅子一些儿水印印也没留下。相反,旅游业兴旺了,来敦煌的中国人外国人瞅罢了佛洞子,准免不了也到曹月水大院啾上一眼,好像这达是个“景点”,妈日的,说,咋院门楼匾上写的是“耕读传家”,进院一看尽是些锯末子刨花,没有一丝书香气。“嘿嘿,是哩。”曹月水一笑。那外国人仍免不了照相机子劈叭一顿乱照,还跟院主人曹木匠合个影,就站在那座古宅子下面。
院子东西各排厢房,大森和媳妇两口儿住东边,一林和小乔住西厢屋。连着院门楼还有一排屋,坐外面里,叫作“倒坐”。倒坐东是厨房,倒坐西像是门房,住着一位外姓老人,早早晚晚为院主看家护院。
尽管曹月水没了女人,可在旁人眼里他并不冷落。尤其是在那位叫作“七爷”的外姓老人看来,每每叹羡地望花了老眼。嗯,天时地利哟,看来是到了曹木匠发迹的时候了!这外姓老人别看一把老骨头在这达混口吃食,他少年读过诗,念过佛,天文地理无不知晓。他记起这瓜沙诸州远在唐宋出过一个大人,曹,曹这,人人,名门大户无不降服,一览河西四郡十州,只闻驼铃叮咚,不见胡马悲鸣,羌笛怨柳,敢莫月水家又应了这气运!
七爷坐在倒坐西屋墙根下,晒着太阳,说:
“月水侄儿,近来你的生意大发喽!”
“嘿嘿,七爷一,也是托你老人家的福了一”
曹月水大声应着,怕他老人家耳背。
“哪里吔,是你的木活精到哩,儿女,也跟上来了!”
“唉,哪个是跟上手的哟!二林时间短,可大森跟我十多年了,到现在花刨子不会使唤,榫卯对不端,合缝合不严,要是我爹活着,骂我们这些儿孙哩“呵呵呵……”外姓老人笑着,眉眼虚眯着。
他爹曹万根,是六十年代上没的。早年万根跟他媳妇都在这院里给阴家做佣。那间倒坐东屋,万根媳妇常从那达出出人人,媳妇年轻,生得几分颜色,为厨造饭手也灵巧。曹万根光为阴家做拉肥的大轱辘车、乘人的轿顶子车就不知做了多少,阴家堂的亲的家家用的都是万根做的。敦煌城西,白马寺那边有一处阴家宅院,那前廊拱斗木帷子跟这边老宅没啥两样,那就是曹万根盖的。可就是那次,曹万根被差到西边做工的时候,这边出事了,万根媳妇被人沾了手,一日,她吊死在那间“倒坐”中……也许是一种补偿,土改时把这宅院分给了曹万根兄弟们。早先这院住着他兄弟几家,后来分开了。此时,大森媳妇走出倒坐东屋,喊一嗓:“爹,饭好了,吃饭吧!”
小乔便先放下手里的零碎活,跑进厨屋端饭。饭就摆在院中柳树下,燕子低飞,一掠一掠的。一家人围着那张矮桌,还有那位七爷,几碟儿青菜咸菜,馍馍就上,再有碗面汤一喝。月水啾啾儿女,想想七爷说的那句“儿女们也跟上来了”的话,心里宽慰慰的,似也忘了娃的娘去了多年的苦楚……比比旁人家的娃,他的娃就是少读了几年书,除此没啥不如人的。月水这样“奔”,还不是为儿女们“奔”个门脸?他有时想,把大门楼那块匾换一换,或是摘掉,可又觉着留着它也体面,外乡来个联系活路的,进村打问曹木匠家,回答者说:“噢,好找,门楼前挂着块匾一”
他啾啾小乔丫头,更记起人们说,“咦?那丫头,满村唯她俊倌,她爹日弄木头,咋日弄出那么根‘乔!你瞅,从那大门楼走出来,就像个大户家的闺女。”月水心说,日奶奶的,走着看,几年后我丫头是不是“大户的”也要你称呼她“千金”哩!
近年,是人们瞅他的丫头长得俊俏,还是瞅他这大院一日日红火,爱来他这院的人多了起来。月泉家的容容常来找小乔玩耍,进门先叫他一声“伯!”叫得亲亲个。
“容丫头,学校里忙吧?你可有些日子没来伯这达了!”
容丫头读了高中,说话腼腼腆腆。高中念得不错,她爹虽然下了台,可还是托得上老关系把她安排在中学当了教师。
她往伯那刨台边一坐,手指捋着一卷儿刨花,说学校里倒是不太忙,可伯这JL忙,来了怕打搅,乔妹子也不去我家走动走动。”
小乔把茶杯子斟满递给她,说:“姐现在是女先生了,还记着干木活的妹子”
容容一笑,说你呀,总是个嘴厉害!”
“呵呵呵。”曹月水高兴地笑着。觉着容容一来这院,把他和月泉的关系都拉近乎了。
“容丫头,你爹在家干啥着哩?”
“噢,我爹现在还能干啥呀,包产了,各干各的了,他在家里蹲着呗……”呵呵,回家跟你爹说,他要想干木活,也不算晚,上这院来跟我搭伙就是了!呵呵呵”
容容脸颊子一红,说:“是哩,我爹要早像伯这样,家里也啥都置下了。”唉,你爹这半辈子……”
容丫头没再吭声,那对儿大眼睛微微低着,啾着手指上那缕缠来绕去的刨花儿。
说让月泉来搭伙,那是笑话。谁不知那汉子的心思根本放不到这上面。月泉咋说也是个干部的身架,一时半晌放不下来。现今他的大儿子仍在县上文化局当处长,咋,老子反倒不如儿,做了木匠?嘿嘿。可曹月水大院又着实眼,了来搭伙手的不来了伙子不,是月牙泉远近驰名的老秀才索天寿的后人,名叫索元亨。吔!亨娃子可说是这村里儿的,不他大上了大,也,刚还乡。人们说,唉,曹月水大院看来是要大发了,不然咋把索家的后人都能上去!
来木家,那的像是在他上啥似的。一日招呼道“那是……索家的后生?”
元亨早听说这位老人,他是阴家“积”字辈的最末一个。但一直没咋见过面。上前叫了声七爷!”
“噢,噢……”老人眼皱在阳光下闪着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