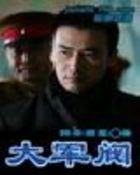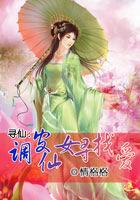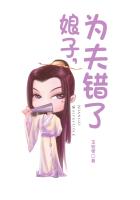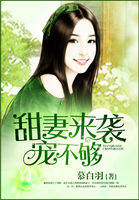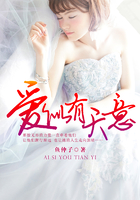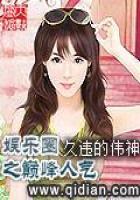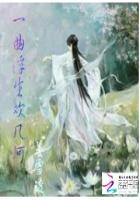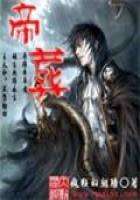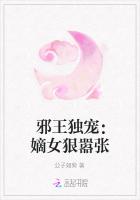1797年天花在英国流行,持续有4年之久,死了很多人,尤其是小孩。威伯福斯认为这是建立强制免疫医疗的时候了,他提出《牛痘法案》,“为小孩健康的缘故,立法强制每个小孩种牛痘”。又有许多反对的声音:“荒谬!竟要立法让每个健康的小孩去接受牛身上的疾病。”“种牛痘?孩子的长相会像牛。”有个医生这样嘲笑道,“为什么狂热的威伯福斯,不听听专业医生的话,提出这么幼稚的法案?政治家该承认自己有许多不懂的地方吧!”不顾反对,威伯福斯仍然坚持《牛痘法案》,因为他的背后有两位优秀的基督徒专家,一位是发现牛痘的金纳(Edward Jenner,1749-1823),另一位是一代奇才贝尔纳(Thomas Bernard)。这个法案的通过,不仅救了许多人的生命,而且使全世界都效法跟进,纷纷立下牛痘法案。
金纳终其一生都在英国的乡村巴克莱(Barkeley)行医,并兼任当地小教会的牧师。他以敏锐的观察力看出挤牛奶的女工不受天花的侵袭而发现牛痘。金纳到伦敦报告这个大发现时,许多伦敦大牌医生都不信这个“乡下来的赤脚大仙”。他争辩了两年,引来更多的讽刺,善良又不善言语的他,带着受伤的心又回到乡下。但是接下来开始有人遵照他的方法做,证实是正确的。
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一直注意这件事。基督徒的信条是“上帝是唯一的正确,传统不一定就正确”,因此只要牛痘是对的,就不管传统医学如何反对。正是这种认知帮助他们突破传统,认清事实,因此跨出为牛痘立法的一步。
39.基督徒的怜恤与社会福利政策
贝尔纳,美国马萨诸塞州人,哈佛大学法律系毕业,他是怀特腓(George Whitefield)在美国东部福音大复兴所结的果子。贝尔纳在上帝面前立下一个特殊的心志一生照顾穷人。”凭着法律的专业,他专门为被欺侮、压迫,请不起律师的穷人辩护。他天生讲话口吃,辩论到热烈时,舌头打结,久久才能说一句完整的话,但是热情充沛,正气凛然,深受敬爱。贝尔纳愈帮助穷人愈发现,他最大的长处还不在法律条文的辩论,而在具有开创力与组织的才能。他与妻子长期不能生育,因此夫妇两人算准赚了若干钱,就可以不用再工作,而全力投入一个从未有人做过的崭新事业——“穷人生活改善中心”。不久,贝尔纳结束律师事务所,到英国加入克拉朋联盟,成为第二代圣徒中负责联络、穿针引线的人物。
贝尔纳认为:“改善穷人生活绝对不在社会福利政策,也不靠同情性的施舍。施舍与福利,反而带来一个危机,使人习惯于被救济,更增加人的惰性和贪婪,更产生反政府的情绪。因此错误的社会福利败坏穷人,使人的劣根性滋长,企盼不劳而获,反成为心志低落的残废者。所以政府愈努力筹钱实施社会福利,所换来的是穷人愈多的反对。穷人感激的不是政府,而是那些唆使他们愈叫嚣才愈能分到大饼吃的人。”这一段话,使得贝尔纳被一般的社会改革家、政治思想家大力抨击,他们两百年来想尽办法要让贝尔纳的言论销声灭迹。
贝尔纳提出:“真正的社会福利,是恢复穷人的自尊与快乐,而最好的方法是制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与改善工作环境的品质。因此应该发展社区大学,让穷人接受更多的教育,学得一技之长。应该用科学方法来制造更多的工作机会!”威伯福斯、麦考利、艾略特等人出了许多钱,给贝尔纳成立这个“穷人生活改善中心”,目的在成立传达各种改善穷人生活方法的资讯站。
这个中心出了许多杰出的科学家:如无机化学之父戴维(Humphry Davy)用电解法发现了15种元素。不过他认为最伟大的发现不是发现元素,而是发掘人才。电磁学大师法拉第(Michael Faraday)用实验证明电与磁的关系。法拉第定律非常有名,但是很少人知道法拉第长期在伦敦的贫民区中,带领一些孩子査考《圣经》。植物学大师班克斯(Joseph Banks)提倡创立植物园,免费教育市民,并设立当时最大的基尤植物园(Kew Gardens)。这些人相信科学研究的成果可以改善社会。贝尔纳发挥他的组织长才,结合这一批科学家和克拉朋联盟组成“英国技术学会”(British Institution),推动《工厂法》(Factory Act)——政府有权突击检查工厂、矿场有无苦待劳工现象——与《济贫法》(Poor Laws)——政府需要提高预算支持穷人教育。这两个法案,后来成为1830年代有“穷人天使”之称的艾希礼(Ashley)为穷人奋斗的基础。英国在过去两百年的历史上,经历许多饥荒、战乱、不景气,而始终没有发生暴力革命,贝尔纳是最关键的人物。
40.星期日法案
1801年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提出一个非常具有争议性的法案,称为《星期日法案》(Sunday Bill)。这个法案不仅引起许多议员的反对,连大多数基督徒也反对。这个法案开始是贝尔格雷爵士(Lord Beigrave)向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提出来的。贝尔格雷爵士本来不是基督徒,他是由于1788年常在议院听威伯福斯的见证而信主的。他是当时非常少有的犯罪学专家,认为“一个人如果每星期工作7天,没有休息的时间,会使人容易犯罪”。他于是成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团体“严守圣日协进会”(Society for the Better Observance of Sunday),探讨守主日为圣日的传统。他愈观察愈心寒,因为星期日许多人仍在工作。他认为这不仅是社会的危机,也是教会的危机。与弟兄们仔细讨论后,威伯福斯决定分为两方面进行,先向基督徒呼吁:“基督徒啊!在星期日时,请看看我们周围的马车夫、送货员、卖菜的……为什么仍有这么多人要为生计卖命,没有休息,也无法安息?星期天真正能休息的,只是中上阶层的少数人……而基督徒渐渐忘记,我们在主日享受到的方便,是建立在贫苦大众的不便上;我们守主日聚会外,仍欣然享受别人的服务。主日聚会会不会渐渐沦为少数中上阶层基督徒的高级娱乐?我呼吁牧师们,除了星期日之外,为那些星期日必须工作的人,设立周间的崇拜聚会。”接着威伯福斯又向皇室贵族、议员建议:“星期日不开会,以免属下不能休息。”
这两个建议遭到全国性的反对,许多牧师认为“威伯福斯对真理认识不清楚,竟然主张不守主日。主日就是星期日,怎么可以改到其他时候”?议员也反对:“星期日不要开会?难道他不晓得我们的会议多么重要,星期日也必须开下去。何况这样才能反应出我们对国家大事的认真与注重。”
在这一大片的反对声中,威伯福斯带着妻子静静地度过41岁的生日。他写下:“喔!主啊!求你用火热的爱,再一次温暖我被我的弟兄姊妹们无情辱骂后的心寒。被人攻击后的沮丧使我迟钝,被人误解后的退缩使我夜里辗转无法成眠。主啊!我厌倦我的事奉。我跌人被误会的泥沼,在挣扎中我无法向你保证心思的洁净。喔!主啊!使我的灵活泼起来,并能感到你的同在。”
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不再提《星期日法案》,转个方向寻求“设立全国性的假日,让所有的人可以一起休息”。严守圣日协进会也宣告解散。
威伯福斯知道许多基督徒误会他了,他的目的不是不守主日,而是顾及中下阶层劳工,教会需要更具弹性的聚会时间。他以深远的眼光看出,19世纪的英国基督徒,在经过卫斯理与怀特腓的大复兴后,渐渐失去了生命的热忱。就如《哥林多前书》所描述的,早期的基督徒是贫穷、知识落后、软弱的一群;信主几年后,蒙神祝福成为富有的中产阶级,反而不去关照穷人,不再传福音了。更糟的是整个教会的思想模式,传福音的对象中产阶级化,与芸芸众生失去了联系。时代的脚步在前进,更多的人涌入城市,尤其是中下层社会的人,他们不晓得他们的教会在哪里。而教会中产阶级的框框,也视他们为局外人。“基督徒没落的热心”是使国家的基督徒比例直线下降的原因。历史证明,到了1850年,英国已经很少有劳工到教会去;到了1900年,失去群众的教会,已成为英国无关紧要的边缘团体了。很可惜!这样的历史仍然不断地重演,于是教会的影响力,就一落千丈了。
41.禁止虐待动物法案
虐待动物是人类的病态心理。在动物不合理的受苦中获得快乐,这种状况一直在人类各种把戏、玩耍中存在。当时的欧洲流行一种狗追野熊的游戏,就是将野熊抓来,用绳子绑缚在钉紧的木头上,再放凶猛的饲养狼犬去咬它。熊狗相斗的吼叫,刺激又血腥。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与法学家厄斯金,首先针对这个恶习提出《禁止虐待动物法案》,促使禁止熊狗相斗的游戏。“为什么要禁止呢?这种活动有助国民勇敢、尚武的精神。”反对者提出。“在丛林里、大草原或是南极探险,才是真正的勇敢,这种血腥的玩耍等于是蔑视生命,对教育只有负面的影响。”弟兄们辩道。“如果你们知道怎么玩,就知道这有多刺激。”反对者答道。“是吗?如果你们能体会动物的感觉就一点也不刺激。”威伯福斯辩道。这个法案后来通过,并且成为野生动物保护的先河。
社会上有许多不合理的现象与制度。1799年克拉朋联盟的麦考利由狮子山公司回来,和长期等待他的女友结婚,并且以他的文学长才,创立一份《基督教观察家报》(Christian Observer)月刊,其宗旨是“以清楚、严谨与信仰的实践,在社会问题上落实布道神学,而非讨论神学上的细小歧异”。威伯福斯有辩论长才,在动笔爬格子方面却缓如蜗牛,麦考利催了他一年,他才挤出一篇短文,并附了个短笺:“我相信你一定为我感到难过,但不要失望。我全心相信这份月刊会办得更好。”借着这份刊物,麦考利以他对时代的敏锐,针对现今问题提出反思,这一份刊物几乎成为克拉朋联盟的“机关报”。
另一个优秀的写作人才是布鲁厄姆(Henry Brougham,1778-1868),英国爱丁堡大学法律系毕业。他曾经在法国居住,只因为不是法兰西种的白人就遭到冷酷的歧视,回到英国后决心为被歧视的人争取法律的公平。他担任伦敦最高法院无人委托诉讼案件的律师(公设辩护人),他的法律专业,把他训练成一个收集罪证的专家。在1807年,他投人第二代克拉朋联盟,和第一代的法律大师史蒂芬并肩作战,取得了许多胜利。他同时兼具写作长才,担任当时最佳期刊《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的主编,反对奴隶制度,并认为奴隶制度是国家公共政策上的大谎言。
布鲁厄姆年轻时是个着名的花花公子,英俊潇洒、口若悬河,博得无数女孩的欢心。他带着当时最大财阀的女儿,私奔法国结婚,在保守的18世纪是件社会大新闻。之后,在法国吃足苦头的布鲁厄姆,身处困境,偶听福音,反而成为热心的基督徒。回到英国后,许多人都因他的桃色新闻太多,而与他保持距离;出人意外地,这时敢出面接受他的竟是威伯福斯。当威伯福斯带布鲁厄姆加人克拉朋联盟时,许多弟兄提出反对:“连一般政治团体都不要的人,我们竟然还请他来。”威伯福斯知人善用,他轻描淡写地讲了一句话:“依我看,当我年老过去时,能够代替我带领弟兄们往前的人可能就是他。”知遇之恩,使布鲁厄姆全力以赴,大展才华,不仅担任《爱丁堡评论》的主编,而且着有《欧洲权势下的殖民政策》(Colonial Policy of European Powers)一书,攻击海外殖民政策。1820年推翻奴隶制度时,他是最主要的攻击炮火。他创立着名的英国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成立“有用知识推广协会”(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将好书以最低的价格卖给劳工界;以法律专长改革英国法院制度,并建立刑事法庭(Criminal Court)。1830年到1834年,他担任上议院的议长,整个奴隶制度就是在这时被废除。时间证明,威伯福斯没有看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