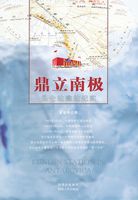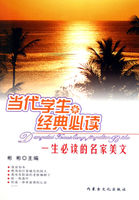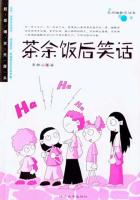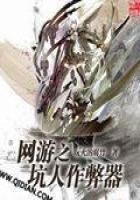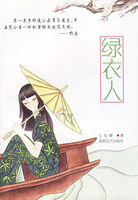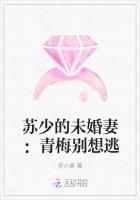逛书店偶得
看过皮皮的《出卖阳光》,因为想了解一种时尚的写作方式,或者是一种时尚的文字堆积,所以,我了解到了那种文字的魅力。曾经感觉很好。今曰又见皮皮,好多书码放在一起,先是《比如女人》,再是《所谓先生》,然后是《爱情句号》,我不知道它们之间会有什么样的联系,但是必有联系的反应却挥之不去。
文字,经人堆积,形成文章,于是,称文章为文。文,一样吗?文,不一样。陈平原着书《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就是在说明这个问题吧,因为文人不一样,所以,文章不一样。说一般人推崇的晚明小品乃典型的“文人之文”,独抒性灵,轻巧而亮丽;而一直不大被看好的清代文章,则大都属于“学者之文”,注重典制,朴实但大气。匆匆扫过关于陈平原这部书的简介,我并不知道作者对于两种文章所持的态度,但是,我想,无论怎样,就算真的有两种文章的差异存在,两种文章都应该是共存的吧。
共存的东西很多,但是我们不会都知道。可能是因为昨天刚买了蓝山咖啡,因而对于“蓝山”两个字格外敏感吧,在书架上,我发现了《蓝山》这本书,是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作者的名字没有记住,但是记住了作者的国籍是以色列。好像我是第一次注意到会有一本书它的作者是以色列人。是怀疑什么呢?不是怀疑什么,只是自己真是很寡闻,在寡闻的背后可能还会有某种偏执,忘记了共存的存在。
其实,忘记也是一种存在。再见《往事并不如烟》似乎确有如烟般的沧桑。还记得那本书风靡之时,秉烛夜读,满怀痴迷于文宇之中最后的贵族。是的,那本书在大陆以外就是以《最后的贵族》冠名的。而今天再见,似乎,成为最后的不仅是贵族,而且还有章诒和的怀想与不甘。
《约翰·克利斯朵夫》对我来说大概只能成为怀想和不甘了吧。人家说那是一本催人奋进的书,但是那也是一本要在青春年少时读的书。可是当我知道这本书的时候,已经不年少了。曾经,每次去书店看到它,总有阅读的冲动,但每次都被那厚厚的篇幅吓退了,所以,最后只买了回来,在书架上占为己有。在浮尘天气里,才会有轻拭拂过书脊。
因为浮尘才会触及的书籍,还有一些是曾经爱不释手的。比如《文化苦旅》。不管有多少批评的声音曾经或者仍在指向它,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它曾经那么深刻地引领过我,在艳阳的午后,在微雨的清晨,在孤单的夜晚,在喧闹的黄昏。可是,在它之后,余秋雨的文章我再也不肯触及。我不知道他会在《借我一生》中谈及什么,不知道他会在走过了希腊、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伊朗、印度、尼泊尔之后如何《千年一叹》。也不想知道。
不想知道的还有余华的《兄弟》下部。余华,被收入当代文学史(台湾)的作家,我不敢继续读他了,因为我怕,我怕一个因我的无度的期望而导致的一个残缺作品的出现。书架上,一色的上海文艺出版社,一色作者余华,但是颜色却是不同的。《世事如烟》《黄昏里的男孩》《我胆小如鼠》《战栗》《鲜血梅花》《现实一种》是浅土色的,很不起眼,有点像是陈旧的白,或者陈旧的黄。《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音乐影响我的写作》《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途》是嫩黄色的,鲜亮、快意。《在细雨中呼喊》《许三观卖血记》《活着》是红色的,浓烈的红色,招摇。到了《兄弟》,是花的了,摇摆不定的、没有了基调的花的了。
倒是,林伟贤,这个名字很吸引我。我曾经听过他的讲座,在山东教育台,每晚不落地听了他的关于资源整合的全部课程,喜欢。他的书,名为《我爱钱,更爱你》,喜欢这个书名,形而下的、形而上的都有了,且错落有致,相映生辉。作为一个着名的国际课程讲师,我更喜欢他谈及的来自亲人、朋友的挚爱,以及他在谈及这些话题时流露出来的美满幸福。
2006年4月。
让爱深植我心
让我的爱像阳光一样包围着你,又给你光辉灿烂的自由。
一一泰戈尔
这句话是朋友告诉我的,在一个不晴朗的午后。后来,我在夜晚回家的出租车上准确复述,那时,我知道这句话巳经深植于我心了。
于是,开始思量那是怎样的爱,竟有如此广大的胸怀,竟有如此深厚的温暖!
思量之后就是幻想了,幻想自己可以拥有这样的爱,从此,了无遗憾。说到这儿,自己也忽然明白了,这幻想产生的基础一定就是这爱离我很远,且遥不可及。
那么,我拥有的爱呢?我还拥有爱吗?
这个问题就很实际了。
静下心来,心平气和地感知,我想我发现了答案。
那么,大声地告诉自己吧!一一我已经拥有了这样的爱。
我已经拥有了这样的爱,还不够!我还得付出同样的爱。
那样,才真正的是“让我的爱像阳光一样包围着你,又给你光辉灿烂的自由”深植我心了。
2006年10月。
认字
我不认得的字很多,稍有生僻的字对我来说就是障碍。以前的时候,一直怀疑是小学没有读好,没有过识字关,其实,细细想来真不应该把责任归于那个学习阶段。小学能够学到的字毕竟是有限的,尤其是那些含义、态度暧昧、晦涩的字,和那些极少提及的书面语言。所以,我想真正让我不识字的原因大概就是自己在以后的学习中没能继续认宇吧。
为什么不继续认字呢?既然认识到了不足,就要努力改正。所以,下决心,以后,当我遇到了不认得的字时,一定要极其仔细地查字典,极其负责地记忆。
“刳”,这个字我就不认识。看字形,知道与利器有关,读文章一一“刳去”,会意它就是要说“抛开”“去掉”的意思。但是,那个字读什么音呢?读“kua”吗?音调又如何?不知。
查字典。字典是个好东西。
刳kū,〔书〕剖开;挖空:刳木为舟。
释然。正拟庆幸学了一个新成语“刳木为舟”时,忽然想起“极其仔细”的决心,于是查阅成语辞典。幡然醒悟,原来“刳木为舟”不是成语。差点又出错了。
合上案头的工具书,开始翻腾自己那点少得可怜的记忆,的确是想不起来在什么时候曾经学过那个“刳”字。刚想为自己的不认识辩解,转念一想,为什么别人竟能使用我都不认识的字呢?
唉,认了一个字,却垂头丧气。
咦?可能就因为我认字之后的这种无成就感吧,才让我不认识那么多的字?可能?可能!
2006年9月。
我不会写繁体字
我是不会写繁体字的,但是却可以认识它,常用字的繁体都是可以认识的,当然能达到这个程度也还是稍下了一些工夫的。
上学的时候学习过一门课程叫《古文选读》,讲课的先生名叫杜宝元,先生是个高个子,戴着高度近视镜,镜片厚极了,在给我们讲古文名篇的同时,要求我们学习繁体字。
起初我们以为只要认识就好,没想到后来还安排了考试,考试就两道题目,一、看简化字写出繁体字,二、看繁体字写出简化字。两道题目给出的字数相同,大概都是二三十个吧,记不清了。看繁体字写简化字似乎并不很困难,连猜带蒙,一会儿也就写完了,可是写繁体字,就有了很多的麻烦,一个字总得要写出来吧,那可是一笔一画的事情,可不是大概,于是先抓耳挠腮、左添一撇右描一捺地写出来,然后再唉声叹气、俯首摇头连连自语“不像啊”。记得很清楚的一个字是“庆”,写的时候就努力地想这个字繁体的样子,样子就在眼前,可就是不能写在纸上,好像有“广”是没问题的,好像还有很多点,好像很像“丰收”的样子的,遂连描带画,然终未成宇。
同学们的情况比我好不到哪里去,那次考试一定是让中文大大丰富了,哈哈。印象中没有那次考试的成绩,大概是压根就没给成绩,也可能是成绩太糟糕了,被我的记忆选择性地遗忘了吧,反正没印象了。
不知道杜宝元先生是否一切安好,距那门课程结束已经二十年了。
2008年3月。
我的文字病了
看过《橘子红了》之后,我真正开始明白什么叫病态的唯美。整个故事似乎都是那么美,美得叫人心痛;所有的画面一定都是那么美,美得叫人心动。
柔焦的透视让老宅笼上了缥渺的忧郁,过大的光圈让心灵显得更加苍白,狭小的景深让琐事繁杂与之相隔,这些都是《橘子红了》中的表现手法,还有声音,与其说是磁性的,不如说是哑声的,更加显出挣扎与反抗。
橘子是美的,红了是美的,《橘子红了》是唯美的,但是从这唯美中我更多地看到的是矫揉造作的病态,我痛恨病态,我向往健康。
然而,我的文字病了,我的文字学会了叫喊,学会了呻吟,学会了作秀,学会了暧昧,学会了把一堆辞藻罗列在一起,表达一句只可以识字却不能会意的话,根本没有情理可言。
是的,我的文字病了,病中仍招摇地诉说,想得到情感的青睐,甚至幻想与情感相伴于青灯竹卷之中。
的确,我的文字病了,患疾的文字承载不了悠长的心情,撕裂后,让心变得更加寂寥。
2003年夏,那时,感冒了。
笔下的文字却不若希望的明媚
几近半年的时间没有写过什么了,越是不写也就越不想写了,倒不是懒惰,而是习惯,我一直想把写作当做一种习惯,但是不曾想不写也会成为习惯的,此习惯,彼习惯,此消彼长,就看谁制服得了谁了。
习惯,这个词对我而言,印象深刻,但这一行为,却总是被我忽视,我知道,这不好。
一九八八年的高考作文题目就是《习惯》,那篇作文被我写得惨不忍睹,尽管那个很烂的作文分数被总成绩掩盖住了,但是那篇作文却沉重地打击了我的笔,一直到大学二年级的后期,我才重新提笔,写自己,写属于自己的那个年龄,写属于那个年龄的学习和生活,曾经写了几本日记,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写本身真的很好,很温馨。
当写成为那时候生活的一部分之后,我才慢慢地从那篇作文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并开始了一种有意为之的写作习惯。
并不是所有的习惯都是有意为之的。比如秋的感伤。秋的感伤于我也是一种习惯,从很早以前。曾经的那份情感一定源于一种深深的诱惑,在我的笔下蔓延,那浓烈的秋的气息,无论颜色还是声响,都是内心深处的找不到出路的自我诱惑吧,这诱惑积郁久了,沉积成感伤,每到深秋,就开始招摇。
然而这个秋天,感伤于我更添了许多,但与诱惑无关。我不希望这份新添的感伤成为习惯,不希望。
我希望我的心永远阳光明媚,我希望我的心永远能体会到那份阳光明媚,我希望我的心永远温暖如阳光明媚,我希望我的心永远阳光明媚如阳光明媚。
但愿希望的这份永远也能成为永远。
但愿内心充盈的希望能成为习惯。
就这样在躺满希望的心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这种自我探索也早已成为习惯,也怕只有这样,我才能感知到生命存在的本身。
笔下的文字却不若希望的明媚。晦涩。
2008年10月。
读蒙田
读书是一种略带忧郁的享受,这是好久以前我在网上看过的一篇文章的标题,一看到,就被吸引住了,于是细细品读,甚至还觉不忍离去,所以打印下来保留至今。
文章中细细描述作者在一人一室一盏灯下的读书感受,说也许正因为有几分忧郁,几分寂寞,阅读的姿势才会如此迷人。
我想是的,我能被这样的感觉所吸引,大概也正是源自对那份忧郁和寂寞的向往吧。
最近读《蒙田随笔》没找到全集,只买了本精选,跟着蒙田走在深深的自我怀疑的路上,那迷茫和疑惑告诉我只能一直走下去,别无他法。别无他法,还因为停留就意味着承受恐惧和最终沦丧。
蒙田谈及高尚的友谊时说因其寡见鲜有而令人惆怅,谈及美丽的爱情时说随着岁月增长而日渐凋零,为此,他认为这两种存在偶然性并取决于他人的交往不能满足人一生的需要,而与书本交往则有它稳定和方便的特有长处,“与书本交往要可靠得多并更好地取决于我们自己”,除此之外,它可以伴随我们一生,处处给我们以帮助,它是我们处于老境与孤独时的安慰,解决我们的闲愁与烦恼,它能磨钝疼痛的芒刺,让我们摆脱生活中令人生厌的伙伴,而且,书总是以始终如一的可亲面容接待我们。
享受书,犹如守财奴享受他的财宝,随时可以,正是这种拥有权让我们的心感到惬意和满足。年轻时读书可能是为了炫耀,后来多少是为了明理,再后来可能就是为了自娱了吧,但从来不为得利。
跟着蒙田,穿越了孤寂与怀疑之后,我才看到了一些仅属于人类思想的光芒,他以一个智者的目光,以深深的刻骨的怀疑试图让我们看清我们自己。
2007年2月。
读卡夫卡
因为两篇评论,于是找卡夫卡来读,读之前,还请教朋友,卡夫卡是后现代吗?朋友说,不是,是现代,但是卡夫卡自己说,自己什么代也不算。
不管算不算,先读吧。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读卡夫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文字有些晦涩,节奏有些缓慢,甚至连段落也显得与别的格格不人,我不知道,是我没有进人状态,还是卡夫卡本就是这个模样。
我想还是我的浮躁在影响我的阅读,那么,先让自己沉静下来吧。让自己沉静可以借助别人的力量,我开始翻阅别人的阅读成果。有人说,卡夫卡的散文才是最棒的,不看卡夫卡的散文,就不懂卡夫卡。
好吧,那,我也去找他的散文。
差点犯个错误,《北回归线》是亨利·米勒写的,我差一点就给了卡夫卡,看来,对于他们,卡夫卡,还有米勒,我都是很生疏的。
忽然散步
我决定晚上留在家里,穿上便服,晚餐后,坐在明亮的桌子旁边,开始工作或作某种消遣。之后,带着愉快的心情去上床睡觉。倘若天气不好,那自然是待在家里,然而,也有这种情况,虽然在桌子旁边静静地待了很长时间,要到外面去走。这必然会使大家感到惊奇。又如当时楼道是黑暗的,门已关好,但由于忽然心情不好,也会不顾一切地要起床,换上衣服,可能很快就出现在街上,先给家里人讲,要到外面走走,打完招呼很快地就行动了。关好门,于是很快觉得或多或少地扔掉了一些烦恼,一旦到了街上,四肢百节感到意外的舒展和自由,而这种舒展和自由正是人的决定给自己的身子带来的,身子的舒展和自由也是给人的决定以特别动人的回报。从这个决定中你感到自己集中了作出决定的能力,并赋予它不同凡响的意义,也认识到自己具有的力量比要求确实要多,这种力量可以轻易地带来和适应一种迅速的变化,既然要走完这长长的胡同,今晚整个儿就不在家里了。家里也变得空阔些了,而我这个模糊的轮廓,拍着大腿,便上升为一个真实的形象。要是你在深夜去寻找一个朋友,去探视和问候他,还会加强一切。
这是卡夫卡的一篇短篇小说,我怎么就看不出来小说的味道呢?我还是再回到文字中去吧,趁着阳光,可以不至于迷失在无知之中。
2005年11月25日,终止了读卡夫卡的计划。
读梁实秋
翻开梁实秋的《雅舍小品》,一张书里附带的书签露出来,淡黄色的底上深深浅浅的褐色的树和房屋,勾勒出一片田园风光,空白处题了几行小字:“有人说,人在开始喜欢回忆的时候便是开始老的时候。我现在开始喜欢回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