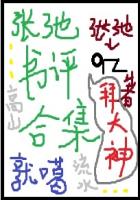“它不是狼。”不知过了多久,宛炎突然指着趴在他脚边的大型动物冷不丁的来了这么一句。
“那是什么?”顾潇潇疑惑。
长时间的沉默竟然在不经意间很好的被宛炎化解了……
“是狗的一种,哈士奇,你知道吗?”
顾潇潇隐约记起在网上好像听人说过,挺蠢的一种狗,怎么和今天见到的不太一样?
“你怎么想起来养狗了?”顾潇潇顺嘴问道。
宛炎怔了怔,眼神顿时暗了下去。一下一下的捏着哈士奇的三角形耳朵,动作轻轻柔柔的,那条狗还做出一副享受的样子。
顾潇潇望着这条颇通人性的哈士奇,忍不住弯了眼角:现在才有点狗狗的样子嘛,刚刚那么凶干吗,真是的……
“它叫什么名字?”顾潇潇再次顺嘴一问。
宛炎又再次怔了怔,望了眼顾潇潇,然后低下头默默说道:“小小,它叫小小。”
顾潇潇听了直想发笑:这么大条恶犬,你叫它小小,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哈哈哈哈……
她笑的正起劲,却没注意到宛炎的余光全落在了她身上,眼中闪着某种不明的情绪。
其实它哪里是叫小小,只不过诓你的谎话罢了。
顾潇潇笑的豪迈无比,一时间竟忘了来这一趟的正事。过了会儿,突然停了笑声,不好意思的挠挠头:“颜老师……呃……还是应该叫宛老师?废话不多说了,我们来谈谈正事吧。”
顾潇潇陡然的严肃让宛炎很不习惯,特别是那两个听起来极其疏远的称呼,什么颜老师、宛老师的,你干脆叫我苍老师好啦!
面上还是死鸭子嘴硬,装出的一副淡然的样子:“随便你。”
“好,颜老师。我的来意刚刚已经表明了,不知道您的意愿如何?”顾潇潇端出一副无比官方的样子,好像两人不是在宛炎家,而是在******的会客厅。
宛炎看到她这副假正经的样子就胃痛,没好气的说:“你的来意?对不起,我给忘了。”
顾潇潇强压下怒火,好脾气的笑了笑,耐着性子又给他解释了一遍。
宛炎思考了下,然后悠然的岔开了话题:“口渴了。”
顾潇潇怒火中烧,你特么还当老子是你家保姆吗?那都是八百年前的事了!要不是他身边有条看起来很凶的哈士奇,顾潇潇非冲上去拍死他!
“家里有水吗?我给您倒。”顾潇潇的耐心显然已经到了极点,强忍着的嘴角不自然的抽搐。
“没有。”宛炎双手一摊,无辜的答了句。
“那你特么平时喝什么!我给你弄还不行吗!”顾潇潇终于忍不住吼了出来,胸口急剧起伏。
宛炎心里颇有种得胜的快感,三年了,自己还是喜欢看她生气时暴跳如雷的样子,这个怪癖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养成的,自己……是不是有点变态啊?宛炎在心里小小的反思了一下,然后继续理所应当的使唤顾潇潇:“平时都喝矿泉水,今天恰好没了。”
顾潇潇急中生智,开始拆她带来的脑白金。
宛炎惊恐的叫到:“喂喂,你不会要给我喝着个吧?”
顾潇潇一边粗鲁的拆包装,一边阴险的笑了下:“这可由不得你了。”
“我不要我不要啊!”宛炎连忙摆手,吓得俊脸刷一下白了。
顾潇潇动作十分麻利,已经拆下了一瓶,三下五除二拧开了瓶盖。刚刚的滔天怒火此时仿佛全数化作了如牛的蛮力,顾潇潇死死的把宛炎按在沙发上,扒开他的嘴就把整瓶脑白金倒了进去。
宛炎被她的一连串动作吓得不轻,以为这姑娘是被自己逼疯了,竟然忘记了反抗。直到那微苦的液体源源不断的进入到口中,他才惊觉发生了什么。两只手在空中乱挥,嘴里含含糊糊的不知说了些什么。
一旁的哈士奇见主人遭受如此“侮辱”,咬着顾潇潇的裤脚狂吠了起来,不过显然,顾潇潇已经失去了理智,笑的跟个逼良为娼的老鸨似的,放浪形骸。
一瓶很快灌完,顾潇潇把空瓶子扔在茶几上,随手抽了张纸巾擦了擦手,满意的坐在沙发上,望着宛炎面露狠色。
宛炎刚刚被灌得太急,现在不住的咳嗽。身上的浴袍也因为方才的撕扯而大开大敞,露出了光滑结实的胸口,再配上这张秀色可餐的小脸儿……顾潇潇心中的怒火还未息,欲火又蹭的一下燃了起来,心中突然涌出一个疯狂地想法:要是就地把他给办了,一切的烦心事儿不就迎刃而解了吗?自己不用再日复一日的苦恋,爸妈也不用担心自己的终生大事,一切都好了……
只可惜,她没有那种釜底抽薪的勇气……
她站起身来,整理了下衣服,正色说道:“颜先生,看来您今日心情不佳,不适合谈公事,我改日登门拜访,到时候再详谈,再见。”说完拍拍屁股走人。
宛炎抽了张纸巾默默的擦着嘴边残留的棕色液体,心中不知作何感想。
“小小”十分善解人意的跳上沙发,舔了舔宛炎的手,整张脸耷拉下来,看起来像是在同情的主人刚刚的遭遇。
宛炎笑了笑,抬手摸了摸它背上的毛毛,淡淡道:“潇潇,你还是这么傻。”
其实,这只瞳色不一的哈士奇的名字不叫小小,而是叫——潇潇。
顾潇潇下楼的时候刚好碰到徐进,徐进像是见了鬼似的叫到:“潇潇?你怎么在这里!你把宛炎怎么了?”
看那副样子,说不定是以为自己把宛炎先奸后杀了。顾潇潇见不得他这副忠心护主的样子,即使他是她最好的朋友的男朋友,也不行!
想来,徐进跟宛炎是多年好友了,他一定知道宛炎的笔名就是颜挽,居然还帮着宛炎一直瞒着自己,真是太可恨了!顾潇潇抑制住自己想要骂人的冲动,大力的推了徐进一把,然后蹬着恨天高急急下楼。
徐进耸耸肩,一头雾水的来到了宛炎家。
“嘿,怎么回事儿啊?我刚刚看见潇潇气冲冲的跑下楼了,她来找过你了?”徐进一进门就看到宛炎衣衫不整的样子,眼睛都快毛火光了。那眼神,恨不得自己是一台单反,现在就把宛炎这副样子拍下来,公之于众。
宛炎不说话,沉默着走到卧室。
徐进像条尾巴一样一直跟在他身后,而“潇潇”则乖觉的跟在徐进身后。
“我说,你倒是说句话啊,你俩怎么了?是你怎么她了,还是她怎么你了?这都三年了,怎么还跟仇人似的呢?”徐进又开起了话唠模式。
宛炎走到卧室,关上门,徐进死皮赖脸的抵住门:“让我进去啊,都是大老爷们儿,怕什么!”
宛炎懒得理他,冷着脸自顾自的拉上了窗帘。解开了浴袍的腰带,露出精瘦的腰身和结实的胸膛以及那满身的伤痕。
宛炎触到自己满是伤痕的手臂时,心里居然暗松了一口气:还好刚才只露出了胸口,不然……又不知道要生出多少事端。
徐进瞄到宛炎的手臂时,眉头倏地一下皱了起来。他没想到,他身上的伤口居然又多了些。那一条条触目惊心的伤疤蜿蜒在他雪白的胳膊上,和那些已经结痂的陈年旧伤交织在一起,深深浅浅,有些已经淡到看不出颜色,有些还泛着血丝。
徐进的脸立刻阴沉了下来,不语不发的坐在一边,冷眼看着宛炎脱下浴袍,换上衬衫。
“你不准备解释些什么?”徐进的目光定在他还未扣好扣子的右臂上。
“就像你看到的,不必解释。”宛炎头也不抬的继续扣扣子。
徐进啪一声摔了床头柜上的玻璃杯,大吼道:“你他妈就这么不把命当命啊!老天爷给了你横溢的才华,给了你至高的天赋,就是让你这样糟蹋的吗!”徐进气的头上青筋直跳,握着扶手的指关节也微微泛白。
宛炎转身面向徐进,身后是厚重古朴的纯黑窗帘。宛炎一直睡眠不太好,晚上睡觉的时候见不得一丝光亮,这毫不透光的窗帘是徐进跑遍了大大小小的建材市场好不容易才买来的。
屋内一片昏暗,宛炎穿着件修身的白衬衫站在房间里最黑暗的地方,黑暗笼罩了他全身,只有那双眼睛,泛着冷冷的幽光,仿佛再多的黑暗都没法儿让它隐没。
良久,宛炎闭上了眼,拱着眉尖,道出一句:“你说上天厚待我,可他给了我这么多,却唯独忘了一样,忘了一样最重要的。”
徐进看不清他的表情,只觉他的语气十分悲伤,脆弱的像个孩子,让人不忍苛责。
“是什么?”徐进问。
宛炎扯了扯嘴角,声音飘忽若蚊呐:“他,忘了给我快乐。”
霎时,徐进只觉得自己的心像是被一只大手紧紧的攥住,慢慢碾碎,痛的说不出话来。
他无言以对。
当初认识宛炎的时候,他不过十七岁,是班里年纪最小的一个。那时的他便很少展露笑颜,其他同学都私下猜测他是不是有面瘫症,不敢靠近他。唯有徐进这个不怕死的,愣是用自己的热脸一次次的去贴他的冷屁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交到他这个朋友。
可是,即便自己使出浑身解数想要逗他笑,往往也是收效甚微。直到后来,顾潇潇出现了。徐进觉得宛炎就像是一颗在泥土中沉寂已久的向日葵种子,陡然遇到了他生命中早已注定的灿烂——顾潇潇。他在慢慢的变化,一点一点,这变化可能连宛炎自己都察觉不到。所以他极力的撮合他俩。
就在他以为宛炎要彻底被顾潇潇改变的时候,事态却急转直下。向日葵种子却拒绝了阳光的示爱,并说要离开那片有太阳的土地。徐进想破了脑袋也想不出宛炎拒绝潇潇的理由,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渐行渐远。
妈蛋,那叫一个焦心!宛炎这株脑残的向日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