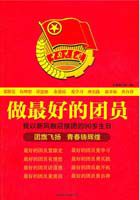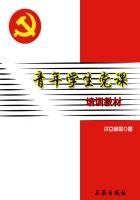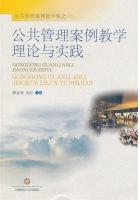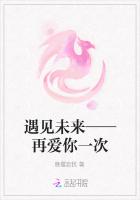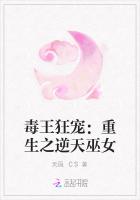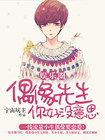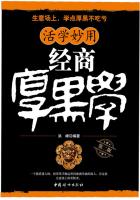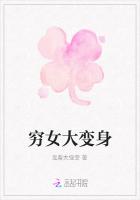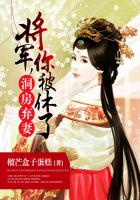西哲苏格拉底有云,不加检省的人生是无价值的人生。这句话存在了两千多年,但至今也仍是只为少数人所乐道,因为有检省的人生是很不简约的人生,就像产品改型需要很多资源投入一样,不能突破“资源瓶颈”,过多的检省使会生活变得很不好受。所以大多数人宁愿生活在惯性之中,让“自我”变成免检产品。
不过,检省人生一向受人推崇,毕竟是有一定的道理。它蕴含着不使我们完全变成一具行尸走肉的要求。所以我对那句格言也曾检省再三,觉得还是改为“找不着感觉的人生是没价值的人生”较为妥当,一来可免于纯动物性的快乐,被人骂为“衣冠禽兽”,二来颇具普罗风格——苏格拉底那个层次的检省,岂是人人可以做的,而感觉大伙都不缺,就看你如何捕捉并把它略作提升,使之成为比肾上腺素更丰富一点儿的东西,即可当得起“人生”的尊称了。
只有这种能够捕捉感觉的人生,才能让你真正喜欢上什么。比如我们交不共事的朋友,一般并不借助于事先的检省或算计好的标准,第一感觉是这人很有味道儿,才有交下去的可能,有道是“臭味相投”,可知成语乃智慧之结晶并非虚言。张洪便是这样一个让我觉得很有味道的人。我们相识得很早很早,但真正有了成年人的情谊,却是几年前她结束漂泊生涯,重新定居于北京之后。彼此有过数通信札往还,还为欧洲的什么事抬过杠,未久被她“闲话六根”的妙文搅得像是喝了一瓶二锅头,气氛一下子热烙起来,此后再没消退。
如果深究起来,喜欢上张洪的文字,并非因为她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固然,出大学校门未久,她便进了京城,继之以云游四海,去柏林,赴巴黎,走韩国,跑新加坡,不是上车睡觉下车撒尿的那种,而是一住多则一两年,少则数月半载。然而,整日穿梭于天际的商务舱里,这样的人物又何止千万。
我也不是有感于她涉足的面积太广,古典音乐,电影小说、诗词歌赋、基督教和佛门等等,样样她都摸得说得,让我的头脑忙活不过来。我之喜欢上她,是因为尽管历经了这么多容易给人上套的东西,她却依然那么率性,那么没羁绊。读她的东西,我总有一种情不自禁的感觉,她一定很明白被好多人忘记了的道理:如果“高层次”的东西并不优秀,那一定是虚荣和无聊不忍舍弃的东西,这样的“高层次”便只是我们为不值得为之辩解之物强找出的辩词。
所以我们看张洪说人论事,她并不太在意什么“层次”问题,上至时间的奥秘,下到儿时大明湖畔的咸菜店,有想法就放开了说,并不拿学理章法当回事。随便翻翻那些小文,就知道她肚里有货,其意境却不是刻意为文所能企及的。到了黄土齐腰这把年纪,心灵的步态仍能如此轻盈,对很多人来说是难上加难的事情,在她却如同晨露随朝霞散去一般自然。若想知道天性,即她说的“六根”之和,为何会比理性更加多智多谋,看看张洪的《说话》就明白了。
套用前面被我篡改的格言,她是个很会捕捉感觉的人。道理能讲且讲,得挖苦者且挖苦,让你一时搞不清她是想传真经,还是说风凉话。当她斩钉截铁申述柏林墙的微言大义时,你无法想象她接下来会写出“边吃边说”那样的篇什。也由于本然感觉的敏锐使然,在行色匆匆的笔端下,她时时抛出几句隽永的心得,散落于字里行间,使语言变得张力十足,令人惊叹唏嘘。读这样的文字,你经常会被她忽悠得心荡神移。那种挑起话头百端,说到精妙处便戛然而止的习惯,由不得你不对她生出几份恨意:这人怎么这样,用菜谱吊起人家胃口,就是不给上菜呢?她则答曰:这不就是小品文的禀性么,说好说坏,由您老去了。
换个角度说,她也许更像是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中那位麦布女王(Queen Mab)的化身,无执守的好奇心充塞于头脑,总是瞪着一双惊奇的眼睛,发出温敦调皮的笑声,同时又念念不忘环顾四周。这个天使振翅盘旋于我们的头顶,通知大家要dum vivimus, vivamus(活着,就得活得像个样),至于怎样才算“像样”,她并无专一的使命。她不是为撒播semper ubique et ab omnibus——万世不易、很成体统很权威的东西——而来的。
也许,她的文字与前些年的“洋插”经历一起,只是为了印证生命的流动性而存在的。人生毕竟不是只有一个正确答案的数学题,而是由层层叠叠、不断扑面而来的事件和疑惑所组成。甚至沉淀在最深处的哲理,也只是一种流动性被暂时凝固的感觉。生活的动人之处,多是在流动中发生。古人云,上善若水;桑塔亚那说,流动才是生命的本质,我们的血液和精液,泪水和汗水,都是属液态的。因此世间再没有比流动不居、转瞬即逝的事物——譬如音乐和爱——更加动人的了。
这种飘忽不定惹人伤感,但僵死与停滞更加令人悲哀。再好的港湾,没有航行便失去了意义。我们的理性算计能力往往觉得只有老子厉害,能把一切搞定,但激发生命色彩的,肯定不是被搞定的东西。没有源自于最深层的动物性嬉戏,不但艺术和道德无法存活,理性算计的大厦也会变得空空荡荡。
但是我也相信,激发张洪的嬉戏和想象力的源头,不是格瓦拉或萨特之流。她说,上大学那会儿,曾经很是迷过萨特一阵子。时至今日,只是残留下一丝淡淡的逆反与讥诮,还有《时间之矢》(我最喜欢的一篇)中的一串串感叹,都是恰如其分,都在我尚可接受的限度。看看“侃朔爷”和“孤岛与湖”中的几篇就知道,她骨子里也许是个文化自然主义者(恕我用这个自相矛盾的字眼吧)。
这样的人注定了要在羞怯与自信之间徘徊,无论对己对人,一碰上不是自然流淌出来的东西,就会皱眉头,就想打退堂鼓。从她的内心深处,我们总能感到一种对自然之物的敬重,以及随之而来的一份莫名其妙的谦卑。这使她宁肯只冲着我们憨笑,也不愿把文化变成作秀;可是一瞅见耿直较真的老梁或汉斯(《老梁二三事》《阳光汉斯》篇),她必报以澄明如同皓月的眼神。如果你要问她最希望世道如何待她,她十有八九会说,那就让我随处走走,随手翻翻吧。一旦你随她去,她回来后一定会给你说说话,说些我们不易听到又很爱听的事情。
总结一下。张洪不是个想振兴文化的人,她只想做个蹑蹑于文化身边的伴娘。有人往往不自知,一心要匡正文化,结果使人在生活中不时会犯的一些错误,本可作为逗乐的谈资,却变成了十分可憎的专横。如果文化像在张洪那儿一样,也在好多人的心头悄悄活着,那它必不同于供奉于庙堂之上,让人献身或让人恨的各路神明,而更像是飘浮于拉卜楞寺(她是去过那地方的)的香气,似有似无地存在着,传递信仰的气息,却不会挡人抽身离去。它很知凡尘中人的无奈,不想惹大家烦。
学问加理想,调理不当会让人很无聊;文化加感觉,搭配得法能使人很有趣。张洪肯定属于后者。至于她所乐道的“悟”境,我理解为种种内因外因错综复杂的神秘化合物,我们共同心向往之,却至今不知这个宝贝存放于何处。
不过,话还得说回来,“悟”是一种大境界不假,但往往身陷困局时才迫切需要它,做出的决断也一定是很绝然的。暂时没有它,说明我们眼下都还活得平顺。
阿弥陀佛。
张洪:《说话》,中国工人出版社,200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