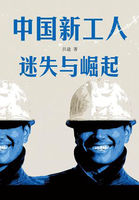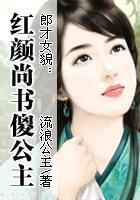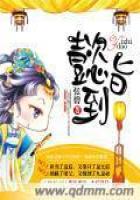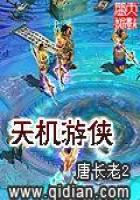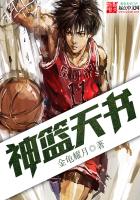人是一种有欲望的动物,按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人又是一种政治动物。如果通俗地理解,这里所说的“政治”,是指一种超生物学的组织要素,它赋予人们的群居生活某种公共性,压制人的一部分欲望,满足其另一些欲望。但这显然尚不足以表达人这一物种的全部特性,一些群栖动物,更不用说灵长类,显然也有复杂的符号系统,也遵循着某种“制度”,其个体成员也不能为所欲为。要想给人下一个较完满的定义,还得为“政治”补充上另一个要素:人是一种能够对欲望进行自我反思的动物。也就是说,他能够对自身的欲望形成某种“善恶观”,并随环境的变化而调整它。所以有不少人认为,对这种现象的理解,既可解释人类个体的行为,也可揭示社会制度的变迁或多样性的奥秘。
据赫希曼说,他写这本题为《欲望和利益》的小册子,发端于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的一句话:“人的欲望可能促使其做坏人,但其利益却阻止他们这样做。”这个命题的意义在于,对于人的欲望,可以分析出一种应当特别称为“利益”的欲望。在近代之前,并不存在“利益”和“欲望”之分。“欲望”中最突出的表现之一,即对金钱和财富的贪婪,被基督教认定人类“七宗罪”之一,奥古斯丁也把它同权力欲和性欲并列,称为导致人类堕落的三大罪恶。不过基督教神学的希腊化也给奥古斯丁的思考留下了烙印,他在谴责欲望的同时,还观察到在不同欲望之间存在着某种张力:比较而言,权力欲也许比另两种欲望要好一些,它对“荣誉”和“公共美德”的追求,抑制了另一些罪恶。这虽然仍是一种古代世界的欲望观,却为以后的“欲望制衡说”留出了余地。
文艺复兴以后,尤其是17世纪以后,人们逐渐失去了“能够用道德教化式的哲学或宗教戒律来约束人类欲望”的信心,于是他们开始寻找约束欲望的新方法。神的权威既已不足恃,对欲望本身的观察和分析也就随之产生。按帕斯卡尔的说法,人的欲望是“有秩序的”,而秩序是美丽的。这种美丽性,也许处于欲望者的意识之外,但它就像日月星辰一样确实存在。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理性主义崛起的时代,人的欲望也被客观化了,它是自然世界众多相互对立的因素之一,共同服务于某种冥冥中的力量。这种基于自然理性的思考,引发出许多非常著名的学说。例如,培根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严肃地思考“如何使一种欲望反对另一种欲望,如何使它们相互牵制,正如我们用野兽来猎取野兽,用飞鹰来捕捉飞鸟一样”。在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中,“私恶”可以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奇妙地向着襄助“公益”转化。黑格尔也说,决定着事物之目的性的“刁诡的理性”,可借助于邪恶来实现自身,故而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然而,这些学说不管从哲学角度听起来多么有意思,能否把它落实为一种真正可以制服欲望的制度,却是非常不确定的。
人的欲望得到克服或升华,仍然有赖于人类对欲望的重新认知,即从欲望中明确分离出“利益”的概念,它是发生在18世纪的休谟和孟德斯鸠等人的体系中。按赫希曼的文字考据,西语中“利益”(interest/intérêt)一词,在16世纪以前并无今天我们所使用的含义,对人类行为动机的分析,一直仅仅受着“理性”和“欲望”这一对范畴的主宰。此后一些专谈帝王术的文献,才使这种情况悄然发生了变化。罗昂的名言“让君主支配人民,让利益支配君主”,赋予了“利益”一词微妙而影响深远的含义:君主如果放纵“欲望”,是对其“利益”有害的事情。这里所说的利益,显然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欲望,而是变成了一种经过理性权衡的欲望。这一点更为清晰地反映在巴特勒主教的话中:“具体的欲望与……世俗的利益并不一致,具体的欲望既会导致邪恶行为,也会导致威胁我们世俗利益的鲁莽行为。”利益不再是一种邪恶的欲望,反而成了一种可以用来压制欲望的欲望。
在一个为“欲望很容易征服理性”而焦虑不安的时代,“利益”这一概念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它是一个可以沟通和平衡两者的因素:使欲望成为融入“理性”的欲望,使理性成为受“利益”驱动的理性。可以说,从欲望到利益的认知,鲜明地反映出人类具有惊人的自我反思能力,它最终促成了古老的人性论的一次制度主义转折。这就是休谟说的“没有一种欲望能够控制利己的欲望,只有那种欲望自身,借着改变它的倾向性,才能加以控制……我们在维持社会的过程中,要比孤立无援的状态下能获得更多的财富”。这种“倾向性的改变”,使一种新的组织形态得以形成,较之“欲望”驱动的行为后果它具有若干优点,如可预见性和持久性,更为重要的是,它使“贪婪变得无害”,这在孟德斯鸠“哪里有商业,哪里就有善良的风俗”一语中得到了最好的表达。
此外,它对政治生态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它使统治者获得了影响社会的巨大物质力量,后来的福利主义和新帝国主义可由此得到部分解释;另一方面,它也使统治者恣意用权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大受孟德斯鸠赞扬的动产的增长,它不同于土地这种传统的财富形式,其易于流动性限制了君主的暴虐。当然,它也使世界变得更为“庸俗”,使人生变得更加“无聊”,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用斯密对人们丧失“崇高精神”、喜好奢靡无用之物的嘲讽,或马克思的“异化说”,来加以证明。
此书篇幅虽小,但涉及的文献甚多,这里不及一一详述。概言之,它可被视为对资本主义发生原因的一种心理-观念史的讨论。人们在读过此书后,大概会留下这样的印象:它的核心问题——资本主义何以发生——肇端于韦伯,但它试图用“利益说”来取代韦伯的“理性化”。其实两种范式是可以相得益彰的,譬如,利用这种受理性调整的利益观,我们可以解释资本主义扩张与以往历史上的大规模族群冲突之间有何不同。就此而言,作者有条件接受的熊彼特的观点,我倒是觉得更为正确,他认为,“一般说来,与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不同,扩张领土的野心、殖民扩张的欲望和好战精神,并非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更准确地说,它们产生于残存的、前资本主义的精神。然而不幸的是,这些精神深深地植根于欧洲主要国家的统治集团之中”。熊彼特这段话并未涉及欲望和利益之分,但它却暗含着这样一层含义:殖民扩张是源于赫希曼所说的“欲望”而非“利益”。我们不必否认资本主义为殖民帝国提供了强大的技术和物质手段,但那种征伐与扩张的内在动力,与其说是来自资本主义本身,不如说同奥斯曼帝国、蒙古帝国或西班牙帝国的联系更为密切。这种扩张与掠夺的现象,是前资本主义欲望的遗存,而不是来自“开明的自利”——工商业阶层对“欲望”的一种独特的理解。这个团体或许也重视民族国家的建设,但是与过去的统治集团不同,它并不把国家的武力,而是把“温和的商业活动”,视为获取财富的主要手段。所以,它所建构的体制,也不同于前近代的帝国体制,而是被差强人意地称为“资本主义”。
赫希曼:《欲望与利益——资本主义胜利之前的政治争论》,李新华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