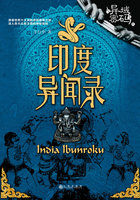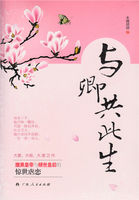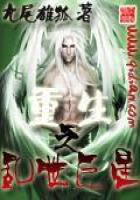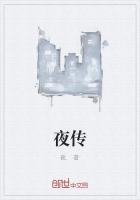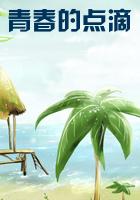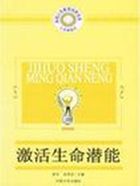1962年下半年,印度得寸进尺,在侵占我大片国土之后,又疯狂地进行武装挑衅,不断制造流血事件。我在反复警告无效、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奋起自卫还击。
这个故事说的是我东线反击中的某一战斗。
1962年10月20日清晨,东方刚刚露出一丝光亮,巍巍的雪山像一排巨人俯视着克节朗河。
从昨天晚上起,我军的各攻击部队就源源不断地走上了阵地的各个歼击地点,各在各的岗位上,静静地等着攻击命令。
司令员张国华和副司令员邓少东站在塔格拉山脊上,等待着那庄严时刻的到来。离他们不远,是我军的加农炮和迫击炮阵地。
7时15分,7时20分,7时25分……风轻轻地扫过克节朗河两岸的丛林,残余的星星还在眨着眼睛。
张国华看了看表,邓少东看了看表。……7时29分!张国华望了一眼邓少东,邓少东点了点头,二人同时又看了看副司令员赵文进。
“准备!”赵文进对身旁的炮兵司令劳宣下了命令。
大炮一下子撤掉了伪装,炮口升了起来。黑黝黝的炮管像一支支高伸的手臂,刺向蓝蓝的天空。
7时30分,“射击!”赵文进眼睛一亮。话音刚落,旁边的信号兵就发出了两颗红色信号弹。
“轰隆!”顿时,我军阵地万炮齐发,一下子天摇地动起来!一道道尖利的红线戳破了天空,落在对岸印军的阵地上,接着就是一团团火光,一团团浓烟,一片片炸响。火光闪过之处,乱石、武器,还有印度士兵的残骸便纷纷落下,克节朗河两岸一下子充满了呛人的火药味。
2连在五号桥头集结,对岸是印军的一个据点,驻扎着一个连的兵力。2连的任务就是敲掉这个连,然后配合从四号桥、三号桥、坦普洛格桥进攻的兄弟部队,迅速攻下章多。
突然,一阵嘹亮的冲锋号声响了起来,我军炮火延伸了,冲锋的时刻到了!2连连长杨士昌一下子跳了起来,大吼了一声:“冲啊!”话音刚落,从堑壕里一下子跃出了许多战士,一部分战士迅速冲上了五号桥,一部分战士干脆直接冲入河里趟水而过,这时正是枯水期,克节朗河已经可以徒涉了。
印军第7旅旅长达尔维准将刚刚起床,外面还是一片漆黑,天冷得很厉害。但达尔维还是迅速穿上了衣服,喝了勤务兵送来的一杯热茶后,便走出了旅部。
他整了整衣服,走到旅部左边的一个阵地。士兵正抱成一团取暖,达尔维没有说什么。
突然,天空一下子被刺破了,炮弹呼啸着落在印军的阵地上,阵地顿时成了一片火海。士兵惊叫着乱窜了起来,达尔维准将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勤务兵一下子拉住他的手,拽着他跑回旅部。几分钟过后,达尔维才清醒过来:中国军队开始进攻了。
外面的炮火更激烈了,炮弹不断地在旅部外面爆炸,临时修筑的防御墙不时地倒塌下来。达尔维拿起电话机,但怎么也摇不通,通向各营的电话线已经被排炮全部打断了。
杨士昌带领士兵冲过五号桥以后,立即率领两个排向五号桥西南的印军据点冲去。一个月前,印军利用地势修筑了这个据点,并部署了旁遮普联队的一个连的兵力。应当说,这个据点修筑的是相当巧妙的。
就在离五号桥西南200多米的地方,是一座相对高度200多英尺的山峰,从五号桥到章多的小路正从这座小山的脚下蜿蜒而过。印军在山口上利用自然地势修筑了几个交叉火力点,封锁住我军的前进路线,因而我军必须首先打掉这个据点。但从桥头到山脚是一片开阔的谷地,这给我军的进攻带来很大困难。
杨士昌在战前就已经侦察好了印军的火力配备状况,他知道,关键问题在于这片200米的开阔地带,只要能冲过这片谷地,其他问题就好办了。因而我军炮火一延伸,他便乘印军尚未反应过来,立即带队冲了上来。
旁遮普联队是被印军称为能征惯战的联队,守卫五号桥的3连连长鲁比克上尉更是英勇善战。他曾经参加过二次世界大战,参加过北方各邦的战斗,作战经验十分丰富,达尔维旅长因此把守卫五号桥的任务交给了鲁比克。但鲁比克做梦也没有想到,他遇到了更强硬的对手。
炮轰一停,鲁比克立即冲出掩蔽所。在他眼前的是一片狼藉的景象,一个印度士兵的半截身子埋在泥土里,头部已经被炸烂了;另一个受了伤,两条腿搭在折断了的木头上。鲁比克顾不得这些了,立即命令跟在身旁的传令兵:“迅速命令各排占据阵地!”
杨士昌正率领队伍快速推进的时候,敌人的机枪响了,子弹“哒哒哒”地在他身边跳跃着,几个战士倒了下去。“不好!”杨士昌暗暗叫道。没想到敌人的反应也够快的,他们这时已经冲到了离敌人60米处,再有几秒钟就上去了,却一下子被压在山脚下。往前40米是一片灌木丛,看到这片灌木丛,杨士昌顿时眼睛一亮,他立即命令身边的通讯兵:“呼叫司令部,我被压在山脚,请求三分钟炮火支援!”
我军的大炮又怒吼起来,印军的阵地顿时遍地开花。趁印军躲避炮火的机会,杨士昌一挥手,率领十几个冲上来的战士几个窜跃,瞬间扑到了灌木丛边。我军炮火一延伸,杨士昌和战士们一跃而起,几步便冲上了山头敌人的矮墙。几个印度士兵刚刚从泥土里钻出来的时候,十几支冲锋枪一齐开火,他们连哼都来不及就被撂倒了。右方4名印度士兵刚想逃走,杨士昌一梭子打过去,又将这4名家伙打翻在地。接着,杨士昌和战士们分成两组,分别沿着矮墙向左右扑去。
20分钟后,炮轰停止了,达尔维走出了旅部,眼前的景象使他大吃一惊:山脚下无数的中国士兵正冲过河来,双方的军队挨得如此之近,以至看来好像是发生了一场哗变一样。
我军采取的是中央突破的打法,为了保证作战计划的进行,指挥部在三、四号桥之间部署了三个团的兵力,其中一个团担任正面攻击,其他两个团分别从两侧渗透,然后从侧翼进攻。战斗打响后,部队进展十分顺利,三号桥、四号桥的拉加普特联队仅仅抵抗了一个小时就全线崩溃了,我军迅速向前推进,拿下了扯冬哨所。但在攻打廓尔喀联队时却遇到了麻烦。廓尔喀联队第1营驻守在第7旅旅部的西南,那里是一个较高的山嘴,前面是几百英尺的峭壁,只有一条崎岖的山路通向山顶,印军利用有利的地势修筑了坚固的工事。
当我军某部1连推进到山脚下时,被压在树林里动弹不得,战斗进入了胶着状态。正在连长唐吉万焦急万分时,作为预备队的火箭筒班冲了上来。火箭筒班班长钟琪骂了一句,接过战友递过来的火箭弹,迅速架好了火箭筒,瞄准敌堡一扣扳机,只听一声巨响,敌堡射孔里冲出了一团团浓烟。树林里的战士一跃而起,冲向山顶。印度的廓尔喀联队也是训练有素,当即挺着明晃晃的刺刀扑了过来,双方展开了一场白刃战。我军后备部队不断地冲上山来,印军抵挡不住,一下子崩溃下来。
拉加普特联队和廓尔喀联队的相继覆没,使得达尔维的旅部成了孤家寡人。面对着被包抄的危险,他决心撤退。
达尔维看了看地图,只有一条后撤的路线,那就是章多。然后绕到嘎坡第一山口,最后向南到不丹,经过布莱亨到塔希岗宗,最后到印度。他担心鲁比克上尉能否守住五号桥,如果五号桥失守,那么中国部队非常可能直接进军章多。这样一来,他的后退路线就全被切断。
不幸的是,正在他这一行人快要走到章多时,遇到了被打散的鲁比克上尉,上尉沮丧地告诉他:五号桥失守后,上尉带领剩下的十几个士兵向章多撤退,不料中国部队推进的速度更快,在离章多还有1英里的地方,中国部队赶上了鲁比克一行。“但是”,鲁比克上尉说:
“他们根本不理我们,就一路奔章多去了。似乎他们知道会有人收容我们似的,而他们不愿要我们这些累赘。”
达尔维心里猛地一凉,看来,中国部队知道,拿下了章多,就是捏住了口袋,在这海拔1万英尺以上的高山地区,第7旅的残余部队如果不自己走到章多交出武器,就只能在冰天雪地里冻饿而死。
22日,在达尔维前面出现了一支中国部队。这支部队根本没有开枪,而是静静地围了上来。达尔维走上前去,用英语说道:“我是印军第4师第7旅旅长约翰·达尔维。”
他想:第7旅再也不存在了。
守卫印军阵地右侧一号桥的第4近卫军联队和旁遮普联队并不比第7旅幸运。第7旅的覆灭使得一号桥左翼完全暴露在中国的炮火之下,第4师师长普拉沙德少将立即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下令将联队撤到哈东山口——仲昆桥一线。哈东山海拔1.35万英尺,位于从一号桥通往色基姆的必经之路上,与西边的章多两相对应,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但是已经晚了,当两个联队后撤时,他们却突然发现哈东山口已经被我军占领了。我军只轰不攻,就是为了拖住印军,在此同时,以一支作战分队神不知、鬼不觉地插入克节朗河阵地与哈东山口之间,截住了南下的印度军队。成连成连的印军被缴了械,侥幸逃出的印军向西败退,历尽千辛万苦,经由不丹走回了印度。
送给蒋介石的“寿礼”
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单方面撕毁合同和协议,突然撤走专家。萨姆-Ⅱ导弹,我们还没来得及仿制出来,苏联人就甩手了,按协定提供的62发导弹越打越少。
这令人心痛的事实,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一步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希望外援,但绝不能依赖它!只有独立自主地发展才是唯一出路。
党中央的决心变成了全国人民的行动。各路才子智星,八方专家学者,解放军指战员秘密而又神速地云集大西北,着手建立我们自己的战略腹地,加紧研制、试验我们自己的尖端武器。
美国和台湾国民党政府急不可待地要得到这些战略情报,一架U-2飞机被击落,另一架训练时自毁。
他们仍不死心,又派遣两架U-2飞机,从1963年3月28日到11月,入窜大陆17次,多数是直奔西北地区上空侦察。新来的两架不同于以前被我击落的U-2飞机,上面加装了针对萨姆-Ⅱ制导雷达工作频率的电子预警系统。当我萨姆-Ⅱ制导雷达电磁波照射U-2飞机时,它就向飞行员发出有地空导弹威胁的报警信号,敌飞行员由此判断我导弹阵地方位,马上转弯绕飞,逃避导弹的打击。无论我导弹营分散设伏,还是集中组成大面积火网,都未获战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