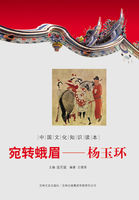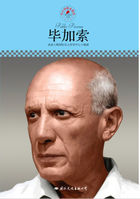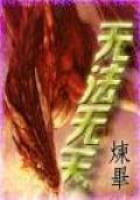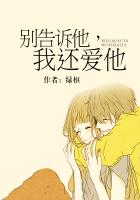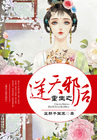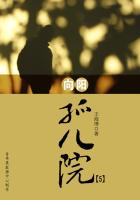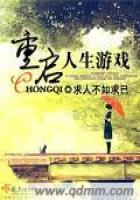冯宪珍:中国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1954年生,1977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
主要戏剧作品:《大风歌》、《灵与肉》(获中直文艺团体观摩评比演出青年演员一等奖)、《哥们儿折腾记》(获首届梅花奖)、《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命运的拨弄》、《老顽固》、《故意伤害》、《死无葬身之地》(获文化部优秀表演奖、中国话剧研究会话剧表演金狮奖)、《老妇还乡》、《青春禁忌游戏》(获上海白玉兰女主角奖)、《SORRY》(获梅花奖)等。
王毅:你是1977届中戏的,当时中戏怎么1974年就恢复招生了呢?
冯宪珍:我是“文革”后期1974年入学的,1977年就毕业了。它是属于江青搞的那个五七艺术大学,比如上戏有奚美娟、潘虹,中戏我和王洁实是一个班的,我们是第一拨,陈宝国是第二拨。只有这两个班,然后1978年就恢复高考了。
老师是谁?
张仁里、徐晓钟当时都在。
中戏没有受到“文革”的影响吗?
当然受影响,教学都是样板戏的教学方式,到了后期才好一些。图书馆开放了,前期图书馆里都是一些“文革”时期的宣传书籍,文学名着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就多起来了。
粉碎“四人帮”的时候你还在上学?
对,后来回放当时学生大游行的录像,打腰鼓,扎着小辫,都是我们班。
这个班是怎么招上来的?
也是全国招生,也要考试,跟现在差不多。唯一不同的是,要政审,要工农兵子女、革命干部子女。我还是挺感谢我们老师的,当时政审我们班就我没过,我父亲在接受审查。春季入学的时候,我直到四月份才最后一个拿到录取通知书,别人都开学将近两个月了。我当时以为肯定没戏了。
你当时在哪儿?
在南京微分电机厂,已经工作了。现在看这厂是相当不错的,是军工转的。但那我也不愿意待。对我来说像在监狱里面待着,受不了。
怎么就想到要考中戏呢?
我在工厂的时候就不安分守己,一直在外面折腾。当时不是有宣传队、演出团吗?我又参加乐队,又演又唱又跳,什么都干。所以当时一听说中戏在招生,马上就去考。
当时中戏的教学是什么情况?
教学的元素还是按照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系的,从小品开始。老师还都是原来的老师。我们是中戏老师经过“文革”没有教学以后,接到的第一个班,师生关系特别好。那时候老师刚从干校回来,都没有老师的架子,学生年纪又都很大了,有的都三十多了,跟老师像哥们儿,不像现在学生特怕老师似的,现在还经常聚会。
毕业就到了中央实验话剧院?
当时是中国话剧团。中国话剧团是“文革”时把儿艺、青艺和实验话剧院合并了。当时还演了几个戏,《枫叶红了的时候》,粉碎“四人帮”的戏,特火。然后1978年开始分院,筹建中央实验话剧院和儿艺、青艺。当时我在的剧组实验话剧院的老人儿居多,所以说服我去了实验话剧院。我还是挺幸运的,我们剧院很单纯,都是各个学校的学生。
当时几个比较有影响力的戏比如《灵与肉》、《大风歌》都是你演的。
陈白尘的《大风歌》演了近300场,《灵与肉》还是在《大风歌》之后。还有《最后一幕》,是我们剧院蓝光写的。
那时候一个戏演100场,一点都不稀奇。
一点都不稀奇,一般都是奔200场300场去的,比现在演电影还勤,而且还有日夜场。那时票也便宜,两毛钱一张票。我们演一场才拿两毛六。
而且所有演员都一样,是吗?
都一样。没有什么主角、配角的差别。
然后你的《灵与肉》、《哥们儿折腾记》就获梅花奖了,那时候评梅花奖是什么状况?
很严,因为是第一届。我都不知道风声。后来(徐)晓钟老师给我打电话透了个信息,说有我,祝贺我。我高兴得不得了。第一次嘛。
跟你一起得奖的演员现在都在干吗?
那时候得奖的话剧演员有五个,李雪健、尚丽娟、刘文治、蒋宝英和我,现在只有我一个人还在演舞台剧了。太老了,一说我的历史就觉得太长了,是该退休了。
后来你比较被大众熟知,是因为《爱你没商量》那个电视剧吧?
对。当时导演来找我,我说我不拍电视剧,当时特瞧不起电视剧。结果导演见了我,就更加坚定,非要找我。后来我就纳闷儿,为啥非要找我。我看了剧本,觉得这还真是非我莫属。话剧导演当年我接触得最多,尤其是女导演,像陈颙。我当时那个气质,剃一个短头发,男不男女不女的,都不用化妆就是那个角色了。当时我胖得不得了。因为拍这戏之前出了一次车祸,被汽车撞得很厉害,牙都撞掉了,脸都破了烂了,被送到医院急救。我爱人就劝我别拍这个戏,但他们还是老缠着我。当然后来拍的过程中和他们合作很愉快。但戏出来的结果我觉得反响一般。
当时觉得演电视剧和演话剧有什么区别吗?
我觉得没什么区别,能演舞台剧,演电视剧就是手到擒来;但演影视的未必能演舞台剧。我不赞同把演员分成舞台演员、影视演员。在表演领域,演员应该是无所不能的。不能说你面对机器你就发怵,在舞台上面对观众就撒欢;或者反过来,对着机器你无所畏惧,对着观众就犯难,这都不是好演员。我挺佩服苏联的那些表演艺术家,比如《办公室的故事》那两个演员都是舞台演员,在镜头面前表演得非常自如,给他们配音都觉得他们的演技始终压着你。
后来北京演出的《小市民》里面有一个演员就是《办公室的故事》里的男演员。
对,我认出来了。他都七十多了,胖了。他就是舞台演员。包括那个柳德米拉,有一年来,特意要求见我。
她也知道你给她配音了?
是啊,包括导演梁赞诺夫,还有《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导演,激动得不得了。其实我们跟他们真的有血脉相连的地方,很亲切。
你说话剧是生命中的唯一,现在说这话的演员很少。
但我觉得我不能干别的了。电视剧我也不看,自己都不看的东西我怎么去演。我没有任何兴趣去看某一个电视剧。
你觉得是剧本的问题,还是表演的问题?
我觉得它不是艺术。在家里干什么的时候都可以看,它不像剧场、不像电影,你必须去剧场待四五个小时,端端正正坐那儿看。那是你在为观众表演,那是艺术。我当时拍电视剧,去东北的小地方,天天在小餐馆里,溅着酱油点子醋点子,你觉得你是在被亵渎。说老实话,我这人骨子里比较清高。我特别热爱话剧吗?未必。但是,没有其他事情可干。做买卖,我不会,遗传里没有这个基因。电视剧也拍过,但自己都不愿意看。话剧的东西我都存档,有盘,有老剧本,可电视剧我没有存的欲望。
但话剧受限制。
对,它是太沙龙了。
现在话剧演几百场都没可能,也就几十场,北京、上海走一走。
我以前觉得我是生逢其时,但有一年去伦敦西区待了半个多月,每天看戏,看到人家一条街一个剧院挨一个剧院,而且半年前票就订出去了,还有日场,而且演的都是传统剧目,《推销员之死》这样的剧还在演。我看到这些,又觉得自己生不逢时。这么好的氛围,我没赶上。
这就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但这也不能操之过急。“文革”带来了一段饥渴,1978年是爆发,这也是一个极不正常的现象。但现在这样的现象也不正常,我觉得是正在不断往上攀爬,路程艰难。现在完全市场化,电影搞成了那样,戏剧也是。现在经济发达了,可道德水平在下降,这时候的戏剧是很悲哀的。我也反对用一个形式去拯救某某,你没有这个义务去拯救谁,我不赞成拯救戏剧这个说法,不用拯救。就像一个人,你把他闷在水里十分钟,他为了生存会反抗的,不会束手待毙的。只要他的心还在跳。
你之前说话剧就该小众,就该沙龙。
不能像1978年那样,人人下了班都骑自行车去看话剧,这也是不正常的。那时候经济极度衰退,人精神上极度饥渴。但现在的人,被经济这杯酒灌醉了,酒足饭饱到歌厅去,他还要文化干什么。
沙龙化会不会让明白的人更明白,不明白的人更不明白?
但我现在就很喜欢去大学,跟学生搞剧社。这些学生未必是搞戏剧的,我想让他们认识表演,认识戏剧。
有一年11月,文化部搞的送高雅戏剧进校园,把我感动得,就像到了1977年。孩子们说,怎么还有这么好的表演形式,我们在电视上只看到超女,看到这个都傻了。谢完幕学生都不走。我们当时演出的环境很差,就是一般的礼堂,没有接待过正式演出,门都是开着的,根本谈不上什么音响效果。为什么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孩子,反而更能接受话剧形式,而经济发达地区却拒绝戏剧,就是我前面讲的那个原因。戏剧真不是没市场,中国地域太广了,不能光守着上海、北京这几个地方。你要出去了,你会感到别样的天地,你会觉得你活了。人都是平等的,他们有权利接触高雅艺术,我们有义务把高雅艺术送到贫困的地区,送到他们家门口。要培养观众,不是没有观众,是我们没有找到。
我不太赞成现在有的戏剧像游戏。因为我觉得现在的社会到处充斥着游戏和娱乐。现在我们只是用甜蜜来麻醉观众,那种苦、痛、冲击少。包括所谓大片。演员在上面声泪俱下,观众无动于衷,因为离观众的生活太远。
做戏剧的,首先自己要为之所动。我演戏很使劲,每一场都让自己灵魂出窍。年轻演员问我,说你这样不累吗?我生活中很轻松快乐,但就在舞台上的两个小时,我要让自己筋疲力尽,我要大哭大笑,这是最享受的。我二三十岁的时候没有这种感受,直到五十岁以后,慢慢发现,人这一生不能只追求一种感觉,太乏味了。话说回来了,假如我现在像三十岁的时候那样一贫如洗,我肯定会像无头苍蝇一样追着拍电视剧,因为这个来钱快。我不反对年轻演员去拍电视剧,我很能理解。但人在物质满足以后,是需要精神的释放的。我就是在演了《死无葬身之地》以后,这种感觉慢慢强烈起来。我发现我在舞台上是最美的,在镜头前都没有这种优势。我觉得我天生就是舞台演员。我相信那些四五十岁的观众看了我的戏,会带他们的孩子来看我的戏,话剧观众不会泯灭的。
我在一次儿艺的会上发言说,假如国家不重视儿童剧,就是不重视未来的戏剧观众。戏剧也要从儿童抓起。在儿童剧院门口会看到孩子因为没买到票而大哭,在我们剧院门口就没有这样的情况。为什么?因为观众断档。我不是指望戏剧舞台有什么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的变化,但改变是一步步来的。哪怕有的观众是为了炫耀高雅而来看戏,我也要让他在走进剧场以后,忘掉自己的身份,跟着我的戏走。这就是你的成功。
现在很多作品不敢展示痛苦。比如我们的《青春禁忌游戏》,有人就说,为什么把这么残酷的东西摆在舞台上演,为什么不演一些美好的东西?但中国的苦难还少吗?我们却不去碰它,而俄罗斯人敢去碰它。
所以我觉得,戏剧去拯救一代人,是没有这个义务的,但要让观众慢慢觉得,剧场是一个温暖的地方,舞台的灯光很梦幻,他愿意走进来感受这一切。不能光在家里看盗版盘。
你特别难忘舒强导演对你的指导。
舒强是原来实验话剧院院长,已经去世了。《最后一幕》他是艺术指导,《灵与肉》他是总导演,《大风歌》也是。他是一个很各色的老头,不苟言笑。在生活中遇到他,会很畏惧他。你心里没底,不敢进他的排演场。他跟晓钟老师不同,晓钟老师谦虚和善得你不忍心顶他一句嘴。舒强是威严的。晓钟老师是要求导演给一,你反三;而舒强是你不准备十你不敢进排演场,每天进表演场心里要有东西。他当时给我们排戏时,永远在挑剔,很少鼓励演员。我排《大风歌》的时候,导演琢磨孝惠帝让谁演。假如用男演员,恐怕演不好这个小男孩的稚气和柔弱。舒强最后出人意料地让我来演。当时编剧陈白尘就犹豫,让一个女演员来演男皇帝。但舒强坚持了,说我们到舞台上看。舒强也比较了解我,我年轻时,是比较男孩子气。
当时你多大?
28,将近30。我接到这个剧本的时候,也很紧张,戏不是很多,但激情戏很多。看完陈白尘的剧本,就会掉眼泪。这人物已经活灵活现了,假如演不出来,就失败了。对舞台演员来说,假如剧本人物没有血肉,发挥起来空间更大,但陈白尘的剧本不是,所以我的压力很大。舒强排戏的时候,就像盯一个猎物一样盯着我。他不太说话,记性特别好,谁在哪个位置,先迈哪只脚,下几级台阶,他脑子极清楚,谁也蒙混不了他。这个角色磨合了三个多月。
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记得他了。但舒强能让一个演员从不自信到自信,从毫无光彩变得在舞台上光芒四射。就像一开始你是一个铁丝搭的架子,他往上面铺皮肤的质感,到头发丝,把你塑造成很细腻很完美的形象。我特别感谢他。《大风歌》完了后,紧接着是《灵与肉》,又是他导演,又是他主张让我演女主角。我刚脱掉皇帝的大袍子,又来演一个美国的少女,一时很难从角色上转换。《大风歌》里迈丁字步,拿着架子,一呼百应,现在要含情脉脉,谈情说爱。在排练场,我不由自主就拿出了皇帝的架子演少女。舒强在排练场会很挑剔地指出来,苛刻得让你受不了。
《灵与肉》里,我要亲吻男演员。1980年代,在舞台上要亲吻男演员,心理上是很有障碍的。舒强就让我回去想一个替代的办法,我想得头发都快掉了。第二天到了排练场,我就先亲自己的手,拍到男演员额头,再亲手,拍到他的鼻子,无数遍反复,舒强看了高兴。这既是美国人的表达方式,又是中国人能接受的,而且能表达女人的那种情绪。这是舒强第一次表扬我。他在排练时会给你造成一种压力,但你会迎着这种压力上,而不是退却,退却就完了。
这是跟他最后一次合作吗?
对。后来他去儿艺拍了《报童》。后来他年纪大了,只给我们的戏做做艺术指导。他最好的戏就是上面这两个,也是我在话剧院立足的两个戏。我觉得他不是一般人。他内心特别丰富,你能感觉到他满脑子都是戏,思维在飞速流转,滚烫的激情让你害怕。这个老头很可爱。
他是延安鲁艺的?
对。他最早是国立剧专(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的。他跟晓钟老师都是南京人,我也是南京人,觉得他真的是我的长辈。我特别为他感到惋惜。他没赶上好时候,没多排几部好戏。我们剧院很多人像韩童生都是他带出来的。我挺想念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