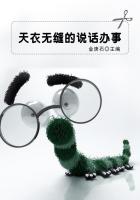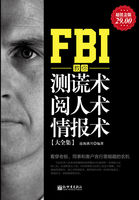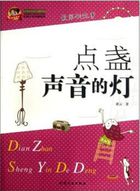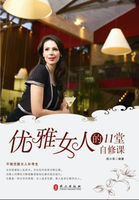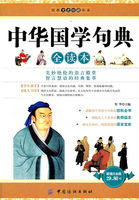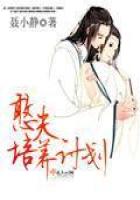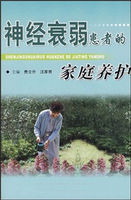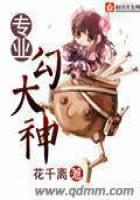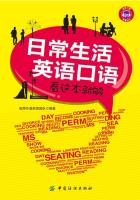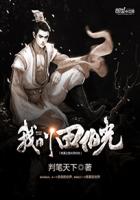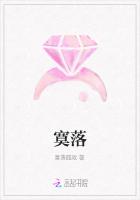人总有三亲六故,周恩来也同样为人亲眷。如何对待亲友,周恩来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周恩来从小就厌恶那种家运兴隆时,宾客如云,趋之若鹜;家道衰落时,则惟恐避之而不及的势利小人。无论在动荡不安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当了共和国总理后,他都始终如一地保持着与亲友的密切联系和情谊。然而,他爱亲友却从不为亲友谋私;他重情意,但从不拿原则作交易,在处理与亲友的关系时,他始终严守共产党人的党性和原则。
周恩来出生在一个大家庭中,叔伯、兄弟很多。但在他出世后,这个大家庭就败落了。在家庭败落中,一家人和衷共济,这使周恩来从小和家人的感情很深。自从到沈阳求学后,他多年远离故乡,常常思念家中亲人,有时竟很痛苦。在南开学校读书时,他曾在作文中写道:"津辽七载,所余梦寐者,亦仅思瞻我乡土,乐我兄弟,省我叔伯而已。乃境遇困人,卒难遂愿。"到了除夕之夜,同学们大都回家了,他思念乡土家人之情就更甚了。他又在作文中写道:"今日何日耶?非家庭团聚时耶?余也何如?"他想念家中亲人,以致于"泪盈枕席,交不能寐矣"。
他的叔父周贻奎,从小偏瘫在床,周恩来在日本时,他病逝了。接到堂弟报告噩耗的来信,周恩来十分悲痛。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身在海外,猛然接着这个恶消息,那时候心中不知是痛是悲,好像是已没了知觉的一样。"第二天又写道:"想起家中一个要紧的男子也没有,后事如何了法?这几年来八伯(指叔父周贻奎)同八妈的苦处已算受尽了,债务天天逼着,钱是没有,一家几口子是要吃的,当也当尽了,卖也卖绝了,借是没处借,赊是没处赊,不要说脸面是没有了,就是不要脸向人家去要饭吃,恐怕也没有地方去要。八伯这个病,虽说老病,然而病到现在何曾用一个钱去医治的呢?简直说是穷死了。"接着又写道:"连着这3天,夜里总没有睡着,越想越难受。家里头不知是什么样子,四伯(指他伯父周贻赓)急得更不用说了,只恨我在海外,不能够立时回去帮着四伯、干爹(指他父亲周劭纲)做一点事儿。如今处着这个地位,是进不得也退不得。"可见,周恩来对叔父的去世,是何等的悲切,对叔父生前乃至他整个家庭的困境,是何等的痛切!而对自己身处异国他乡,不能对家人有所帮助,又是多么的愧疚!这些都很突出地反映了青年周恩来对长辈们的感情。
周恩来对长辈的尊敬和热爱,在他后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后,也丝毫未减。
1939年3月,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前往浙江西部视察工作,顺路回绍兴省亲。有一天,他的姑父王子亲先生来访,周恩来恭恭敬敬地请王先生进入室内,并将他推至上座,自己完全以一个晚辈的身份接待,丝毫没有"政治要官"的架子。后来,周恩来见到周氏族长周希农老先生时,立刻恭敬地向周老先生行了三鞠躬礼,然后,推老先生坐在首位,自己坐在下位,恭听周老先生介绍绍兴周氏族中的一些情况。
尽管公务繁忙,周恩来还是挤出时间一一满足亲戚要他题词的要求。他为自己的大姑父挥笔写了岳飞的"满江红",接着,又为三姑父写了"生聚教训,二十年犹未为晚",落款还写了"愿吾叔老当益壮"。一个借岳飞之志,抒发民族志士收复失地气壮河山的气概,一个借越王勾践复国的故事,暗示持久抗战和抗战必胜。充分体现了周恩来尊传统,重亲情的一面,同时也表明了周恩来时刻不忘自己革命者的身份,在任何时候都不忘宣传救国真理、革命思想,在处理和亲友的关系时也不例外。
周恩来是长兄,又很重感情。在10岁时他就领着两个弱弟,从清江浦回淮安度日。很显然,他和两个相依为命的弟弟的感情是极深的。我们可以从周恩来给他舅父万富之的信中体会到周恩来对幼弟的深深爱护之情。
1916年,他在天津,二弟周恩溥也来天津,周恩来给舅父写信说:
"……溥甥(即周恩溥)遂于当日劝身,前日下午抵津,一路尚属平安。现寓四家伯处,拟令其暂束身心,俾一切习惯渐变故态,然后再量材施教,以冀其成。惟恨时机已晚,不克受完全教育。七载荒废,责在父兄。今而后知教育子弟事,非可疏忽视之,致贻后日无穷之悔也。"
做长兄的责任感以及对弟弟的爱护之情,感人至深。
对亲兄弟如此,对堂兄弟周恩来也很有感情。1946年,他率中共代表团驻南京,他的堂兄嫂去看他。我们可以从周恩来给他们的信中看到周恩来和他们的感情。
铁仙四哥嫂:
相别几近30年,一朝唔对,幸何如之。旧社会日趋没落,吾家亦同此命运,理有固然,宁庸回恋。惟人生赖奋斗而存,兄嫂此来,弟处他人檐下,实无可为助。倘在苏北,或可引兄嫂入生产之途,今则只能以弟应得之公家补助金5万元,送兄嫂做归途费用,敢希收纳。目前局势,正在变化万端,兄嫂宜即返扬,俾免六伯父悬念。弟正值万忙之中,无法再谋一面。设大局能转危为安,或有机缘再见,届时亦当劝兄嫂做生产计也。
匆匆函告,恕不一一。顺颂旅安,并祈代向六伯父问候安好为恳。
七弟拜启
6月11日
弟妹附笔。
"相别几近30年,一朝唔对,幸何如之。"表达了周恩来与阔别近30年的党兄嫂相见的无比兴奋的心情,我们也从中看到了周恩来对堂兄嫂的感情是何等的真挚。当时,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周恩来代表中共驻在南京和国民党及军调部的美国代表交涉、谈判。由于国民党不断破坏,局势变化万端,国民党特务也专门盯着周恩来,所以,他要堂兄嫂赶快离开南京返回扬州,并"以弟应得之公家补助金5万元,送兄嫂做归途费用"。可见,周恩来对堂兄嫂是非常关心、体贴的。
1968年,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健初中毕业后,主动申请去内蒙古大草原锻炼。周恩来知道后,专门在家中为侄女做了送行饭,并一遍遍地嘱咐说:"我没有什么好招待你的,最好的食粮就是精神上的支持。你到草原去当牧民,我们坚决支持。"
两年后,周秉健在内蒙古参了军,当她穿着新发的军装,高高兴兴地到北京去见伯父、伯母时,周恩来不高兴地对她说:"你参军虽然符合手续,但内蒙古那么多人里挑上了你,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上?我们不能搞这个特殊,一点儿也不能搞。"
周秉健愉快地接受了伯父的批评,重新返回了内蒙古草原。在返回前,周恩来和蔼而风趣地问秉健:"想通了吗?同志!"站在一旁的邓颖超风趣地说:"你听见了吗?你伯伯称你同志啦!"周恩来接着说:"你回到草原,对你歧视会小,对你的照顾会大,要警惕!"
周恩来身居高位,可他决不允许自己的亲属由于他的关系而有一丝一毫的特殊。
1956年10月29日,周恩来在淮安老家的婶母患病,被县委送到人民医院治疗。后来,因病情反复,县人民医院便写信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立即给淮安县人民委员会写了回信。信中除表示感谢外,说:"我婶母的病我们知道是无法治疗,今后一切治疗还要麻烦你们(请县人民医院治疗好了),不要向外地转治。如果治疗无效,一切后事也请你们代为办理,但要本着节约和简朴的精神办理。现寄去人民币贰百元作为治疗和办理后事的费用。如不够时,请你们先垫付,事后来信说明支付情况,我再补钱去。"(《周恩来书信选集》,第532页)周恩来的婶母去世后,1957年4月19日又致信淮安县人民委员会负责同志,寄去安葬婶母善后费用所尾欠的垫款二十五元,并且在信中说:"我伯母家现还有陶华等人,今后她的生活费用均由我这儿接济,请当地政府对她勿再予照顾。"(《周恩来书信选集》,第535页)此后,周恩来对弟媳陶华治病期间所花费用也都如数寄还给淮安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