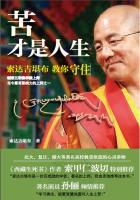周六的下午,我准时来到了珍妮花的别墅。韩森立在金碧辉煌的大门口迎接我,身着一套白色的亚麻休闲衣裤,看起来年轻而随意,精心修饰后的随意。
我优雅地走过去,朝他伸出右手,我的意思是采取中式的握手。他却伸出双手轻轻地握住我的右手说:“夭夭,你真漂亮!”
他的眼珠是琉璃般的棕色,平时透出一股平静的神气。但此刻眼眸中闪烁的热烈,让我相信这句话是发自内心的。
我穿着一件裁剪简单的白色及膝连衣裙,V领口开得很大,但只是视觉上的大,事实上它恰好地遮了我的胸,露出我细柔纤美的脖子。
裙子在右肩部交叉起来,两根飘带扎成一个蝴蝶结,随着我的身子每动一下,就轻盈地扑腾着,仿佛真有蝴蝶停在我肩膀一般。
我有着通常女孩子的浅薄个性,当有人夸奖漂亮时,心情立刻会明艳起来。“韩森,你也帅极了。”这一句就属于礼尚往来了。
但他高兴地咧了一下嘴,然后轻轻地拥抱着我,唇在我脸颊一触。很快,他松开了我,微笑着说:“我不一定总在你身边,但要玩得开心点。”
他还是一贯的细心,我叹息。人差不多已到齐了,有十来个,我扫了一眼,女士全是熟悉的面孔。
一帮三十出头的少妇,珍妮花所在圈子的密友们,一帮不缺钱的女人。除了搞服务的,出面负责接待女士们的,除了韩森,还有三位男士,应该全是他们公司出品。
那三个男人看上去,素质都不错,应该是高层管理人员。此刻被五六个女人围在沙发那边,热烈地讨论着问题。我走了过去,好奇地听了一会儿,不由莞尔。
讨论的问题是为何查尔斯王子不爱英伦玫瑰,反而喜欢又丑又老的卡米拉,几十年不变。
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那就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真不值得讨论。我们身边有很多人,不爱吃鱼刺燕窝,独独爱吃臭豆腐几十年不变。不过没人觉得这个小癖好,值得拿出来谈论罢了。
但看各位女士们一脸正色,仿佛在讨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国策,不可以马虎。她们说的话大同小异,一致认定卡米拉有过人之处,归结起来就是指有“驭夫之术”此类的能力。
我差点失笑,幸好及时收敛,否则难免又遭人嫌。
考虑到她们已为人妻,迫切需要在驭夫方面树立榜样或者楷模之类的人物,以便仿效,而力求自己的男人们能够对她们忠心耿耿,几十年不变。
更何况,在如今的中国,富有男人养情妇不仅是公开的事情,甚至还在质量和数量上互相攀比。围城里的妻子们,瞅着墙外茬茬鲜嫩水灵的花朵,心里的焦急是可以理解的。
恐怕难为了这几位男士,闲话是非本就不该是他们的长处。他们眉宇间不无尴尬,但更多是焦急。
因为今天这帮娘们,全是他们公司的目标客户群体。今天的聚会,为的是拉拢她们,尽管他们心里不屑于这样的八卦是非,但表面上,还得装出兴趣盎然的模样。
结了婚的女士比较大胆,当中一位,已隐隐提到是否卡米拉床上功夫过人,将查尔斯迷得七晕八素。
客厅的空调冷气很足,我穿着薄薄的衣衫,已感到凉意阵阵。其中一位男士却开始额头沁出细细汗球,他摸摸额头,无奈地说:“我觉得,原因在于卡米拉一直穿我们公司生产的内衣。”
最笨的人也听出这是一句玩笑话,所以大家全都轰笑,我也不例外。鉴于我实在加入不了这样的谈话,于是便在这笑声中,穿过正厅旁边的一个娱乐小厅,来到外面的草坪上。
太阳伞下,白色休闲椅上横陈着一个凹凸有致的肉体,穿着黑色的比基尼泳衣。屋宅的主人珍妮花,放浪形骸的生活并未在她的肉体留下过多的痕迹,她看起来依然娇嫩芬芳。
可此刻,她身旁另一张椅子上歪着的男人,让我有一种头顶上天雷滚滚的感觉。好在卢远航没穿泳衣,这次戴着一个深褐色的墨镜,我看不清楚他的眼神。
珍妮花摘下大大的浅黄色的太阳镜,挑起了大拇哥,眯起眼睛微笑着,说:“夭夭,你来了!快过来坐,今天很漂亮哦!”
我假装听不见,在她另一边的休闲椅上坐下,问:“珍妮花,你身为主人,怎么自己躲起来偷懒了?”
珍妮花和卢远航交换了一个表情,无所谓地说:“今天我也是客人。再说,我还有客人在呢!夭夭,你见过的,这是卢远航!”
见过好多次呀!我心里感叹。卢远航整个身体犹如美人春睡般,侧躺在休闲椅上,一只胳膊撑着下巴,面朝着我的方向。
他懒洋洋地摇摇他的左手,表示打招呼。我点了点头,表示收到。
我笑着对珍妮花说,“你倒是能及时调整自己的位置,乐得清闲。”
她扭头看着卢远航,问:“远航,你刚才不是要走,有时间的话,要不要一起玩一下?”
“董事会开会是下周二,我的秘书当天会给你电话的,记着不许缺席呀!”卢远航看了看表,摇了摇头,对珍妮花的提议,给予了否决。
“我晚点还有个约会,去早了也没用,要么我自己呆会儿吧!你别管我了。游泳就不参与了,这些人下去,还不成煮饺子了?”
我看了看只有标准游泳池2/3面积的家庭泳池,心想十来个人挤在里面,可不成了小孩子的嬉水池了。
珍妮花和卢远航的关系,应该是源远流长的那一类,于是也不再管他。她转头看我,催促我去换泳衣。
我本来是不太想去游泳的,可卢远航这厮的意外出现,倒帮我下定了决心,我立刻答应下来。
毫无疑问,当大家一窝蜂扎进水池时,空间立刻变得拥挤,在碧蓝水波中忽上忽下全是白晃晃的鲜嫩肉体。几块遮住重要位置的布,显得非常有必要,必要地将肉体的性感逼出来。
这样的场合,人人都不由自主地兴奋起来。在游泳池里扑腾着,欢快如同第一次游水的小孩子。
只是游泳毕竟是单一的行动,所以有人建议打水球。所有可以玩的东西,在珍妮花的储藏室里都能找到。
男人们帮忙,从中间拉了张网,无需太严格地,男女们自发分成两队,就开始比赛了。
这是不错的活动,全面展示男士们强有力的胸大肌和充盈的臂力,也让女士们的胸部剧烈起伏。另有她们的尖叫声,夹杂着男士爽朗的哈哈大笑声。
我有点佩服韩森,明知道这个聚会不过是为了推荐他公司的产品,但自至而终,连一张图片都没看到,言词中更是只字不提。口中说出来的,全是一些风花雪月的事。
我已经预料到,这帮女人将会成为他公司产品的忠实拥趸,在各种聚会上,化身一个个的大喇叭,卖力地替他宣传。
大家轮番打水球,累了就上岸。吃点东西,喝点酒水,在椅子上躺会,充当啦啦队。
我只不过在水里游了几个来回,就跑到岸边吃东西去了。这样的活动,我兴趣真不大。
今天之所以来,主要还是对韩森有兴趣。不过兴趣不在于将他弄上床,而是想象怎样创造机会,成为他们的合作伙伴,虽然知道成功的希望非常渺茫。
各种吃食、点心和酒水就摆在游泳池旁边的白色长桌子上,是韩森预定的金钱豹自助餐厅里送来的。点心味道不错,饮料也很丰富。
韩森还特意安排了一个烤架,离游泳池较远,紧挨着围墙,烟雾很快便消散了,不会呛着玩乐的大家。
珍妮花的漂亮保姆淌着汗,烤着肉排。一边斜眼瞅着肆意狂欢的一群人,可能在心里诅咒命运的不公平。
我一边冷眼旁观,一边捡着爱吃的,大快朵颐。韩森脸上始终挂着温和的笑容,跟每位女士攀谈着,除了我与珍妮花。相对来说,我与珍妮花跟他算是熟人,他不必费心思来亲近。
他长得斯文,举止谦恭有礼,谈吐不俗,具备了赢得异性喜欢的条件。何况,他说话又是那么善解人意。
我亲耳听到他对一位长得丰满的女士说:“你令我想起了玛丽莲.梦露……”
丰满女士自是心花怒放,笑得脸上都起了褶子。幸好梦露尸骨已腐,否则断然会自棺中跳出,掴韩森一耳光。
不过,千万不要以为韩森是虚伪的人,恰恰相反,他说这话时表情非常的诚恳。或许他就是那种人,眼球中所看到的东西,没有一样是坏的或是丑的,他总是能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发现事物动人之处。
韩森的魅力很快征服了在场的女士,她们娇滴滴地呼唤着他的名字,看着他的眼神中,有了几分撒娇的意思。
我很快发现了一个好笑的事儿,韩森要是在岸上跟某位女士稍微聊久一会儿,其他女士的眼光就会频频溜到他们身上,一种无言的抗议。直到他不得不再度跳入游泳池中,加入水球比赛,女士们这才罢休。
韩森显然很累,但脸上一直挂着笑容。女士们的焦点在韩森身上,其他男士们绝不会吃醋。他们心里非常清楚一点,这可不是在玩儿,而是在工作。
又有几个人来吃东西了,我不喜欢暴露在别人的视野内,且身着泳衣。于是披了一块浴巾,端着一杯柠檬水,爬上了露台。
露台朝西,极目望去,首先收入眼中的是显得格外娇小的香山,暮色中呈现出苍蓝色,犹如一幅水墨天青的画布。
再近一点,眼前、也就是紧挨着别墅的是凌海。凌海其实是个人工湖,据说是开发商最大的卖点。
但北京真的缺水,只有在夏天的时候,开发商才会启动循环的水系统,给湖里蓄满水。但水远达不到广告上的磅礴水平,永远不会有碧波荡漾的可能。
不过,有白色的水鸟时时翩然降落,它们在此休闲觅食。在寻觅食物的过程中,它们常常娴雅地在滩上踱着步,恍然不知,它们在这背景下,踱着踱着,踱成了一幅动人的画图。
我知道这种鸟可能是鹳的一种,体型优美,极其娇小。爱极它们在斜晖中起落,白色的羽毛笼着一层金色光晕。
鉴于我无良的酒品,医学术语就是酒精过敏,一点酒精就会让我失去理智。前半生唯一的一次放纵,后果就是我失去了秦尉。
此刻,我对着鸟儿遥遥举杯,然后自己喝了一大口柠檬水。
隔着珍妮花别墅十来米的下面一排的别墅,很少有人住,据说是某位香港三级片明星的,以波霸而出名。
珍妮花不能免俗,曾好奇地用望远镜偷窥了一下。看见过之后,她同我说:“也不过如此。”说着挺了挺她的胸。
珍妮花个头高挑,胸部规模也不小,她曾得意地说:“男人是掌握不了它的。”
那就是一手难以掌握了,这恐怕得益于她过早且过频的性生活吧。十六岁之前,她还担心自己会同她的妈妈一样,一辈子都是一马平川。
暮色徐徐下降,一楼游泳池的欢笑声浮了上来。我探头张望了一下,游泳池波光盈动,男人们女人们带着薄薄的醺意,非常晦涩,说不清楚是什么感觉。
或者是一些暧昧的东西在空气中流动,也可以说****将要滋生,但还没有滋生。
珍妮花说过,十九世纪的英国上流社会,常常在城堡里举行的聚会。通宵达旦地跳舞玩乐,JQ是其中的一个主题。
主人会一早安排好房间,每个镀着泊金边框的门上都有一小孔,插放卡片——上面写着人名,这样子大家就不会走错房间。
在中国被戴绿帽子,那是污蔑祖宗的大不孝。奸夫和丈夫见面时,犹如上了战场,恨不得一方不死不休。
但英国上流社会的情夫和丈夫见面,彬彬有理地打招呼,拍打着肩膀开着玩笑,甚至一起共进早餐。
不过JQ仅在贵族圈里进行,各人心照不宣,绝对三缄其口。所以在其他人看来,他们一个个是绅士淑女,衣香鬓影,却料不到满肚子的男盗女娼。
其实后来大城市高级白领之间的****行为,应该是源于古老的欧美资本主义的流毒。我曾开玩笑地问珍妮花,是否也曾计划过开这么一个性质的party。她大笑,说不想被唾沫淹死。
依我来看,今天这种性质的聚会,是非常容易滋生奸情之类的媒介。
但这并不关我的事,我居高临下地看了他们一会儿,知道自己永远融不入这一圈子。
韩森之所以邀请我,估计是因为我和他深夜在沙滩上,聊过北京的热情。然后一起被请进了局子里,估计从没有将我与他的事业联系起来。
我走到摇椅边坐下,借着逐渐昏黄的暮色,看着手中的酒杯。浅绿色的水里,漂浮着一片柠檬,晶莹剔透的冰块散发着清冷的光芒。
我晃动着杯子,冰块相撞,发出清脆的声音,和凉风呼应,感觉到天簌正将我包围。
我靠在椅子里,眯起眼睛,凝视着天边那抹金黄。风起云涌,它变淡了,天空渐渐地转为铁青色。
或者我怔忡失神,或者我是睡着了。
一只手带我回到了有知觉的状态,非常温暖的手,按在我的肩膀上。我半扬起脸,看到了韩森平静的脸,他看起来很累,但脸上浅笑如初。
我环顾着四周,路灯全亮了,笼罩着一圈微弱的淡黄色光晕。苍翠绿植中零星地亮了几灯,那是住家的灯。这里的人家占地虽然大,但住的人并不多。
“散了?”我感觉到几分秋天的凉意,拉紧了浴巾,抬头问韩森。
“是的。”他绕过我在我身边坐下。这是一个三人位长摇椅,但他紧挨着我坐着,手也自然地搭在我身后的椅背上。
我觉得他的动作有些许过度的亲昵,胳膊上感受到他身上传来的温热,但是并不讨嫌。
我对他有一定的好感,他那么斯文,而且举止高雅。在他身上,飘浮着秦尉的影子。
他们是同一类型的人,永远是淡定自如。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下,他们充满自信。恰到好处的自信,绝不畏缩,也绝不张扬。
“夭夭,我想跟你谈谈。”
我略为惊讶地偏头看他,他正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微弱的光线令他浅棕色的瞳孔颜色加深了。
到目前为止,我想象不出,我与他之间会有什么共同话题。难道是关于他公司产品的网络媒体广告?我来了兴致,微微转过身子,正视着他。
韩森凝视着我说:“我今年38岁,有两个孩子。男孩六岁,女孩三岁,全在英国。我的太太,要照顾他们,所以没法到中国来。”
我微微皱起了眉,一头雾水,不知道他要告诉我什么。
提到家庭,韩森的眼睛里透出一股温和的光芒。那是幸福的男人才有的光辉,显然他是非常爱他的家人的。
“我是个男人,直接地说吧。”他耸耸肩,笑着说:“我离不开女人。”
我已大致明白他要说什么了,一种怒气开始在胸中凝聚。我的手下意识开始握拳,咬着牙没吭声。
“我需要找一个情人。”
我哑然失笑,偏转头遥望远处霓虹灯将天宇染成妖媚的桃红色。我知道韩森在等我的回答,但我不想开口。怕一开口,就忍不住大笑了。
一个对我怀着这种龌蹉心思的男人,我竟然还对他产生了微妙的好感,甚至幻想着能成为他的合作伙伴。对着自己的幼稚和自以为是,我真的想放声大笑。
韩森的耐心很好,他也不吱声,等着我。平定了自己的气息,我忍不住回转头看他。他靠在椅背上,饶有兴致地看着我,眼神非常柔和,而且分明潜含着某种念头。
我在心中哂笑一声,早不是不谙世事的小女孩,当然知道他可能在想什么。
我想韩森肯定看见我脸红了,因为他笑了,无声无息地笑了,露出洁白的牙齿。他一定认为我是害羞了,却不知道这是我生气的前兆。
虽然依旧凉风徐徐,我觉得空气变得闷热。沉默在此时似乎变成一种化学催化剂,将气氛变得暧昧。
我就那样直勾勾地瞪着他,说:“非常荣幸,你看中了我。”
韩森也不是什么善男信女,哈哈大笑起来,说:“夭夭,为什么拒绝我?”
我有些嘲讽的问:“难道我表现得如此轻浮,让你认定我缺乏这样一个机会?”
他脸色有点难看,但依然很有风度,“恰恰相反,你的表现无懈可击,让我非常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