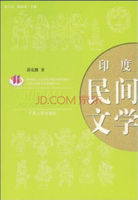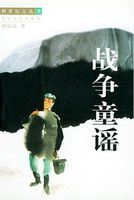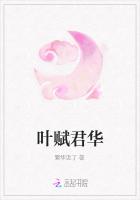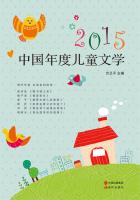对于马原来说,写作就是虚构故事,而不是复制或建立历史神话。传统写实主义把故事当做历史的真实记录,通过赋予故事以自明的历史起源性,故事的发生、发展在阅读经验中被设想为是历史本身,于是,意识形态设计的想象关系或幻想之物成为现实本身,而“现实”--实在之物则消逝于幻想之物和象征之物的“真实性”中。现在,马原的写作明确声称是在虚构,虚构确定叙述的起点,它在告诉你,这是在用幻想替代现实,不是等同于现实。“替代”与“等同”的意义并不一样,“等同”表明“现实”--为意识形态设想的现实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阅读文学作品不过是获取意识形态幻想的预期满足或预期驯化;而“替代”本身是对“现实”的挑战,其前提在于“现实”是必须被“替代”的,也是可以替代的,用一种个人化的反常规的幻想之物,替代。(解构)普遍化的、秩序化的想象关系(当代神话)。
马原的“叙述圈套”拆解了“历史化叙事”,同时改写了历史叙事中的“英雄人物”他的人物被改变成一个角色,一个在虚构空间和似是而非的现实中随意出入的角色,人物、叙述人和现实中的作品,被混为一谈。马原一开始就把叙述人搞得鬼鬼祟祟,他时而叙述,时而被叙述,它在文本中的位置(命名)始终暖昧不清,他类似一副面具、一帧肖像、一道障碍。“英雄人物”的意义被压缩了,‘、“人物”的功能被加大了。因此,对于马原来说;人物的死亡就不再具有悲剧性的意义,他们类似失踪的消失不过是叙事功能转换的一个变数。
洪峰一直被当做马原的第一个也是最成功的追随者,但是人们忽略了洪峰的特殊意义。1986年,洪峰发表《奔丧》,传统小说中的悲剧性事件在这里被洪峰加以反讽性的运用。“父亲”的悲剧性意义的丧失和他的权威性的恐惧力量的解除,意识着对历史化叙事的恶作剧般的疏理。值得注意的是同时期的残雪。1986年,残雪连续发表几篇作品:《苍老的浮云》、《黄泥街》、《山上的小屋》等。残雪显然过分夸大了日常生活里那些精神乖戾的现象,但是她也确实暴露了女性在潜意识里企图用她们怪异的精神反应来对付已经制度化了的男权统治。残雪的写作突然间抛离了以男性权力为中心的历史秩序。她的主题值得推敲,但是她的那种冷峻怪异的感觉,那种对妇女心理的淋漓尽致的刻画,对暴力的幻觉式的处理方式;以及有意混淆幻想和实在的界线的叙事方法,显然严重影响了后来的“先锋派”。
总之,残雪打开了一扇隐秘的窗户,预示了一个没有历史本质的幻想世界在文学中的存在,从总体上看,马原、洪峰、残雪既是一个转折,也是一个过渡,在他们之后,文学的历史观念和叙事方法发生深刻的变异。马原的意义是重大的:过去“写什么”可以从已经完整的历史化叙事中找到与意识形态直接对话的重大题材,写作只有主题的类别之分;而“怎么写”明显地见出才情技法的高下之别,写作不仅要发掘个人化经验的非常特独的角落,而且要去寻找动机、视角、句法、语感、风格等等多元综合的纯文学性的要素。只有独特的话语、技高一筹的叙述,才能在失去意识形态热点的纯文学的艺术水准上得到认可。在这一意义上,马原既是一个怂恿,一个诱惑,也是一个障碍。马原的出现表明,当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动力,不再来自为宏大的历史化叙事增加延续的动力,而在于开拓文学本体的广度、深度和难度。
当然,直到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北村和潘军等人的出现,先锋派形成一个群体的效应,那种文本实验的倾向才构成一种持续的力量。这股力量明显与长期占主流地位的历史叙事有别,小说的艺术方法活动具有首要的意义。
1987年底,苏童发表《1934年的逃亡》,苏童的小说给人以明晰纯净、凝练而又舒畅的感觉。这篇小说多少可以看出一点莫言“寻根”的味道和马原的那点诡秘,然而,以“祖父”“祖母”为表征的历史却陷入灾难,历史已无根可寻,留在虚假的时间容器(1934年)中的,不过是颓败的历史残骸。显然,这篇小说没有可以全部归纳的故事和主题,通篇是叙述人关于“祖父”“祖母”在灾荒的1934年的苦难经历的追忆。然而,我们可以看到前现代的乡土中国,在激进的现代性革命中所发生分裂。很显然,在苏童看来,乡土中国的历史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危机,它无法在传统的宗法制家族伦理秩序中生存下去。但是现代性的革命历史却同样是以灾难性的宿命论叙述加以反思的。这些复杂的思想主题,都若隐若现地在文本修辞中呈现,并且被无所顾忌的诗性化的表意策略所淹没。那些在叙事中突然横斜旁逸的描写性组织,构成叙事的真正闪光的链环。
不管从哪方面来说,《罂粟之家》真正显示了苏童的风格和他过人的小说技巧。
不管苏童有意还是无意,这篇小说实际上是对革命历史经典叙事的一次重写。在《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红旗谱》等革命历史小说的序列中,《罂粟之家》显得似是而非。这些小说都是对某一段历史变革的书写,但书写的方式和给予的意义却大相径庭。在《罂》的叙事中,阶级与血缘建立的冲突模式,通过双重颠倒来完成。陈茂这个乡村无产者的革命性被阶级本质决定了,但苏童显然是有意在重写阶级本质这一关键性的主题。在乡土中国进入现代性革命的进程中,强行的阶级斗争打破了传统中国宗法制社会的秩序,结果并没有培育出一个先进的革命阶级。无法调和的阶级矛盾,使传统的家庭伦理必然在错位的阶级冲突中崩溃,沉草最终打死了陈茂,他拒绝承认与陈茂存在血缘关系。并不是说他要维护传统宗法制社会的秩序,但也许更重要的是,沉草这个在城里受过西式教育的现代人,他所怀有的现代性梦想与乡土中国发生的现代性革命发生巨大冲突,他的悲剧性命运正是现代性在中国发生歧义的后果。
在苏童的观念里,到底是血缘关系、阶级关系还是人伦关系起决定作用?暖昧的血缘关系丝毫没有动摇明确的正义的人伦关系。就这一意义而言,苏童试图超脱经典的革命叙事模式。沉草这个“现代中国人”内心的价值选择是清晰的,家庭、伦理、正义、善与美等等,现代性范畴,并没有被中国式的现代性革命所颠覆,沉草不过是中国现代性断裂的殉难者而已。爱欲与革命以怪异的形式混淆,它们共同意指乡土中国在现代性转型中的历史境遇。很显然,在苏童的叙事中,爱欲是其叙事的主要主题,而革命则是叙事转折的因素。革命导致命运的突变,导致人物关系的重新结构处理,对于苏童的叙述来说,它们如同河流的偶然转向一样自然。把命运的突变,把叙事中的那些具有强大变异功能的因素,如此轻松自如地处理,散发淡淡的历史忧郁之情而远离悲剧,故事明白晓畅却不失深邃诡秘之气,这就是苏童作为一个出色小说家的非同凡响之处。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说,《罂粟之家》不是一部典型的现代性传奇(也许是反现代性的传奇),而只是乡土中国走到它历史末路显现的困境--苏童小说的独到之处正在于此--这是他反复书写的主题,在这样的困境中,他以清峻优雅的笔调抒写着乡土中国在现代性绝境中的挽歌。
对于苏童这一代作家来说,对于个人风格的迫寻远甚于对时代精神或意识形态热点的关切。苏童以及同时期的先锋派作家并没有明确反抗意识形态权威的愿望,对文学文本的关注,对叙事方法以及语言修辞的精心营造,这一切都依赖某种怀旧情调作为背景。经典叙事所包含的那种历史发展观,那种革命的乐观主义情绪,显然构成苏童小说叙事的另一面参照系。在八十年代末的特殊历史时期,苏童发表的《妻妾成群》(《收获》1989年第6期)这部小说,它看上去像是对某种思想氛围的屈服。事实上,这不过是苏童在个人化风格的道路上持续行走的结果。当然,这篇看上去古典味十足的小说,也显示了非常现代的叙事方法;它强调语言感觉和叙事句法,显示了苏童特有的那种叙事韵味。
但这篇小说可以放在一种反现代性的语境中来读解。这篇小说讲述一个女性遭遇婚姻悲剧的故事。与五四时期大多数“新青年”相反,颂莲这个女性却走进一个旧家庭,她几乎是自觉成为旧式婚姻的牺牲品,她的干练坚决成为她走向绝望之路的原动力。这篇小说与关于中国现代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典叙事大相径庭,它完全回避了经典叙事刻画的历史,它在恢复还原历史记忆的同时,也建构了另一种历史情境,它与中国现代性历史背道而驰。在苏童看来,传统中国的危机在于生命主体陷入困境,也就是以生殖为中心的宗法伦理发生了问题,不管是纵欲却丧失性能力的父一代(陈佐千),还是恋母和同性恋癖的子一代。这样的宗法制社会除了提示一个审美的忧郁感伤的情境,还有什么更好的命运可言呢?苏童显然不是在重复讲述封建悲剧的故事,对于苏童来说,“故事”并不特别重要,主题甚至也无须深究。这个并不新颖别致的故事,却能给人以特别深刻的印象,就在于苏童富有韵味的叙事,那纯净透明的语言感觉;那些刻画得异常鲜明的故事情境;那种温馨而感伤的气息……显然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到《家》、《春》、《秋》的痕迹,甚至可以上溯到《红楼梦》、《金瓶梅》那种古典小说的传统。
这种文化记忆的重复书写,也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审美反动。
余华在八十年代末的小说以描写幻觉和暴力而令人惊异。人是如何在幻觉的情境中,怀疑存在的真实性,从而表现超现代主义的心理反应,这使余华的小说一直处在描写入的生存状况的影子的状态。因而,余华的人物轻易地走向暴力,在生存的绝境中体验生命崩溃的快乐。余华的人物没有历史,没有记忆,当然也没有历史的理性和逻辑。余华把那些奇形怪状人物的全部智力压制在正常人的水平线之下,这样余华就可以驱使他们去干任何不可思议的勾当。显然,余华对人物的行动并不感兴趣,他关注的是那些过分的反应方式给叙述语言提示的可能性。《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显然有不少令人瞠目结舌的场面,然而,更加令人注目的是对那些场面的感觉方式和语言特征。
随后的《世事如烟》、(《收获》1988年第5期)、《难逃劫数》(同前第6期),无疑是余华最好的作品。《世事如烟》对暴力、阴谋、罪孽、变态等等的描写淋漓尽致。在余华的那个怪异的世界里,时间与空间、实在与幻觉、善与恶等等的界线理所当然被拆除,而阴谋、暴力和死亡则是日常生活必要的而又非常自然的内容。“算命先生”作为全部阴谋和罪恶之源,如同远古时代令人恐惧的部落长老。这帧历史的古老肖像总是在余华的写作中浮现出来。余华的那些怪诞不经的故事因此又具有某种发人深省的历史宿命论的意味。《难逃劫数》把暴力场面写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它们看上去像是一些精致的画面。余华的那些被剔除了智力装置的人物,总是处于过分敏感与过分麻木的两极,而且总是发生错位,他们不过注定了是些倒霉的角色,一系列的错误构成了他们的必然命运。人们生活在危险中而全然不知,这使余华感到震惊,而这也正是余华令人震惊之处。
八十年代末期,苏童、余华、格非、北村、孙甘露、潘军等人的小说叙事,与经典现实主义的审美原则相去甚远,这代作家不再追寻意识形态热点,他们直接面对艺术创新的压力,而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经验则是他们探索的路标。当然,并不是说他们的小说叙事就与历史无关,就与现代性以来的历史化规划无关,而是说中国文学从末像这样关注语言表现的本体,关注文学叙事的方法论活动。历史、寓言以及对现代性的反思和对现实的隐喻,这一切都不过是文本策略的副产品。他们的文本探索不只阻断了强大的历史化传统,同时也以他们的语言修辞策略和方法论活动,颠覆了庞大完整的历史叙事。
虚构的缩减:反历史化的修辞策略
当历史化演变为文学叙事的经典模式时,它必然要对表现对象进行本质化处理。例如,经典现实主义叙事最重要的美学命题,就是如何把握历史的本质规律。
本质主义写作依赖意识形态强势话语展开,而主导意识形态发生变更,对历史和现实的本质性规定也必然发生变更;同样,当意识形态强势话语开始富有弹性时,本质规律的规定也趋于含混。在八九十年代之交,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实践实际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潜在的多元化情境使真实的历史面目变得模糊,当然也使历史本质变得难以把握。尽管表象系统依然非常发达,但它与历史/现实的实践发生脱节,“本质”从历史表象中滑落,这就使表达变成纯粹的表达,变成符号指涉自身的运动。先锋派的形式主义策略回避了既定的意识形态,没有人可以准确把握符号后面的“本质规律”,所有的思想意识更像是表意策略的副产品。九十年代的文学叙事似乎更接近传统现实主义,故事与人物的复活,美学规范似乎又回到历史之中,但纵观九十年代的文学叙事,找不到总体性的意识形态轴心实践,也无法确认真实的历史本质,更多的是一种表象式的概括,一种单纯的文学话语,一种指向文学自身,或是与现实表象处于同一平面的符号秩序。因此,非本质主义的写作是历史化解魅(disenchant)的根本手法,它使整体性的历史无法找到中心意义建立有序的思想/审美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