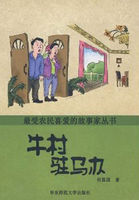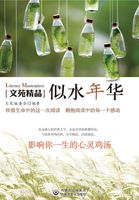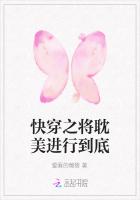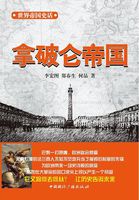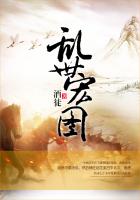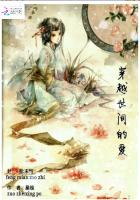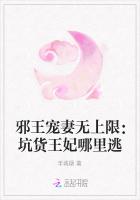二十世纪社会政治背景下的革命文学,无论相对于源远流长的古典文学,还是现代白话文兴起后的其他文学,都显得极不成熟,尽管它的生成与发展有历史的必然性。建国后,革命文学方兴未艾,文学界曾反复讨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正说明人们热心于革命文学的同时,对革命与文学的现实关系也存在诸多歧义。其中特别令人反感的是在革命文学内部,存在着一些貌似革命、或打着革命旗号而不可一世的写作教条,严重地干扰和限制了文学的发展。于是在当代文坛,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的声音始终不绝如缕。
但到了六十年代,特别是“文革”前夕,关于革命文学,无论如何是讨论不下去了。从表面看,为扭转1959年到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出现的经济困境,六十年代初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鉴于这种经济上的调整,文学界也有相对宽松的迹象。但这一切毕竟是权宜性的。只要看一看1960年文学界开始的反修斗争,以及拉开这场斗争序幕的对李何林的一个“小问题”的批判;1963年底和1964年关于“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文艺界“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的两个批示;还有1964年《文艺报》发表的《十五年来资产阶级是怎样反对创造工农兵英雄人物的?》,1965年《文汇报》率先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等文章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在重重压力下,文学已经像到了一条十分狭窄的胡同里,稍有新意而不拘格套,就有碰壁、挨批的危险。
然而,走进这段历史所看到的,又不仅仅是当时严峻的政治形势:1月22日《人民日报》转载了《文艺报》同年第一期社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为争取文艺的更大丰收而奋斗!》,提出在文艺领域进行“反修”斗争的理论主张,正式拉开了文艺界反修斗争的战幕。也可以发现,当时的文学界虽已是山雨欲来,但一些作家和理论家的确“不识时务”,仍然对革命文学中长期流行的标语口号倾向提出大胆质疑。在政治上,他们的表现也许几近天真,全不顾自己后来会遭受怎样的厄运,但也惟其如此,在“十七年文学”史上,他们却留下了不惟世故和权势,一心探求真理的足迹。
1960年1月8日,《河北日报》发表了李何林的文章《十年文艺理论批评上的一个小问题》,这篇文章可视为六十年代关于艺术真实性探索的一种声音。文章对自四十年代开始流行的政治标准(或思想性和思想标准)和艺术标准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说,建国后的文学理论和批评都以为“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相一致的作品,也有不相一致的作品”,这种看法其实是不对的。他认为,“没有思想性和艺术性不相一致的作品”。“思想性和艺术性是一致的,思想性的高低决定于作品‘反映生活的真实与否’;而‘反映生活真实与否’也就是它的艺术性的高低”。如果片面地强调作品的政治思想性,“概念化地表现一些正确的政治观点”,其结果是使作品既无艺术性,“对读者的教育作用和说服力也不强,也就是思想性不高”。作为现代文学史家,李何林以历史上左翼作家为例:
例如蒋光慈的小说,乍看起来似乎它的艺术性比较低,思想性比较高:它的叙述语言里面表现了作者的进步的政治态度和一些进步的政治观点或政治概念;又每每通过人物的口说出了一些进步的政治思想或表达了一些进步的政治概念。但是它的形象和典型大多数都是没有个性的类型,不是有血有肉的,概念化的倾向是相当严重的,因而反映生活的深度和真实性都不够,对读者的教育作用和说服力量也不强,也就是思想性不高。只是概念化地表现一些正确的政治观点,并不等于思想性就高……它的艺术力量和它的思想性不高是相一致的。它的艺术性方面的“粗糙”和它的思想性方面的“粗糙”是相一致的。
这篇文章强调,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应该统一表现于“反映生活的深刻和真实性”“思想性的高低决定于作品‘反映生活的真实与否’;而‘反映生活的真实与否’也就是它的艺术性的高低”。这一点正如鲁迅当年对革命文学所言:革命文学不应仅仅是挂“招牌”,却不敢正视现实;而应该“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真,自然是不容易的……但总可以说些较真的话,发些较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提倡艺术真实性在当时直接触及到的问题,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只能称颂“三面红旗”、而不敢揭示“大跃进”和公社化造成的严重恶果的政治氛围和创作倾向;触及到革命文学领域长期流行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二元等级化问题。
因此,李何林的文章提出的“小问题”,在当时掀起轩然大波,作为修正主义的标本受到有组织的严厉批判。批判者认为李何林的“公式,本质上是‘艺术即政治’的修正主义公式,表面上是左的,实际上是右得很”,这就把作者所强调的艺术真实性对创作的意义纳入反修斗争的政治范畴,使文学的真实性,以及由真实性所涉及的艺术性问题愈加成为禁区。
六十年代小说艺术的探索就在这种环境艰难而顽强地展开,特别是对艺术真实性的批判,并没挡住小说家探索的脚步。就在此后一两年,一批通过描写历史题材向现实发问的小说接二连三地发表了,并以创作实绩响应着理论家关于小说应该“反映生活的深度和真实性”的呼唤。陈翔鹤相继发表的短篇小说《陶渊明写(挽歌)》(1961年)和《广陵散》(1962年),就是以历史题材回应现实的一种艺术探索。《陶渊明写挽歌》描写东晋诗人陶渊明去世前的一段生活。宋文帝元嘉四年的秋天,年近六十二岁的陶渊明来到庐山东林寺,本想静心养性,谁知那里正在大办法事,寺院的主持慧远法师高傲、冷漠而又装腔作势,还以“‘三界不安犹如火宅’,生啦死啦的大道理来吓唬人”,他对匍匐在地上的会众“连正眼都不曾看一眼”,“而这种‘我慢’之概的印象”,又正是慧远本人对陶渊明时常提起,认为是违反佛理的。这件事深深触动了陶渊明,于是他写下了三首《挽歌》和一篇《自祭文》。魏晋时代是历史上王纲解纽、战乱不断的年代。一些士人有感于官场黑暗,“时局动荡,好多人觉得过去苦心孤诣学来的规矩方圆,到时全无用场”,因而归隐乡间,寄情于山林。陶渊明四十一岁任彭泽县令,因不满官场恶习,在官八十余日即弃官归隐。小说基于史实,却从细节描写人手,深入人物内心,着重展示诗人不肯同流合污的性格。比如作品描写刘遗民和周续之在东林寺劝陶渊明加入白莲社:“‘浔阳三隐’中有两位都已经加入,渊明公再一加入,那便算是全数了!”陶渊明不想交恶于小人,于是敷衍他们说:“让我再想想看。人生本来就很短促,并且活着也多不容易啊!在我个人想,又何必用敲钟来增加它的麻烦呢?”其实,他心里对这些人和事是这样看的:
看来东林寺以后是不能再去啦,这些和尚真作孽,总是想拿敲钟敲鼓来吓唬人。最可笑的还有刘遗民、周续之那一般人,平时连朝廷的征辟也都不应,可是一见了慧远和尚就那样的磕头礼拜,五体投地!是不是这可以说明,他们对于生死道理还有所未达呢?死,死了便了,一死百了,又算得个甚么!哪值得那样敲钟敲鼓地大惊小怪!佛家说超脱,道家说羽化,其实这些都是自己仍旧有解脱不了的东西。
“未知生,焉知死”。对生的执著和对死的困惑,自古以来就是哲人们悉心探究的问题。作品通过描写陶渊明的东林寺之行,表达了陶渊明对这个问题的总体看法:生与死不可抗拒,这是世人皆知的自然法则,但有人一定要在生死问题上大做文章,实际是对“生死道理还有所未达”。刘遗民等人拜倒在慧远脚下,甘愿做白莲社的附庸,他们的种种表演,不过是当时社会人际关系的缩影:东晋时代的黑暗统治就像一只巨大的章鱼,把专横而残暴的触角伸向社会不同领域和阶层,于是阳奉阴违,弄虚作假,逢迎拍马,比比皆是。慧远不过是以“出家人”身份作障眼法,讳饰自己效仿朝政、愚弄众生的功利心而已。小说揭示陶渊明名为“田园诗人”,但“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不过又要做得“不至于招人注意”,所以既描写他在乱世求生,出于无奈而产生的生命玄想:“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更传递出他对无望的现实决不妥协的心迹:“人生实难,死之如何!”生死既不足惜,功名利禄又怎么能动摇诗人高洁的志向和素朴的诗心呢?
这篇小说不像编故事,却也不是纯粹地写历史,这种写法在鲁迅的《故事新编》中已有先例。鲁迅说《故事新编》是“速写居多,不足称为《文学概论》之所谓小说。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说起来“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倒无需怎样的手段”,但毕竟“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因此,像《不周山》等作品里,都有作家把“博考文献”和讥刺现实“可怜的阴险”两者融合起来的努力。在这样的作品里,现实的诱因与历史掌故只一步之遥:现实引起小说家对历史的回想;而由他叙述的历史又倒映着对现实的感慨。
虽不能简单地说,《陶渊明写(挽歌)》中的一些描写就是对“大跃进”、“反右倾”运动中“共产风”和“浮夸风”的比附,但作品中,诗人对大法师专喜欢“装腔作势”,拿“大道理来吓唬人”的憎恶;对官场中“侍宴啦,陪乘啦,应诏赋诗,俗务萦心,患得患失”的不屑;对寒门素士在社会中遭冷遇的不平……在这样的描写中,也不能排除作者由于现实生活的刺激而转向对历史的诉求,通过描写历史来宣泄他对当时社会“上有好之,下必甚焉”的恶劣风气的不满,呼出被当时环境所压抑的郁闷之气。因此,作品虽然受到“攻击三面红旗”,“阴险地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的批判,但当时更多引起的还是作家和批评家的共鸣:“陈翔鹤同志的近作《陶渊明写(挽歌)》,真可以算得是‘空谷足音’,令人闻之而喜。”“如果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还有慧远和尚、檀道济和颜延之之流的人物,那么,像陶渊明这样的耿介之士,恐怕还不能算是‘多余的人’罢。”短篇小说《广陵散》也也把关注点投向传统的士人精神。小说描写魏晋之交,嵇康和吕安在最高统治阶层司马氏和曹氏的争斗中无辜被杀的经过。作者在作品“附记”中说:“这篇故事是想通过嵇康、吕安的无辜被杀,来反映一下在魏晋易代之际,由于封建统治阶级争夺王位和政权,一些具有反抗性、正义感的艺术家们,曾经遇见过怎样的一种惨痛不幸遭遇。”历史上的嵇康出身微寒,与曹魏皇室既是姻亲,又是乡里,这样的社会地位使他与当时执政的司马氏集团处于对立的方面。
当时司马氏利用礼教,试图以“禅让”的形式夺取皇权,而嵇康却和阮籍提出“自然”来和司马氏的“名教”相对抗,不仅在《幽愤诗》中表述了“采薇山阿,散发岩岫”,不与司马氏合作的心迹,而且公开说自己“非汤武而薄周礼”,“把司马氏积极准备着以‘禅让’形式夺取皇权的根据给推翻了,所以嵇康就非死不可”。
嵇康的文学成就,他那些为人称道的思想新颖、风格清峻的散文和诗歌,都与他的经历,特别与他愤世嫉俗和刚直不阿的性格紧密联系着。
小说重点不在于歌颂嵇康的文学业绩,而是揭示在历史上特别黑暗的年代,一个富于理想和正义感的文人的精神气概。与传统戏剧或文学作品中那些手无缚鸡之力、耽于空谈的文人形象不同,小说中嵇康是高大有力的,他不像文人,却像从事体力劳动的铁匠或农夫。作品开篇描写嵇康爱好打铁:
时间虽然已到初冬,但洛阳的天气却并不怎么寒冷,柳树叶也还没有脱叶,因此嵇康此刻只露髻、短褐、乌裤褶、赤脚草履,正挥动着大锤,在被阿凤用长铁钳子紧紧夹着的一块红铁上,一锤一锤地直打下去。大约有一个多时辰之后,大家都静默无声,严肃而且兴味盎然。这其间,只偶然可以听见从嵇康口中发出来的“嗬嗬”的声音。这就算是他在工作中的一种表情,而且也算是他对于铁和火花的一种礼赞!在王朝转换、时人对司马氏推崇的礼教阳奉阴违却又趋之若骛的年代,嵇康却我行我素,任情恣性地鄙薄俗流,在铁锤打造飞溅的火花中显示自我生命的力量。
嵇康后来被司马昭处以极刑,“死时刚四十岁”。小说描写嵇康死前在刑场上弹奏《广陵散》的情景尤为动人:他镇定自若,全身心都投入演奏,那“肃杀哀怨,悲痛惨切的情调”,竟使行刑的兵士们“拄立着戈矛,歪斜着身体,低垂着头,去聆听和欣赏悠扬缓急,变化多端的琴韵。仿佛这不是刑场,他们也不是来执行杀人的任务,却是专门为听琴而来似的”。选择这样的历史人物加以描绘、铺陈,表现出小说家对一种崇尚自然而又刚健有力的士人人格的推崇。
如同所有历史人物,嵇康的思想其实也很复杂。鲁迅对这个问题看得透彻:
“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他们真正反对的是在历史转折关头,口是心非,完全置伦理道德的常识于不顾的“识时务者”。“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做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这些历史小说对现实发难的武器也往往来自传统文人在精神上赖以安身立命的以儒学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例如黄秋耘的《杜子美还家》描写诗人杜甫从躲避安史之乱的凤翔起程回家的经历,由于他在凤翔触犯了肃宗皇帝,皇帝下令,他被迫离开凤翔。一路上他“想到自己从弱冠之年起就怀抱大志”,正所谓“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但“四十六年的岁月白白过去”,却未尽精忠报国之志,因此吟出了“晚岁迫偷生,还家少欢趣”的诗句。冯至的《白发生黑丝》描写杜甫去世前以船为家,亲眼目睹渔民悲苦的生活,由于经常和渔民来往,他的诗歌吸收了民间情趣,这竟使诗人的白发生出黑丝……小说对诗人经历的描写,以及心理剖白,也是对“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文人传统的生动写照。不过,这种文人传统当时并没解决诗人内心的矛盾,自然更解决不了社会的问题。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作家重提中国文人传统,以扭转世风,正如黄秋耘所言:如果在“现实生活中还有慧远和尚、檀道济和颜延之之流的人物,那么,像陶渊明这样的耿介之士,恐怕还不能算是‘多余的人”’,但这种探索在当时的形势下并不乐观。在“重提阶级斗争”的背景下,“文革”式的批判已经抬头,这种局面的确不是知识分子中的“耿介之士”所能抵挡的。尽管如此,作家和批评家对文人传统的眷顾也值得重视,他们为越来越狭隘和封闭的文坛带来了艺术探索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