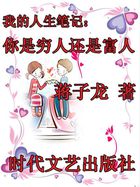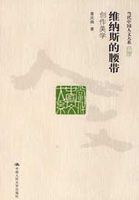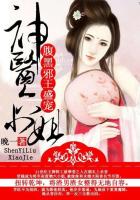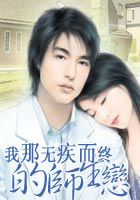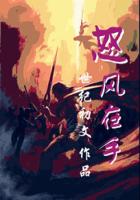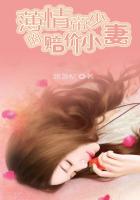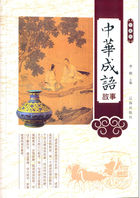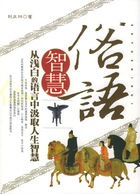李渔则比他的前辈们迈进了一大步,从戏剧艺术的结构特点立论,来阐明一部传奇作品的最末一出应该怎样写,故事的结尾应该怎样适应观众的欣赏需要,以收到积极的舞台效果。他所谓“无包括之痕”,就是要求传奇的结尾应该“自然而然,水到渠成,非由车戽。最忌无因而至,突如其来,与勉强生情,拉成一处。”也就是说,不要人为地硬去搞大团圆,而应该使结尾成为剧情发展的自然结果,人物性格的必然归宿。中国古典戏剧喜欢搞大团圆的结尾,但是往往落入固定的套子,俗不可耐。例如,写男情女爱,则常常是女为千金小姐,男为白面书生,必要书生上京考中状元,方能最后成亲。李渔自己的几部传奇,也都是故意搞个大团圆的结尾,《比目鱼》、《奈何天》、《巧团圆》等,都是如此,总令人感到忸怩作态,失却自然,正犯了他自己所批评的“包括之痕”的毛病。
李渔所谓“有团圆之趣”,是要求传奇的结尾应具有“到底不懈之笔,愈远愈大之才”,犹如“水穷山尽之处,偏宜突起波澜,或先惊而后喜,或始疑而终信,或喜极信极而又致惊疑,务使一折之中,七情俱备”。就是说,传奇的结尾,不应该成为强弩之末,像撤了气的皮球瘪下去,而是直到最后还要有“戏”,做到“收场一出,即勾魂摄魄之具,使人看过数日,而犹觉声音在耳,情形在目”,使人“执卷留连,若难遽别”。
但是,要做到“无包括之痕,有团圆之趣”,发生“勾魂摄魄”的艺术魅力,是颇不容易的事情。中国古典戏剧,特别是明清传奇的结尾,为什么常常出现李渔所反对的那种毛病呢?这原因不能光从个别作家的艺术技巧上去找,还应该从中国传奇的结构特点上去找。如前所述,结尾离高潮太远,高潮之后还往往敷衍一大段情节拖长故事,这必然使人有强弩之末、冗长拖沓之感,削弱了勾魂摄魄的艺术力量。要克服这个毛病,也应该从整个戏剧布局、结构的传统手法上去注意。
传奇在结构上的这种传统,一直影响到现在。例如电影《二泉映月》,写阿炳一生,不无感人之处;但影片在结构上却似乎沾染上了明清传奇作品常有的那种毛病,即高潮距结尾太远。影片写到阿炳在船上被毒打,琴妹投水自尽,已达高潮;但这之后又写了很长一段情节才到结尾。虽然高潮之后的情节并非毫无可取之处,却显然使观众在情绪上松懈了下来,减弱了强烈的吸引力量。如果这部影片在结构上再花一番工夫,艺术效果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从这里我们能否得到这样一种启发:对中国古典艺术以及传统美学理论,不能无分析无批判地吸收、继承。的确好的,拿来;有好、有坏的,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不好的,不必硬当国粹,而应丢掉。
李渔论戏剧语言
语言,被高尔基称为文学的第一要素;而对于戏剧来说,语言更有着一种特殊意义。戏剧的重要特点之一,用高尔基的话说,就是“每个剧中人物用自己的语言和行动来表现自己的特征”,“剧中人物之被创造出来,仅仅是依靠他们的台词”。对于一个戏剧作家来说,在诸多戏剧表现手段之中,除了结构,他最重视的大概莫过于语言了。如果说结构是戏剧的骨骼,那么语言(台词)则是它的肌肉,是展开故事、塑造人物的最基本的材料和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动作,外在的动作和内在的动作(即思想、心理的动作),对于戏剧当然是极为重要的,没有动作就没有戏剧。有的剧,例如哑剧,不用语言而单靠动作也能使观众看得懂,给人以美的享受;然而,缺少语言而只靠动作,毕竟使戏剧发挥自己的艺术力量受到很大限制。犹如一只雄鹰,翅膀上如果羽毛很少,甚至全无羽毛,它也难以翱翔于崇山峻岭之上。
戏剧语言既不同于小说、散文的语言,又不同于一般诗歌的语言。比之于前者,它更像诗,即使是用散文写成的剧,它的语言也应该是诗化的、充满着诗意的;比之于后者,它又更具有小说的描绘性、通俗性、口语化、个性化。它是兼有二者特点、而又与二者都不相同的第三种文学语言。中国的古典戏剧又有自己的特点,它既不同于一般的外国戏剧(从古希腊的悲剧和喜剧到现代的话剧),又不同于只有唱而没有白的外国歌剧,而是有着自己鲜明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特殊类型的歌剧。它的语言是以唱词为主,而又兼以宾白。它的唱词是具有戏剧特点的诗歌,被称为剧诗;它的宾白也是具有戏剧特点的散文,或者对子、四六骈语等等。
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正是总结了中国古典戏剧语言的这些特殊规律。
对于戏剧语言的各种问题,李渔之前的许多戏剧论着不但早有阐发,而且恐怕比其他问题谈论得更多,也更充分。特别是有不少戏剧理论家往往把戏剧作为案头文学来欣赏,就更着重于像论诗、论词那样来论曲(戏剧),因而对词采、音律的问题就更加重视,他们虽然有忽视舞台特点的倾向,但的确提出了许多精彩的见解。李渔认真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关于戏剧语言的一系列看法。并且他更重视戏剧本身的特点,因而所论也就更深透、切实。
李渔非常重视戏剧语言的通俗化、群众化。在论述“词采”的时候,他首先就提出“贵显浅”的主张,要求台词一定要通俗易懂,明白如话,而不可“艰深隐晦”。显然,李渔此论是发扬了明人关于曲的语言要“本色”的有关主张而来。然而,细细考察,李渔的“贵显浅”与明人的提倡“本色”,虽相近而又不完全相同。
明人主张“本色”,当然含有要求戏剧语言通俗明白的意思在内。例如,徐渭在《南词叙录》中赞扬南戏的许多作品语言“句句是本色语,无今人时文气”;而批评邵文明《香囊记》传奇“以时文为南曲”,生用典故和古书语句,“终非本色”。他明确提出“曲本取于感发人心,歌之使奴、童、妇、女皆喻,乃为得体”。这就是后来李渔论戏剧语言要“贵显浅”、“忌填塞”时所更加发挥了的意思。但是,所谓“本色”,还有另外的意思,那就是要求语言的质朴和描摹的恰当。王骥德在《曲律》中是把“本色”与“文词”、“藻绘”相对而言的,说:“曲之始,止本色一家,……自《香囊记》以儒门手脚为之,遂滥觞而有文词家一体。”还指出:“夫曲以模写物情,体贴人理,所取委曲宛转,以代说词,一涉藻绘,便蔽本来。”臧懋循在《(元曲选)序二》中,也要求“填词者必须人习其方言,事肖其本色,境无旁溢,语无外假”。总之,“本色”的主要含义就是要求质朴无华而又准确真切地描绘事物的本来面目。这个思想当然是好的,戏剧也应符合这个要求。
相比之下,李渔“贵显浅”的主张,发挥了明人“本色”的某些意思,而为了适应戏剧舞台表演的特点又更重视、更强调戏剧语言的通俗性、群众性,因而对戏剧来说也就更加切实。李渔是在比较了戏剧语言与诗文语言的不同特点之后而提出他的“贵显浅”的主张的。他说:“诗文之词采贵典雅而贱粗俗,宜蕴藉而忌分明”,而曲文之词采则要“判然相反”,“话则本之街谈巷议,事则取其直说明言”。为什么非如此不可呢?因为“传奇不比文章,文章做与读书人看,故不怪其深;戏文做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看,又与不读书之妇人小儿同看,故贵浅不贵深”。在谈到传奇的作用时,李渔也是强调传奇要“借优人说法与大众齐听”,包括与那些“认字知书少”的“愚夫愚妇”们“齐听”。因此。戏剧艺术的这种广泛的群众性,不能不要求它的语言的通俗化、群众化。那些深知戏剧特点的艺术家、美学家,大都是如此主张的。西班牙的维迦就强调戏剧语言要“明白了当,舒展自如”,要“采取人们的习惯说法,而不是高级社会那种雕琢华丽抑扬顿挫的词句。不要引经据典,搜求怪僻,故作艰深”。
同时,戏剧艺术的舞台性,还要求它的语言不能“只要纸上分明,不顾口中顺逆”,不能“观刻本极其透彻,奏之场上便觉糊涂”,不能“艰深隐晦”,佶屈聱牙;而应该“观听咸宜”,既“中听”,又“好说”,宾白要朗朗上口,唱词要明白晓畅,使观众一听就懂。李渔以汤显祖的《还魂记》为例,说明戏剧语言“艰深隐晦”对于舞台艺术是多么不可取。《还魂记》当然不失为优秀之作,这在文学史上是已有定评的;但是,它的某些语言,作为文人案头欣赏品味是好文字,而奏之场上,实在会令一般观众觉得“糊涂”。李渔指出:“《惊梦》首句云:‘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以游丝一缕,逗起情丝。发端一语即费如许深心,可谓惨淡经营矣。然听歌《牡丹亭》者,百人之中有一二人解出此意否?若谓制曲初心并不在此,不过因所见以起兴,则瞥见游丝,不妨直说,何须曲而又曲,由晴丝而说及春,由春与晴丝而悟其如线也?若云作此原有深心,则恐索解人不易得矣。索解人既不易得,又何必奏之歌筵,俾雅人俗子同闻而共见乎!其馀‘停半晌,整花钿,没揣菱花,偷人半面’及‘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遍青山啼红了杜鹃’等语,字字俱费经营,字字皆欠明爽。此等妙语,止可作文字观,不得作传奇观。”的确,如上述李渔所举出的《还魂记》中这种过于典雅艰深、曲折隐晦的语言,若在舞台上演唱出来,观众必定觉得茫然。
那么,李渔是否认为戏剧语言一味显浅就好呢?不然。李渔认为,如若“一味显浅而不知分别”,则又流于粗俗、浮泛,又走上了另一弊端,亦不可取。戏剧语言的显浅,其实是要“意深词浅”,是要在浅处见深。李渔所特别推崇的《西厢记》,它的许多语言自然是以“绮丽”着称;然而也有许多语言是以“意深词浅”见长。请看第二本第四折中,老夫人赖婚之后,莺莺埋怨老夫人时的一段唱:“佳人自来多命薄,秀才每(们),从来懦,闷杀没头鹅,撇下赔钱货;下场头那答儿发付我!”这段唱词中,大多为当时的口语、俗语所组成,既通俗晓畅,妇孺皆懂,而意思又很深刻,耐人寻味。特别是以“没头鹅”(把头掖在翅膀里的鹅)喻张生当时的窘境,以“赔钱货”(多么口语化!)喻自己此刻的状况,形象生动,寓意深长,充分表现出莺莺这个热烈渴求恋爱婚姻自由的少女的怨恨心情。这不就是李渔所说的以浅见深吗?
为了进一步申明自己的“意深词浅”的主张,李渔还将“今曲”与“元曲”作了对照,认为“今曲”的毛病在于“心口皆深”,不可取;而元曲的长处则是:“元人非不深心,而所填之词皆觉过于浅近,以其深而出之以浅,非借浅以文其不深也。”这里指出了戏剧语言的三种状况:一是“心口皆深”(这是“今曲”的语言);一是词浅意深(这是“元曲”的语言);一是词浅而意亦浅。李渔称赞的是词浅意深的语言。这是很对的。戏剧语言,不论是唱词还是宾白,都必须以浅见深,通俗易懂,晓朗如话。即不能借语词之浅文其内容之不深;也不能以心口皆深以示其高深莫测;更不能以文词之深掩盖其内容之贫乏,堆砌词藻,故弄玄虚,以吓三家村人。
李渔对戏剧作家提出了一个很高、然而在今天看来仍然很正确很中肯的要求:“能于浅处见才,方是文章高手”。
那么,如何才能于浅处见才呢?这就需要戏剧作家有很高的思想水平、审美功力和艺术技巧。不但要具有准确地把握所写对象特质的能力,而且又要有很深的语言修养的工夫,善于选择和使用形象生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对象的特点准确贴切、淋漓尽致、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关于戏剧作家如何进行语言修养,李渔着重从两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意见。
第一,李渔一再强调戏剧作家必须从现实生活的群众口语和俗语中汲取营养,提炼戏剧语言。在“贵显浅”一节中,李渔提出“话则本之街谈巷议”,在“忌填塞”一节中,他又重复地强调“其句则采街谈巷议”。这个见解放在今天也是相当精彩的。李渔之极力称赞元曲语言,就是因为元曲中的优秀作品,如《西厢记》等等,是将街谈巷议的群众口语、俗语进行提炼、加工,从而创造出自己通俗优美、词浅意深、脍炙人口的戏剧语言,充分体现了现实生活语言本身的鲜亮、活泼、生动并富有表现力的特点。李渔对《还魂记》中的语言,或褒或贬,均以元曲的语言精华作为准绳。其贬,已如前述;其褒,则是下面的一些词句:“看你春归何处归,春睡何曾睡,气丝儿,怎度的长天日?”“梦去知他实实谁?病来只送得个虚虚的你,做行云先渴倒在巫阳会。”“又不是困人天气,中酒心期,魆魆的常如醉。”“如愁欲语,只少口气儿呵!”“叫的你喷嚏似天花唾,动凌波,盈盈欲下,不见影儿那!”李渔称赞这些唱词说:“此等曲,则纯乎元人,置之《百种》前后,几不能辨;以其意深词浅,全无一毫书本气也。”请注意这“全无一毫书本气”几个字,这表明李渔正是要求戏剧作家主要应从现实生活的群众语言中而不是或主要不是从书本上去提炼戏剧语言。《还魂记》中的这些词句之所以好,就是因为它们来自当时群众的口语,因此就能够像当时群众日常说话那样生动、形象、质朴、通俗,如“不见影儿那”、“只少口气儿呵”等等语句,多么口语化!多么明白晓畅!
第二,李渔认为戏剧作家也应该多读书,重视从前人文章中、从古籍中汲取戏剧语言的营养,以增强其表现力,使之更加丰富多彩。他说:“若论填词家宜用之书,则无论经、传、子、史,以及诗、赋、古文,无一不当熟读,即道家、佛氏、九流、百工之书,下至孩童所习《千字文》、《百家姓》,无一不在所用之中。”然而,多读书绝非要戏剧作家掉书袋,生吞活剥地到处引用,弄得满纸“书本气”;而是要求戏剧作家“寝食其中”,“为其所化”,变为自己语言血肉之一部分。那么,提炼群众口头语言和吸取前人书本语言,这二者关系怎么摆呢?李渔明确指出,要以前者为主,以后者为辅。对前者,李渔的提法是“本之街谈巷议”;对后者,他的提法则是“即有时偶涉诗书,亦系耳根听熟之语,舌端调惯之文,虽出诗书,实与街谈巷议无别者”。他坚决反对“多引古事,叠用人名,直书成句”,致使传奇语言“满纸皆书”,造成填塞堆垛之病。李渔主张在读书之后,当“形之笔端,落于纸上,则宜洗濯殆尽”;即使偶用成语、旧事,“妙在信手拈来,无心巧合,竟似古人寻我,并非我觅古人”。也即如王骥德所说:“用在句中,令人不觉,如禅家所谓撮盐水中,饮水乃知咸味,方是妙手。”
李渔上述观点,直到今天也是有价值的,对提高我们的戏剧语言水平很有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