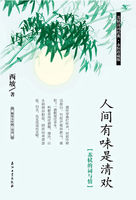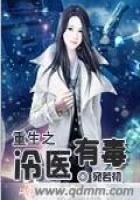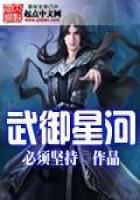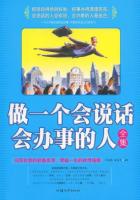那时候,母亲每天早上起床的第一次事就是给我们几个还在被窝里酣睡的孩子每人枕头边放一个她昨天晚上烙好的菜饼子,按年龄大小分配,年龄大的就分个大的,年龄小的就分一个小的,年龄更小的当然也就分的饼子更小了。我往往是眼睛还没睁开,就已伸手去摸枕边的菜饼子,赶紧撕上一口这才算完全醒了过来。本来是每人一个的饼子,其实母亲常常没有,她的一个留给父亲中午来吃,因为她觉得父亲是这个家的顶梁柱,也最辛苦,因此应该多吃一点,但毕竟没有多的,她就将自己的那份多给父亲了。母亲留的这个菜饼子,据我多次细心的侦察,一般存在几个地方,一是藏在挂在门背后的箩里,一是扣在锅台后面放碗的我们叫做“灶爷板”上的碗下面,有时候甚至于藏到锅膛里的灰上面。
母亲之所以这样想尽一切办法的目的是怕我们这些孩子发现后吃了,父亲中午没喝茶吃的馍馍。我发现母亲的藏“宝”处后,往往偷偷地观察过那个菜饼子,并用手亲切地多次抚摸,我惊喜的是,常常在那个菜饼子的周边总会掉下一星半点的馍馍渣渣,我便喜不自胜地用手拈来放在嘴里,再把菜饼子翻过来看,看下面再有没有意外的发现,但这样的发现并不多,实在对这个饼子爱慕得不行了,看它的边上有些不光滑,直至有翘起的菜叶子时,就用手去撕下那些“多余的”部分,有时不经意就把那个菜饼子的边沿撕掉一圈,但最终我还是不敢把个这个饼子完全吃掉,我怕没了这个饼子会挨母亲的一顿巴掌,也怕大人们会认我是个不孝顺的坏孩子,那时我就是一个爱名声的人,我觉得一个好孩子的名声比饿肚子的事更加重要,但我的大哥他比我现实得多,他只要能找到母亲放菜饼子的地方,就先是自己掰上一半几口吃掉,心想着把剩下的一半留给父亲,但后来他觉得还是应该把剩下的那半个也吃了,因为既然已吃了一半,反正母亲的一顿骂是少不了,那就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了。
其实,苜蓿能掐着吃的时间最多也就半个多月,因为再长一点,就没掐的了,苜蓿已长老了,老得人嚼不动了。这期间各家的口粮补助就只能靠苦苦菜之类的野菜了。但等到五六月时,苜蓿又能吃了,那就是捋苜蓿花吃,那一咕嘟一咕嘟的紫色的花朵,一抓就是一大把,捋回来洗净了,和嫩苜蓿一样好吃。只是苜蓿花捋光了,秋天的苜蓿上就很少有籽实的收获了。可见苜蓿对人类的贡献之大,它不仅养活着给人类拉长工的牲口们,也在关键的时候养活着人。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一件偷掐苜蓿的事来,记得有一次晚上月亮很亮,亮得人心里空空的,母亲睡了一阵就悄悄爬起来,挎了篮子去了苜蓿地里,她是想偷偷地掐点苜蓿来,让明天早上一家人的菜饼子大一点,但据母亲后来告诉我,当她刚掐了半篮子苜蓿时,队里看夜的人发现了她,那时的苜蓿也是晚上有人看的,看夜的人吆喝着追她,她只能拼命地奔跑,当她跑着拐过一个弯看到一个塌窑洞时,急忙钻了进去,本来想让追她的人找不见她,但那几个追她的人却偏偏看见她钻进了塌窑,只是那几个人不敢进到窑里来,只在外面拿土块往里面扔,想把母亲逼出来,但母亲就是不出来,外面的人实在没有办法了,也就扔了一阵土块后走了,当母亲回到家里,把半篮子苜蓿放在地上时,身上已满是黄土,而且才发现头上有些痛,一摸才知道被土块打了一个大包。那一夜,母亲一声不吭躺下就睡了,但睡在母亲身边的我却大半夜没有睡着。
后来,听到这件事的我二姑,心疼了好些日子。二姑家与我们家仅隔一座山,有一次,二姑就把她家里掐的苜蓿,装在背斗底部,上面装上柴草,偷偷地背到我家来,让母亲煮了给孩子们吃。后来,干脆让我装成到二姑家不远的山坡上拾柴的样子,把二姑早掐好的苜蓿带回来。至今,我常常跟二姑说起这事,二姑淡淡一笑说,不说了,不说了,这都是那些年饿的。
是啊,都是那些年饿的。有一次,我到二姑家,二姑给我做了一顿白面面片吃,当然里面也是和了一些苜蓿菜的,但更重要的是里面飘着几朵清油花。我盘腿坐在炕上吸吸溜溜着吃,二姑站在炕下的地上一边看我吃饭,一边和我说话,说些家里的生活境况,而这时我的两个表弟则倚在门框上眼睛一转不转地看着我吃面片,他们很饿,也很馋,二姑给他们使了好几次眼神,意思是让他们离开门框到外面去玩,但两个小表弟却怎么也经不住白面面片的诱惑,总是倚在那里不走,于是,没有办法的二姑竟然把两个表弟哄到大门外打了一顿,我也听见了表弟的哭声,但二姑回来怕我难堪,却说那两个表弟太贪玩,给他们安顿的活不好好干,她才将他们打了一顿。我知道那时二姑家没有多少白面,但娘家的侄儿来了,她总要做点好吃的心里才能过得去,于是就有了这么一些情节。不知道表弟现在还是不是能记得这件事,但我至今感到当年很对不住两位小表弟。
后来,我在一首仿民歌的小诗中这样写道:
再高的山头,也在天底下,种不成庄稼了,把苜蓿种下,黄土里过光阴,先把牛养下,抱一抱苜蓿,咱不怕天塌下,苜蓿嫩了,咱人吃哩,苜蓿老了,就给牛攒下,想起了苜蓿,一肚子的话,人活一世,也就是苜蓿一茬,头顶着毒曰头,脚底下烫哩,就这么硬挺着,满眼都是泪疙瘩,打下种子,再种下,只要心活着,西北风里也把根扎下前些日子,母亲从老家托人带来了一些干苜蓿,是母亲掐了苜蓿晒干后装在塑料袋里捎来的,就像捎一袋葡萄干一样,看着这些从故乡的山坡上搭乘着汽车来到城里的“珍馐”,我忍不住要向妻子儿女讲起一些有关苜蓿的往事,当然往事毕竟是往事了,苜蓿早已还原到了作为牲口的草的地位,想必一头毛驴和一头老牛再也不会因为人们与它们争食而耿耿于怀了。
乡村的清油
我所说的清油,就是胡麻油。在我的记忆中,饭碗里如果能漂着几朵清油油花,那就是幸福的时光。
听我一位堂兄说起现今的生活:“一天倒掉的洗锅水里,都比以前一年吃的油多。”堂兄说的以前,指的是用玻璃酒瓶装清油的那些年。那时,每家总有那么几个空酒瓶,用来装清油,或者用来打煤油。现在已记不清那些酒瓶是从哪里来的,但瓶里的油是怎么吃掉的却记忆犹新,甚至我都能记得每一滴油是怎么渗到我的骨头里的。
瓶装的清油有这样几种吃法:一种是用一根筷子浅浅地伸进瓶里的油中,然后再把筷子提到饭碗上面,一滴清亮的油就会小心翼翼地滴到面条或者煮好的野菜上面,漫漫洇开了去,再用筷子搅动几下,那油的香味就会均勻地渗透了整整一碗的食物中,尤其是弥漫了人对美味的渴望中。
第二种是倒一小坨油在碗底或者小碟子中,用一片小布片轻轻蘸了油,那布就叫油抹布,在做饭前用油抹布把整个锅抹一遍,热锅散发出的油味和着油抹布的焦味就在屋子里飘荡开来,于是就感觉整锅的饭菜里都有油了。用油抹布抹锅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摊煎饼时,煎饼不会粘锅,纸一样薄的煎饼用铲锅刀一铲就会干净利索地揭起来。只要抹布还油着,就一直用来抹锅,甚至到那油抹布已干了,变硬变黑了,还用来抹锅,仿佛那只是一个程序而已,已不在乎到底有没有油了。那小小的一坨油有时会用上好几个月。
第三种吃法应该是最奢侈的了,那就是一咬牙将一瓶油咕咚咚全倒在锅里,炸油饼。对当年的一个家庭来说,炸油饼无疑可算得上是一件大事。首先说发面,面不能发得太活,否则就特能渗油,一斤油炸不了几个油饼,必须发到刚刚开始活,但基本上还是死面时就要擀面、下锅,这样炸出来的油饼就只有薄薄的一层皮,不费油。第一个油饼是要献到灶爷板上的,家家都这么做。因此炸油饼就有了几分神秘的色彩,甚至有点宗教的味道。炸油饼时,别人不能随便进入厨房,一旦别人进去就会冲了油神,锅里的油就会溢出来。现在一想,那其实是母亲哄我们的,她是怕孩子们进了厨房,炸出一个吃一个,油饼炸完了也就吃完了。她必须等到油饼完全炸完了,每人才能分到两三个,最多也只能分到五个,剩下的全部封存起来,大人小孩都不准吃,用来走亲戚时当礼物用。于是挂在墙上的那一篓油饼就会让我胃里的馋虫蠢蠢欲动了好些日子,直到那些油饼被送了出去,我才会彻底失望,或者说绝望。
说到瓶装的清油,还勾起我对榨油的一段回忆(记得那时每年的冬天,生产队里总要挑几个人到油坊里去榨油。所谓油坊,就是在河沟的悬崖上挖了几孔深深的窑洞,洞里点着清油灯,但对外面的人来说依然觉得黑得神秘,充满了想象,据父亲讲榨油的程序基本上是炒油籽、磨油籽、包油包、压油等等,至于其中的细节,外面的人是不得而知的。
有一年,父亲去榨油,为了让我们全家都吃到清油,曾让我母亲蒸了荞面和谷面馍馍送到油坊里,父亲在那里把馍馍揉碎了,用油拌了,再带回来。吃那样的一碗油馍馍,嘴角流着油,心里也流着油。现在想来,还往往禁不住舔舔嘴角,满口生津。
油榨好了,就要用铁桶担了缴到公社的粮站上去。缴完油,父亲便急匆匆把两只我们那时叫做洋铁桶的空油桶挑回家里,仿佛走得慢了那困在桶底的油就会蒸发了似的。看父亲来了,母亲就赶紧把那两只油桶斜着倒立起来,桶沿下放上一只碗。两只铁桶往往会控出小半碗油来,然后又倒进油瓶里,一看足足有二三两。这可是一家人欢天喜地的收获。因此,能去榨油和去担油的人,都是让队里人羡慕甚至嫉妒的人。
至于分给各家的油,无论是按工分分,还是按人口分,最多也就三两斤,拎两只瓶子或者提一个瓦罐就打回来一年的油了。为此,每每家里来了亲戚,需要给亲戚做点好吃的,比如烙一张油煎饼或者打两个荷包蛋,往往不是缺了面,就是少了油,没办法只好向邻居家借。如果有人手里捏一个茶杯东家进西家出,那人家里肯定是来了亲戚了。借是终究会借上的,但还油就必须等到年底新油分下来的时候了。如果谁这一年借过油,还掉一茶杯,那这家人过年时往往也就只能用油抹布抹锅了。
瓶装清油的年代已经过去,现在油多了,吃的也丰富多彩了,甚至都吃得大腹便便营养过剩了,但我总觉得什么好吃的都没有当年瓶装的清油香。如今想想那从筷子头上缓缓下滴的一滴油,多像一滴忧伤的泪,或者一粒额头上滑下的汗,或者心里的一点疼。如果说一滴水就能映出太阳的光辉的话,那么一滴清油就可映出一段历史,映出一代人的生活,映出那个时代人们憔悴的脸庞和流泪的心。吃过那种瓶装清油的人往往是对生活最少抱怨的那种。唉,瓶装的清油,瓶装清油的那个年代!
乡村的土豆
一
秋天,当一个人一不小心把一颗土豆挖破了,他看到白色的汁从伤口处流出来时,他的心里难过极了,抓一把泥土捂住土豆的伤口,隐隐感觉那伤口是疼在自己的身上。
偶然一个人看到吃奶的孩子嘴角流出的乳汁,他竟然会想到受伤的土豆……
没有人不对土豆怀有母亲的感恩。
二
据说,在一个饥馑的夏天,一个外出的年轻人扛了一袋土豆回家,当他走到村外的一条河沟里时,看到一个姑娘昏倒在地上,他知道她是饿的,思虑再三就从袋子里拿出一颗土豆让她吃了。吃了土豆的姑娘,慢慢有了力气,她立刻朝着那一袋土豆叩了一个头,她说她要跟了他去,有土豆吃就一定有好日子过。小伙子就这样用一颗土豆赢得了一个姑娘。
当然那小伙和姑娘现在都老了,或许都老得去世了,但村里的老人还常常说起这段辛酸的浪漫往事。
三
秋天是挖土豆的时节,如果这年的秋天冷得早,人们就得在雪地里挖土豆了,因此再细心的人,也往往会遗落几颗土豆在土里。留在土里的土豆,经过冬天的冰雪,被冻得石头一样硬;来年春天,春风一吹,又软得一捏就捏出水来;夏天,毒毒的日头一晒,水分干了,土豆就被晒得又皱又干,黑黑的像一只风干了的胃。地里劳作的人,谁若拣到了它,在衣袖上擦擦土,就直接可以嚼了,脆脆的,甜甜的,是可以当干粮吃的。
当然,土豆的吃法很多,可以烧着吃,煮着吃,炒着吃,等等,反正每一种吃法都好吃。现在城里的小饭馆大酒店都有土豆丝这样一道菜,谁能把土豆切得像粉条一样细,炒出来还不变形,那就是被大家称道的好厨师。你可以随便在任何一家饭馆的菜谱上看到醋溜土豆丝、青椒土豆丝、麻辣土豆丝、东乡土豆片、土豆烧牛肉等等有关土豆的菜名。
前些年,有这样一个说法,说一个村里人给外面的人介绍自家的一日三餐时幽默地说,早上吃羊、中午吃鱼、晚上吃蛋。外面的人很惊讶,说吃得这么好啊?其实,这里的人把土豆叫洋芋蛋,他们只是把洋、芋、蛋三个字分开来说而已。
还有一种说法,陇中黄土有三宝:土豆、洋芋、马铃薯。
四
我有一首仿民歌是这样写的:
像攥紧的拳头,在土里挣着,挣出些想法,在土外面绿着,五谷回家了,土豆还在地里,我端起了饭碗,心还在等哩,把手伸进土里,秋天还这么热着,土心里的疙瘩,装着甜甜的奶哩,揣一颗土豆上路,心窝里踏实,我写下的那些小诗,都是土豆粉嘟嘟的花哩土豆是大地的乳房,土豆是藏在泥土里的灯盏,土豆是攥在节气里的拳头,土豆就是咱供养着老人,喂大了孩子,养活了自己的“洋芋蛋”。
五
荷兰有位大画家叫凡?高,是后印象派的三大巨匠之一。他有一幅作品叫《吃土豆的人》,画面上那些在一盏昏黄的灯光下吃土豆的人,有着骨节粗大的手,他们面对土豆做成的简单食物,眼睛里流露出渴望的光芒。凡?高在给他的弟弟的信中说:“我想强调,这些在灯下吃土豆的人,就是用他们这双伸向盘子的手挖掘土地的。因此,这幅作品描述的是体力劳动者,以及他们怎样老老实实地挣得自己的食物。”
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些“吃土豆的人”时,心里嘀咕:凡?高也是个吃土豆的人?他是画面上的哪一位?画面上的这些人怎么似曾相识?
原来我吃的土豆是凡?高的。老家的洋芋,也就是土豆,原本叫荷兰豆,也叫马铃薯,17世纪中叶从荷兰引进到台湾,然后从台湾传入中国内地。
中国引进外国作物有一个特点,但凡带“胡”字的,大多是两汉、南北朝传入中国的;还有一种是带“番”字的,就是明朝以后传入中国的美洲作物;第三种带“洋”字的,洋葱、洋白菜等等,可能是清朝末年和民国时期传入中国的。所以,带“胡”“番”“洋”的作物,大体上指示了我们这些作物传入中国的不同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