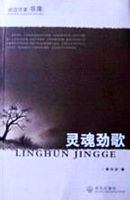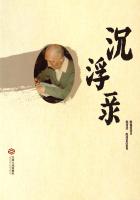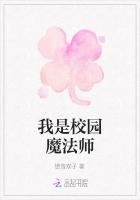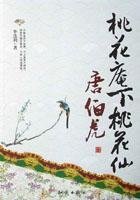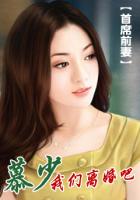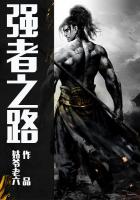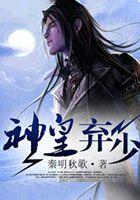乡村的灯盏
孩子们学校里用过的墨水瓶——里面的墨水原本是蓝黑色的,但大都用来写了红色的语言和文字,而且一遍又一遍,老师说熟能生巧,老师还说眼里过千遍不如手里过一遍,直到熟得不能再熟悉了,手里也过了好多遍了,根本不需要再写了,墨水也就一点点地没有了,就像孩子们懵懂的年华一点点地失去了。当然,一个时代也就在这种书写中慢慢过去了,一代人在这样的学习中慢慢长大了。
墨水瓶空了,一个又一个。空了的墨水瓶就用来做煤油灯,把墨水换成煤油就行了。墨水没照亮的眼睛,就用煤油灯接着照。
灯芯是用一小片白铁皮做的,卷成一个小小的细筒,里面穿上用棉花搓的捻子,插在墨水瓶盖中,盖在墨水瓶上,就能吸到煤油,就可以擦一根火柴点亮灯盏了。
再说那白铁皮,原是从收音机用过的旧电池上拆下来的。那电池可是在收音机里播送过最高指示,唱过革命样板戏的,直唱到收音机嗓子沙哑,或者干脆唱不出来了,就废物利用,里面的墨棒让孩子拿到学校里在教室门前的地上画生字,铁皮就做了灯芯。那时,除了收音机用电池,还有手电筒也用电池,记得当时村里演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时,李玉和手中高举的红灯就是在手电筒上蒙了一片红布改装的。当然,村里人没有见过真正的红灯,因为那红灯是铁路工人用的,不通火车的乡下几辈人都没见过火车,自然也就没见过红灯了。但那红灯真的很红,就像把一片红布蒙在眼睛上那么红,或者对着太阳并拢了五指看阳光一样红。红灯在土台上那么一举,灰暗的乡村就有一颗红亮的星了,或者是红亮的心。
红灯高举闪闪亮的岁月已经过去,不说红灯了,还说煤油灯,说如豆的灯光,当然豆也有大小,大的是蚕豆,小的是扁豆。蚕豆样的灯光可以照亮一孔窑洞,而扁豆大的灯光就只能照到一面锅台,或者是炕那么大一点地方了。虽说是高灯低亮,但为了节约灯油,太小的灯光下低处也不亮。
煤油灯是原来的羊油灯、清油灯演变而来的,煤油灯的样式很多,最好的是商店里出售的那种酒瓶一样大,上面有玻璃灯罩的那种,最简单的就是墨水瓶做的。
乡村的记忆里,一盏盏昏暗的煤油灯,在厚重的夜色摇曳着,在纸糊的窗户上照出人的剪影……至于电灯泡,那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了。
通电的那天晚上,乡村中学的全体师生都安静地坐在教室里,谁都不说话,怕一说话耽误了通电亮灯的那一重要历史时刻。大家都在心里一遍遍祈祷,千万别改变了通电的时间,要不这个晚上就会让人沮丧。好多年了,好不容易看着村里拉了电线杆,又架好了线,直到各个屋里都拉上线挂上灯泡了,通电的日子却是一拖再拖,终于确定说是那天通电的,可千万别变了啊。好在上面的通知还算数,晚上8点,还真的刷地一下让学校亮了,让村子亮了,让有史以来晚上从来都没有这么亮过的村子亮得让人简直不可相信了,平常夜里看不见的路啊树的都那么显显地亮了出来,甚至连夜里模模糊糊的山坡也平展展地亮着,同时被电灯照亮的还有学校里忽然响起的掌声和欢呼声,当然还有兴奋的脸庞和按捺不住的感叹。乡村的电灯真亮。
第二天,就有了不少关于电的笑话,说一个老大爷瞅着电灯泡看了半天,然后把旱烟锅凑了过去,但试了几次还是没有点着烟,老大爷得出结论,说电灯好是好,但就是不能点烟。因此,这位老大爷亮着电灯,也点着灯盖,他说要美美地亮个够。
好亮好亮的电灯,亮得有时让人觉得村里将从此不再有秘密。没了秘密的村子,就不再古老。通电的这一年,过年时有的人家就有了录音机,可着院子地吼着秦腔,谁家的录音机响了,全村的人都听得清楚。只是老人们爱听秦腔,可年轻人爱听流行歌曲,因此,录音机刚刚唱了一段秦腔,又放了一段流行歌曲,流行歌曲刚唱了两首,又换成了秦腔……
如果说煤油灯已成为遥远的星光,那么电灯泡就是村里的又一个太阳。
乡村的土炕
黄土箍的窑窑,黄土盘的炕,一辈子守定,这冬暖夏凉炕垴上坐着双亲,炕沿下跑着娃,吆上那对毛驴,就把大苦下汗珠子摔八瓣了,天上的雨你下不下,庄稼人憋气了,也敢把老天骂吃饱了肚皮暖热了心,这就叫把福享哩,打心眼里盼着的,是娃娃一天天长大至于悲欢离合,那是另一片庄稼,这辈子想不通的,下辈子再想—《土炕》坑是一片真正的热土。走进乡下,走进北方坎坎坷坷的农业,风霜雪雨中,土炕是我们最顽强的依托。冷了,炕上暖着;热了,炕上凉着;困了,炕上缓着;疼了,炕上忍着;炕从来不会把我们一把推开。日出人作时,我们感恩土炕;日落而息时,我们眷恋土炕。土炕上出生,土炕上离开这个世界,想想“出生入死”这个词,用在炕头上是再贴切不过了。
作家宗满德在他的散文中说,甘肃皋兰一带的土炕有两种盘法,一种是石板炕,就地取材。扛着铁锤和钢钎,爬上村旁的石崖,撬着,凿着,汗水和石屑一起飞溅,选几块又平整又薄的青石板,手抬肩扛,拿来了,放在砌好的炕洞上,人跳上去咚咚踩几下,不晃动不起伏,和一堆长草泥,在上面严严实实地抹一层,在炕洞里添上草和煤,烧着了,烘干了,再抹一层细泥,再烘干了,连一丝儿死烟也不冒了,铺上草,铺上席,铺上毛毡,新炕才算盘成功了。另一种是打泥炕,在屋子里按照需要,砌出炕墙,里面填满土。把长草泥和好了,就是红黏土和长长的麦早渗和在一起,揽摔,一遍一遍地赤脚踩瓷实了,一锨一锨地堆上去,依然用脚踩平踏实,炕的雏形就出来了。在以后的三个月里,先拿小铁锤不断地砸,半干的时候用木槌轻轻地砸,一遍又一遍,直到完全干透了,掏掉填进去的土,炕洞里添上草和煤,烧着了,封住洞门。土炕上铺上草,扣上瓷盆,十天半月不断地更换,瓷盆里连一点水珠子也没有了,新炕出汗的过程也算是结束了,新炕也才算是盘成了。这种土炕比石板炕更保温,睡上去更觉得浑厚踏实。
在甘肃定西、会宁、通渭一带,土炕的盘法,却与皋兰略有不同,不同之处在于盘炕得用基子。
基子是一种提前打好、晒干的长方形土块,和砖头相似,但比现在的砖头大。我一直以为大是基子区别于砖的一个特点,其实我错了,我后来在一家博物馆里见到的汉砖就跟基子一样大,区别是基子是土的,而砖是把土经过烧制以后形成的。想大汉天子的宫殿也是用烧过的基子砌的墙,我感觉就基子也就有种历史感了。如果把我家屋子的四面墙都换成大砖头的,那是不是皇帝轮流做,今年该到我家了呢?
不做这样的“皇”梁美梦了,还说基子。打基子要用基圈子和石头平头杵子。基圈子,其实也就是框土的模子。先把干土晒上水,润湿了,然后用铁锨操到基圈子中,一个人赤脚站在上面几脚把那土踩平了,再双手提起石杵子,一二三,只三下就打实了,然后用脚后跟在基子的四个角上用力一踩,再用一只脚后跟用力踢开基圈子的后档,人就从基圈子上下来,躬着腰,退开基圈子,把基子搬起来,码到基子垛上。会打基子的人说:打成一片基子,需要“三脚九杵子,二十四个脚底子”。打基子、码基子都是技术活,会打的人一天能打五六百块,不会打的一天也就打上一二百块,不是慢,就是不小心把基子搬破了,重新再打,或者基子垛子本来已垛得很高了,却一转身轰地塌了,辛苦半天白辛苦了,这时打基子的人就懊恼地坐在塌了的基子堆下,骂几句粗话,然后再来。
以前城里搞建筑,要用大量的基子,因为那时砖头少而贵,于是村里就组织了副业队到城里去打基子搞副业,按一千块基子两块钱计算工钱,交够队上的提留,一个人一天要落一块多钱呢。记得我父亲就去城里打过基子。
再说用基子盘炕吧。先在屋里需要盘炕的地方,用基子砌好炕墙,然后用基子在坑膛里支好支架,再把基子削好了,接好缝,盖成炕面,之后就在炕面上抹上厚厚的一层草泥,这种用长麦草和黏土和成的草泥,也叫酸泥。酸泥抹好后,再上一层细泥,炕的样子就出来了。剩下的活就是把炕膛里的基子从炕洞中一片片取出来,把掉在炕洞里的泥土掏出来,填上柴草、晒干的牲口粪烧炕。
有的人家一个土炕要用好多年,甚至几辈子人都用,一片往往是父母结婚生子的炕,儿子也在这个炕上结婚得子。那几片基子撑起的土炕,就这样温暖、呵护了一代代的农家人。
老了躺在土炕上想想一生的收获,便是种了一茬又一茬的庄稼,养了一个又一个的娃娃,唯一的遗憾,是我们把自己活老了,把比我们更老的老人活得看不见影子了,甚至把一个村子都活老了,好在村子里总是老的老少的少。老天老地,老风老雨老土炕,我们不毛之地般的老额头,那里有老土炕的味道。
有子女离开了乡下去了城里,往往把老人也接去住住楼房,但老人怎么说也不愿在城里久留,只是小住几日便要回来,说城里的床不能当炕睡,那绵绵软软的东西根本没有土炕踏实,睡在那里总感觉心是悬着的,尤其是听不见鸡鸣狗叫,听不见毛驴唤草的声音,更闻不到土和庄稼的气味,心里闷得慌。年龄越大的老人越是要急着回到乡下,他们给孩子的说法是万一到了那一天,如果不能睡在自己的炕上,躺在自家的地上那可怎么办呢?
其实,庄稼人也是一种庄稼,庄稼永远离不开生长自己的土地。土炕也是一片土地。
乡村的柴火
以前,缺柴烧是乡下人的一块心病。没柴,粮只能生吃;没柴,冬天只能睡冷炕。没柴烧,我们就只能成为茹毛饮血的原始人。因为农作物的秸秆大多数要作为牲口越冬的草料,所以到野外荒山上铲草根、拾柴火几乎是乡下人一年四季不间断的活。在以前农业社统一出工统一休息的那个年代,农村的妇女们都是利用休息的时间到地埂上、沟坡里去拾柴,一坨草胡根子、一朵骆驼蓬、一棵冰草都会令一个农村人眼睛放光,只有急急地赶过去,一下子铲到自己背兜里,或拔到自己手里才心满意足。
雨水好的年景,野草、野柴生长茂盛,拾柴还不算太难,但如果遇上旱年,太阳把土地都晒透了,连草根都晒死了,拾柴就是个很难的事。那时有一句话,叫“一样有了,样样有;一样没了,样样没;样样没了,填炕没”。记得有一年,就因为柴草少,过年的时候炕冰得像冬天的院子一样,我们一家人挤在一床破被子里,一夜挤来挤去谁都冻得睡不着,没了办法的母亲忽然想起父亲曾当生产队会计时用过的一撂账本,便二话不说就把那一撂账本塞到炕洞里,账本烧了一阵炕才有了一丝温气。有一次,我和弟弟妹妹在大雪天出门铲草胡子,雪中找草胡子,其难度可想而知,因为铲回来的柴比较少,我和妹妹还被大哥打了一顿,至今说起这事来,我们都还有些怨大哥。
拾柴的活主要是母亲干的。离家近、容易去的地方,往往早就没有一根柴了,母亲只好不断地向远处、难处去找。冬天日短,母亲去拾柴,早上出了门,腋下夹个铲子、一根草绳,口袋里装点干粮,中午不回来,一直到天黑,她一个人在荒凉的山沟里、荒坡上不断地铲着、拾着……
有的柴太湿,铲下来立即背回去太重,母亲就暂时摊成一片,晒在山坡上,待干几日再去背回来,但有时也会被别人偷着背走一些,那当然很使母亲心疼,因此母亲尽量把当天铲的柴全部背回家里,晒在门口处才放心。一大捆湿柴至少也有七八十斤,母亲在陡峭的山路上背着一大捆柴艰难地移动着,远远看去,只看见一捆柴在动,而根本看不见柴下面的人,那时母亲被柴草压得几乎脸贴着地面了。碰上一个土坎,就靠上去,喘口气,抹一把流到眼里和嘴角的汗,然后使出猛劲,才能把一捆柴再一次背起。
柴草在她的肩上哗哗哗地闪着,有时闪得很快,有时闪得很慢,可当她停下来听时,柴草也就停住不闪,听她牛一样粗的呼吸。从沟底爬上来,或者从坡上颠下来,到达家门口时,我看见人和柴草一起栽倒在那里,好一阵子没有起来……
现在,村里的山坡上到处是柴草,偶然回到乡下,有时竟忍不住想蹲下去拔上一把,这都是当年缺柴留下的“后遗症”。现在村里人已不在乎山上的柴草了,他们不缺柴烧,一是即使有一年天旱了,不仅存余的粮食可以吃上两三年,连粮食的秸秆也足足可以用上好几年了。再说,有的人家常年都用炭火做饭,甚至还用木炭来烧炕,上了岁数的老人有时就抱怨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节俭过日子,但年轻人却嫌用炭烧炕麻烦,而干脆改用电褥子了。
乡村的炭
在黄土高原上,人们一般见到的石头,都是从河滩里拣的。即使河滩上,石头也少。人们拣来的石头一般是用于压酸菜缸的,或者放在门口垫脚的。这些石头也一般都是麻乎乎的,有拳头大的,有碗一样大的,最大的也就是盆一样大的。形状也大致差不多,和村里人的脸型不相上下。
后来,村里的人们知道一种黑色的石头居然能燃烧,而且热量比硬柴还大。所谓硬柴是指木头,而软柴自然就是草和粮食的秸秆。这比硬柴还硬的石头,也叫炭。也叫的原因是,村里以前光景好一些的人家也用过炭,但那是木炭,是把木头烧到一定程度后把火扑灭,这时木头还没有变成灰烬,储存起来,到冬天,尤其是到了过年的时候就可以点燃取暖了。那种烧木炭的火盆,以前在村里常见,现在却已很难找不到了,要是细心的人家存了一个,在“大炼钢铁”的年月没有被炼了钢铁,那可以算是一个文物了,如若再过些年月,说不定和青铜器之类样珍贵了呢。当然曾架在木炭上熬过的茶罐罐,也和陶罐一样值钱了。
村里第一次用了石炭的那位老大爷,现在已经不在了,但他当时的兴奋和说法却至今在村里还常常被人们说起‘说是儿子从县城卖来一个铁火炉和几节炉筒子,同时拉来了一麻袋石头炭。生火炉的那天,天正下着雪,年关也近了,老大爷仔细目睹了生火的整个工程,然后第二天就在村里逢人便讲,那石头着火后的情形。他抖动着花白的胡子,嘬着嘴,夸张地学着炭火燃烧的声音,他说,那火那才叫厉害呢,哄哄哄一哄哄哄一,似乎老人家的嘴里就这么冒着火苗。
上世纪8乡年代的农村,人们用炭一般只是在过年的时候,把炭当成年货来置办的,都是在县城里买上二三百斤,过三天年有炭烧,感觉这日子也就红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