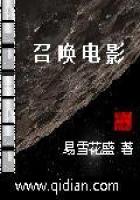她父亲已经转过身来,瞪着自己的脚看;样子很忧闷。“他的脚长得很小,很好看,”她心里想,眼睛恰巧和他的眼睛碰上。索密斯的眼光立即避开。
“你是我惟一的安慰,”索密斯忽然说,“然而你闹成这种样子。”
芙蕾的心开始怦怦跳起来。
“闹成什么样子,亲爱的?”
索密斯又看了她一眼,如果不是眼中还带有着情感,说不定可以称得上贼头贼脑的。
“你懂得我过去跟你讲的话,”他说,“我不愿意跟我们家那一房有任何来往。”
“我懂得,亲爱的,可是我不懂得为什么我不应当来往。”
索密斯转过身去。
“我不打算列举理由,”他说,“你应当相信我,芙蕾!”
他说话的神情使芙蕾很受感动,可是一想到佐恩,她就不做声,用一只脚敲着壁板。她不自觉地摆出一副摩登姿态,一条腿将另一条腿盘进盘出,弯曲的手腕托着下巴,另一只胳臂抱着胸口,手抱着另一只胳臂的肘部,她身上没有一处不是弯弯扭扭的,然而-尽管如此-仍旧有一种风采。
“你懂得我的心思。”索密斯继续说,“然而你在那边待上四天。我想那个男孩子今天跟你一起来的。”
芙蕾的眼睛盯着他望。
“我不要求你什么,”索密斯说,“我也不打听你做了些什么。”
芙蕾忽然站起来,两手支颐,凭着窗子看外面。太阳已落到树后,鸽子全都阗静地歇在鸽埘上,弹子的清脆响声又升了上来,下面微微有点光亮,那是杰克·卡迪更把灯捻上了。
“如果我答应你,譬如说,六个星期不和他见面,”她突然说,“你会不会高兴点呢?”索密斯无所表示的声音还有一点打抖,使她有点意想不到。
“六个星期?六年一六十年还像点话。自己不要迷了心窍,芙蕾,不要自欺欺人!”
芙蕾转过身来,有点吃惊。
“爹,这怎么讲?”
索密斯走到近前盯着她的脸看。
“不要命令我,”他说,“除了反复无常以外,你还当真有什么糊涂心思吗?那太笑话了。”他大笑起来。
芙蕾从来没有看见他这样笑过,心里说,“那么,一定是深仇大恨了!唉!那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她一只手挽着他的胳臂,淡然说:
“当然不会,不过,我喜欢我的反复无常,不喜欢你的反复无常,亲爱的。”
“我反复无常!”索密斯恨恨地说,转身走开。
外面的光线暗了下来,在河上投上一层石灰白。树木全失去了葱翠。芙蕾忽然苦念起佐恩来,想着他的脸、他的手和他的嘴唇吻着自己嘴唇时的那种感觉。她双臂紧紧抱着胸口,发出一阵轻盈的笑声。
“哦啦!啦!就像普罗芳德说的,多么爱小题大做啊!爹,我不喜欢那个人。”
她看见他停下来,从里可口袋里掏出一张小纸。
“不喜欢?”他问,“为什么?”
“没有缘故,”芙蕾说,“就是反复无常!”
“不,”索密斯说,“不是反复无常!”他把手里的小纸张撕成两半。“你对的。我也不喜欢那个人!”
“你看!”芙蕾轻轻说。“你看他走路的派头!我不喜欢他这双鞋子,走起来一点声音没有。”
下面,普罗斯伯·普罗芳德在暮色中走着,两只插在两边口袋里,轻轻从胡子中间吹着口哨他停下,望望天,那神情好像说:“我觉得这个小小的月亮不算什么。”
芙蕾身子缩回来,低声说,“他像不像一只大猫?”这时弹子的响声又升上来,就好像杰克·卡迪更的一记“碰红落袋”把猫、月亮、反复无常和悲剧全盖过了。
普罗芳德又踱起步来,胡子中间哼着一支调侃的小曲。这是什么曲子?哦!对了,歌剧《里里莱多》里面的“水性杨花”。正是他心里想的!她紧紧勒着父亲的胳臂。
“就像一只猫在那里探头探脑,想偷食东西似的!”她低声说,这时普罗芳德正绕过大房子角上。一天中那个日夜交错的迷幻时刻已经过了-外面静静的,徘徊留恋,又温暖,野棠花和紫丁香的香气仍旧留在河边空气里。一只山鸟突然唱了起来。佐恩现在当已到了伦敦,也许在海德公园里,走过蛇湖,心里想念着她!她听见身边有一点声音,眼睛瞄了一下,她父亲又在撕碎手里的那张小纸。芙蕾看出是一张支票。
“我的高更不卖给他了,”索密斯说,“我不懂得你姑姑和伊莫金看中他什么。”
“或者妈看中他什么。”
“你妈!”索密斯说。
“可怜的爹!”她想,“我看他从来没有快乐过-从没有真正快乐过。我不想再刺激他,可是佐恩回来以后,我当然顾不了他了。唉!这一夜碰到的尽够了!”
“我要去换衣服吃饭,”她说。
她到了房间里突发奇想,穿上了自己的一件“奇装”。那是一件金线织锦的上袄,裤子也是同样料子,在近脚踝的地方束得很紧,肩膀上搭着一条侍童的短斗篷,一双金色的鞋子,缀着金翅膀的麦鸠利的金盔,浑身上下都是小金铃,盔上尤其多,只要一摇头,就叮叮当当响起来。穿好了衣服,她觉得很倒口味,因为佐恩看不到她,连那个活泼的年轻人米契尔·孟特没有能见到也似乎有点遗憾。可是铃声响了,她就走上楼来。
客厅里被她引起一阵骚动。威尼弗烈德以为“非常有意思”。伊莫金简直着了迷。杰克·卡迪更满口的“好极了”,“妙透了”、“第一流的”、“真棒”。普罗芳德先生眼睛含笑,说:“这是件很不错的小小行头!”她母亲穿一件黑衣服,非常漂亮地坐在那里望她,一言不发。他父亲只好对她来一次常识测验:“你穿上这样衣服仿什么?你又不去跳舞!”
芙蕾打一个转身,铃子叮叮当当响起来。
“反复无常嘛!”
索密斯瞪她一眼,转过身去,把胳臂伸给威尼弗烈德。杰克·卡迪更挽着她母亲,普罗斯伯·普罗芳德挽着伊莫金。芙蕾一个人走进餐厅,铃声叮叮响……
“小小”的月亮不久就落下去了,五月的夜晚温柔地笼罩下来,用它的葡萄花的颜色和香气裹着世间男男女女的千万种善变、诡计、情爱、渴望和悔恨。杰克·卡迪更鼻子抵着伊莫金的雪味,打起鼾来,健康得就像头猪,倜摩西在他的“古墓”里,由于太老的缘故,也不能不像个婴儿那样睡着:他们都是幸福的,因为有不少、不少的人受到世上错综复杂的人事的揶揄,都醒在床上,或者做着梦。
露水降下来,花儿合上了,牛群在河边草场上吃着草,用它们的舌头探索着眼睛看不见的青草,南撒州高原上的绵羊睡得就像石头一样寂静。宠钵尼林中高树上的雉鸡、旺斯顿石灰矿旁边草窠里的云雀、罗宾山屋檐下的燕子、美菲尔的麻雀,因为夜里没有风,全都睡得很安静,一夜无梦。那匹梅弗菜牝驹,对自己的新地方简直不习惯,微微拨弄脚下的干草;少数夜游的动物-蝙蝠、蛾子、猫头鹰-则在温暖的黑暗中非常活跃;但是自然界一切白昼里出来的东西,脑子里都享受着夜的宁静,进入无色无声的状态。只有男人和女人还骑着焦虑或爱情的竹马,把梦魂和思绪的残烛寂寞地烧到夜静更深。
芙蕾身子探出窗外,听见穿室里的钟低沉地敲了12点,一条鱼发出轻微的溅水声,沿河升起的一阵轻风使一棵白杨树的叶子突然摇曳起来,远远传来一列夜车的隆隆声,不时黑暗中传来那一点无以名之的声音,轻微而隐约的,没有名目的情绪表现,是人,是鸟兽,是机器,抑是已故的福尔赛世家或者达耳提家或者卡迪更家的幽灵回到这个他们过去有过肉体的世界来,作一次夜晚的散步,谁也说不出。可是芙蕾并不理会这些声音,她的灵魂绝非远离肉体,却带着迅疾的翅膀从火车车厢飞到开花的棠篱那儿,竭力找寻佐恩,顽强地抓着他被视为忌讳的声音笑貌。她皱起鼻子,从河边的夜晚香气里追忆着佐恩甩手隔开野棠花和她秀颊的那一刹那。她穿着那件“奇装”,凭窗伫立多时,一心要在生命的烛焰上烧掉自己的翅膀,而那些蛾子也在这时纷纷掠过她的两颊,像朝圣的香客一样,向她梳妆台上的灯光扑去,没想到在一个福尔赛世家人家火焰是从来不露在外面的,可是终于连她也有睡意了,她忘掉身上的那些铃子,迅速进房去了。
索密斯在他那间和安妮特卧房并排的房间里,也醒在床上,他从开着的窗子听见一阵隐约的铃声,就像是从星星上摇落下来的,或者像露珠从一朵花上滴下来那样,如果人能够听得见露水的话。
“反复无常!”索密斯想,“我真说不出。她非常执拗。我怎么办呢?芙蕾!”
他这样一直沉吟到深夜。
母亲和儿子。
要说佐恩·福尔赛不愿意随母亲上西班牙去,那是不完全适当的。他就像一只好脾气的狗随着女主人出外散步,把一根美味的羊肉骨头留在草地上。他定时回头看了一下而已。福尔赛家人被夺掉嘴里的羊肉骨头时,往往会生闷气。可是佐恩生性却不大会生闷气。他依恋自己的母亲,而且这是他头一次出国旅行。他只随便说了一下:“妈,我倒想上西班牙去;你去意大利的次数太多了,我要我们两个人都玩得新鲜。”于是意大利就改为西班牙了。
这小子不但天真,而且也很聪敏。他始终记着自己要把原来建议的两个月缩短为六个星期,因此切不能露出一点你骨子里想干什么的蛛丝马迹来。一个人家里放着一根那样迷人的羊肉骨头。而且主意那样坚定,他实在算得上是一个好旅伴,因为,他对上哪儿去和几时去都无所谓,吃饭却在乎,而且十分欣赏这样一个对多数英国人都是陌生的国家。芙蕾拒绝跟他写信,真是极端明智的做法,因为这样子他就可以每次到达一个新地方时,不存有任何希望或者狂热,而把注意立刻集中在当地风光上面:驴子和荡漾的钟声、神父、内院、乞丐、儿童、叫唤的公鸡、阔边帽、仙人掌编的篱笆、古老的白色山村、山羊、橄榄树、绿油油的原野、关在小笼子里的鸣禽、卖水人、夕照、瓜类、骡子、大教堂、油画和这个迷人的国土上那些浮空的灰褐色山岭。
天气已经热了,很少看见有什么英国人来此,这使他们玩得很开心。佐恩就他自己所知,并没有非英国人的血统,然而碰到自己本国人时,他却往往内心感到不快。他觉得英国人一点没有荒唐气息,而且看事物比自己还要实际。他私下跟母亲说,自己一定是个非社会性的动物-这样离开每一个人,不去听他们谈论人人都谈论的事情,确是开心。伊莲听了,只随便回答一句:
“对啊,佐恩,我懂得。”
在这种隔离的情况下,他有一个无比的机会来领略一些做儿子的很少能理会到的母爱的深厚。由于肚子里有事情瞒她,他当然变得过分敏感,而南欧的民族风尚又刺激了他对母亲这种美丽典型的倾倒。他过去习惯听见人称她是西班牙美人,可是现在他看出完全不是这回事。她的美既不是英国美、法国美、意大利美,也不是西班牙美-是一种特殊的美-他也很欣赏母亲那样的玲珑剔透,这是他以前没有过的。比如说,他就说不出她是否看出他在全神贯注地看那张郭雅的《摘葡萄》,或者是否知道他在午饭后和第二天早上又溜出去,第二次、第三次在那张画前面足足站上半个钟点。当然,这张画并不像芙蕾,然而照样能使他感到情人们所珍视的那种回肠荡气滋味-使他想起她站在自己床脚边,一只手举到头顶上。他买了一张印了这张画的明信片,放在口袋里,不时掏出来看看,这种坏习惯当然迟早会在那些因爱、妒或者忧虑而变得尖锐的眼睛下暴露出来,而他母亲又是三者俱全,眼睛自然更加尖锐了。在格拉那达时,他就完全地被捉着了。那天他在阿尔罕布勒山一处小堡的园子里,坐在一条被太阳晒得暖暖的长石凳上;他原应该从这里眺望风景,可是他没有。他以为母亲在端详那些剪平的刺球花中间的盆花,可是听见她的声音说:
“这是你喜欢的郭雅吗,佐恩?”
他缩了一下,已经太迟了-那点动作就像他在学校里藏起什么秘密资料时可能做出的那样-他于是回答:“是啊!”
“这一张当然很有吸引力,不过我觉得我还是喜欢那张《阳伞》。你爹一定会大人赏识郭雅敢说他1892年到西班牙时没有见到。”
1892年!比他出生还要早9年!他父亲和他母亲在他出生前的生活是怎样的呢?如果他们有权利分享他的未来,当然,他也有权利分享他们的过去。他抬头望望母亲。她脸上有某种神情-一种饱受风霜的样子,是喜怒哀乐、阅历与痛苦留下的神秘痕迹,使她望去深不可测、庄严而神圣,连好奇心都不敢有了。他母亲过去的生活一定非常、非常有意思,她是这样的美,而且这样-这样-他形容不出那种感觉。他起身站在那里凝望着山下的城市、麦苗青青的平畴和环绕的群山,在消逝的阳光中闪映的神奇景色。她的身世就像这座古老的摩尔城市的历史一样,丰富、深远、遥远-他自己的生命到现在为止还只是这样的幼稚、愚昧和天真得不像话!他望见西面的一带山岭就像从海中拔起一样矗立在青绿平原上,按说当初的腓尼基人-一个黝黑、古怪、隐秘的山居民族-就住在那些山岭里!对于他来说,他母亲的身世就像这个腓尼基人的历史对于下面的城市一样:朝朝暮暮,城中鸡鸣犬吠、儿童欢闹,然而对它的历史则茫然无知。他母亲会知道他的一切,而他只知道她爱他,爱他的父亲,以及她长得很美,这使他感到受了压抑似的。别人还有一点大战的经历,差不多人人如此,他连这个都没有。他的幼稚和愚昧使他在自己眼中变得渺小了。
那天晚上,他从卧室的凉台上凝望着城中的屋顶-那就像嵌上黑玉、象牙和黄金的蜂窝,事后,他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倾听着钟在报时时哨兵的呼唤,一面在脑子里吟成下面这些诗句:
深夜里的呼声!沉睡着的古老的西班牙城市,
在它皙白的星光下看去是那样黑漆漆地!
清澈而缠绵的声音,它诉说些什么悲痛?
是否那守夜者,讲着他太平无事的古话?
还是个筑路人,向明月振起他的歌喉?
不,是一个孤单客在哭诉自己的情怀,
是他在叫唤,“要多久?”
他觉得“孤单”两个字太平淡,不够满意,但是“孤伶”又太过头了,此外再也想不出两个短长音的字眼能用得上的。诗写成时已经两点过了,再拿来自个儿哼上二三十遍,一直过了3点方才睡去。第二天,他把诗抄出来,夹在写给芙蕾的一封信里,他总要把信写好方才下楼,这样就可以心无挂碍地陪他的母亲说笑了。
就在同一天快近中午的时候,他在自己旅馆的瓦顶平台上,感到脑后忽然隐隐的一阵子痛,眼睛里有种怪感觉,人要作呕。这是太阳和他太亲热了,中了暑。往后的三天全在半昏迷中度过,除掉前额上的冰块和他母亲的微笑外,他对什么都只有一种迟钝的、痛楚的冷淡感觉。他母亲从不离开房间一步,总是静悄悄地专心一致地守护着他,在佐恩的眼中简直像个天使。可是有时候他会极端地自怜自艾,并且希望芙蕾能看见他。有几次他痛苦地想像着自己和她、和尘世的永诀。他甚至拟了一个由他母亲转给芙蕾的遗言-可怜的母亲啊!她一直到死都会懊悔不该分开他们-可是他也很快看出现在他可以借口回家了。
每天傍晚时会传来一连串的钟声-一串宕荡的叮当声从下面城市里升起来,然后又一个个落了下去。他听到第四天傍晚时,忽然说道:
“妈,我想回英国去,这儿太阳太厉害了。”
“好的,亲爱的。等你能够上路时,就走。”立刻他觉得自己好过了些-但也卑鄙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