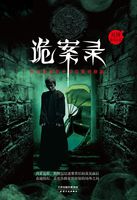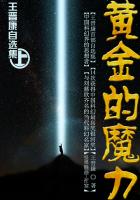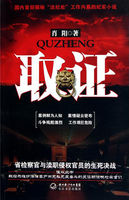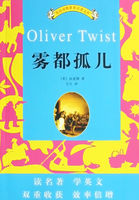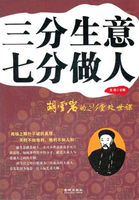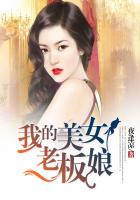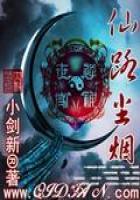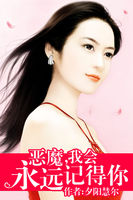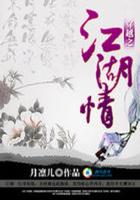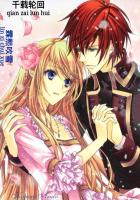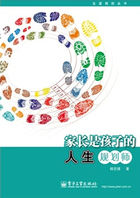全球化时代的底层写作与乡土叙述
一
对于沉寂日久的文坛而言,近几年来关于“底层写作”的争论,可谓是一件不大不小的事件,其持续至今仍没有终结的迹象。显然,“底层写作”作为一种命名,无疑是近些年来才有的事情,但作为一种写作倾向及其叙述表现手法,却是早已有之渊源有自了。因为,其自有阶级以来“底层”就已存在,因而关于“底层”的写作也一直不绝如缕。但问题是,为什么唯独在新世纪以来才有“底层写作”这一称谓或命名呢?而据阿尔都塞看来,命名的变化其实体现的是“总问题领域”的变化。换言之,“底层文学”之于新世纪,显然是不能等同于“底层”叙述之于文学传统的。因此,讨论“底层写作”就不能不涉及到具体的语境,而不能被“共时化”为超越时代的写作趋向了。从这个角度看,像鲁迅的《一件小事》和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等等,就不能被纳入到“底层写作”这一范畴中了。同样,虽然“底层”不可避免地与苦难联系在一起,那些不同时代描写苦难的小说,也不能被放在“底层写作”中来讨论。
讨论“底层写作”,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底层”到底意味着什么?而当“底层”与“写作”耦合在一起的时候,又意味着什么?其实,在这里,第一个问题是从属于第二个问题的,也就是说,只有明晰了“底层”与“写作”之间的耦合关系,我们才真正明白“底层”在这里意味着什么。换言之,是“底层写作”赋予了“底层”的含义,而不是相反。如果“底层写作”关注的是底层的悲苦和艰辛的话,那么底层写作大可以称之为“新左翼文学”,而实际上已有不少多学者从左翼文学与底层写作之间的关系入手,发掘出其间存在的内在关联。同样,“底层写作”也被认为在精神上内在于批判现实主义中,因此不妨看成是其在新世纪的余音。这种种从源头挖掘“底层写作”的做法,虽然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其实也表明,这种做法恰恰忽视了“底层写作”中最重要的一环,即其与当前语境的内在关联。也就是说,“底层写作”之所以被称为“底层写作”,而不是新左翼文学或者新批判现实主义,其本质的规定性就在于全球化时代中国当前现实语境的制约。
顾名思义,“底层”就是社会的底层。但这一底层的构成,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毋宁说,不同时代有自己不同的底层之构成。建国前,“底层”无疑就是阶级构成上的被压迫阶级,故而那时的底层写作就可以称为左翼文学或无产阶级文学。建国后,“底层”的构成无疑发生了翻转,此前作为底层的农民和工人阶级,此时已变为国家的统治阶级,他们虽然在物质资源的支配上仍然处于社会的“底层”,但在精神的层面上却是国家的主人,因此对他们的叙述,显然已经不能被称为底层写作了。一直到八十年代,这种状况仍然有所延续。很明显的就是那些改革小说,比如说鲁彦周的《彩虹坪》等等,其中主人公虽然处境极其艰难,但却不能被称为底层,而毋宁说他们这种处境只是暂时的,一旦改革的实施及其承诺的兑现,这种艰难的处境就会发生改变。伤痕小说虽也写到苦难,但这是“英雄”的受难,自是另当别论。而即使是那些知青小说,在写到知青返城后的极端困窘(如梁晓声的《雪城》)时,这种对未来的希望仍一直存在。但到了九十年代以来,情况则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其实已有端倪显露,那就是孙少平的难以预测的将来。如果说孙少安还可以在改革的承诺中发家致富的话,那么孙少平的未来则注定了前景黯淡,因为他其实就是那当前中国数以万计摆脱了土地的束缚,纷纷来到现代大都市的青年打工者(小说中叫“揽工汉”)的原型,而这正是全球化的今天所亟须的;全球化在孙少平身上已经显露出了最初的伟力,这一状况在今天已然变得十分明显。
其实,《平凡的世界》也已显示出乡土中国的农村在全球化时代的结构性位置,即作为为“全球空间”(或全球化大都市)输送劳动力的“地域空间”。从这个意义上看,在全球化时代,农村已经在整体上被置于附属的位置,以及被剥夺的处境。此时的农村显然已经不再是八十年代以及更早时期的农村,虽然其在落后上一仍其旧。在今天,全球化无疑已将其敏锐的触角伸向了中国的每一个村庄,而不管这个村庄在地理位置上是多么的遥远,多么的偏于一隅。这从新世纪以来的乡土小说中已有非常明显的表征。而实际上,即使是像李锐的《太平风物》这样表现古典乡土意象在现代社会遭遇困境的小说,也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全球化时代写作的味道和关注底层的倾向,“我能在毁灭和新生,悲怆和欢欣中,找到文学的绿意吗?我能在全球化的滔天巨浪里用方块字立定脚跟吗?这就是我的追求,也是我的困境。”(《骆以军六问——与李锐对话录》)因此,不妨说,在全球化的时代,传统意义上的乡土写作已不复存在:全球化无处不在的渗透,已使乡土写作无可避免地同“底层写作”缠绕叠合在一起,此时,任何试图把它们截然分开的努力已不再现实。而这,也正是本卷要把乡土与底层放在一起的缘故。乡土中国的每一个青年或不再年轻的农民,都在潜在可能的意义上作为全球化时代的劳动者而存在,而不管他的身份及其处境如何,即使是像白连春的《拯救父亲》和曹征路的《问苍茫》中的党员干部,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全球化结构中的一个打工者,特别是前者中的主人公,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和生产队长,以及父亲,这样的三重身份,因而他的打工之路也特别的富有寓意。
二
如果说“底层”范畴表明的是一种特定时空关系的比喻的话,那么这一“底层”其实是全球化时代中的结构性存在。换言之,这一结构性存在,是全球化时代资本的全球旅行所内在决定并以之作为前提而存在的。这一底层的存在,既表现为在整体上作为“全球空间”之外的“地域空间”中的农民,也表现为全球化都市空间中被边缘的群体,以及“地域空间”中被权力剔除出去的弱势群体。而且,这一“底层”也并非原来意义上的被剥削阶级,而毋宁说其在阶级构成上表现出某种混杂性,他既可以是党员、村干部——就像白连春的小说,曹征路的《问苍茫》所表明的,也可以是白领和大学生——就像梁晓声的《贵人》表征的一样。但他们在整体上都表现出被边缘化的倾向,即那些凡是被抛出全球性空间之外的“他者”的存在,都可以作为底层而存在,其既可以是下岗工人,农民工,也可以是社会的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如舞女发廊女、京漂族、蜗居族、蚁族等等。如果说底层总不可避免地带有苦难痕迹的话,这种苦难却很难找到罪魁祸首,因为这一底层面对的已经不再是单个的资本家,或剥削阶级,而是全球资本。他们面对的是资本而不是资本家,这也是今天之“底层”不同于此前阶级意义上的受压迫剥削阶级的含义所在。简言之,“底层”就是全球化时代的“他者”之构成,这一“他者”既是被命名的,也是全球化的逻辑所内在决定,并不断变动中的。
这样也就能理解,在关于“底层写作”的讨论中,被列举的作家,既有持续写作底层的曹征路、刘庆邦、孙慧芬、迟子建、范小青、王祥夫、陈应松、罗伟章、鬼子、白连春、尤凤伟、葛水平、吴玄、吴君等等,也有早已出道并成名已久的作家,如贾平凹、王安忆、铁凝、余华、刘心武、韩少功、林白、梁晓声等,甚至还包括那些少数民族作家如梁志玲、陶丽群、讴阳北方、肖勤、雪静、王华、德纯燕等。其实,这一作家名单还可以拉得更长,而这也说明,在今天,当全球化已经变得不再能被忽视或熟视无睹,“底层”作为一种结构性的存在也已日益构成我们经验性的日常对象的时候,“底层写作”作为一种创作倾向,其实就是全球化时代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底层”已日益成为各路作家竞相争夺、言说乃至建构的对象。而实际上,这也表明,“底层写作”其实也已突破原有的理论预设,并渗透到各种流派风格的小说创作当中,作为一种构成性的因素而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今天,任何试图从题材上区分乡土和城市,或者从风格上区分小说的努力,都显得多少有点力不从心和犹豫不决。
本集中所选均为新世纪以来乡土题材及底层写作的代表性作品。其目的在于,力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突出新世纪以来中国乡土农村和城市中的边缘群体被剥夺的时代主题,及其现实困境,同时又力求反映乡土和底层写作多方面的面貌。本着这样的原则,以下所选小说中,很大一部分是涉及底层叙述的,另外几篇则大体表现了乡土生活的各个方面及其叙述者想象乡土的不同方式。
三
城市一直是乡土叙述的参照和“他者”,同时也是乡土中人“看”世界和感受万物的重要前提,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刘庆邦的中篇小说《到城里去》可以说是这样一篇很有象征性的乡土叙述。小说中女主人公“宋家银”执著不悔地驱赶丈夫“到城里去”,不是因为别的,而是源于城市男性带给她的创伤性体验。这是一个循环式的逻辑,城市成了一个隐喻和象征,更成为一个符号,压制和禁锢了鲜活的个体生命。有意思的是,小说以“到城里去”为轴线,贯穿了当代中国从“文革”期间到新世纪近三十年的历史,这是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的三十年,也是中国从全球化之外逐渐加入全球化进程中的三十年,但在小说中却是以一个农村女性的视角,把这三十年的时间变化转换为仅仅从农村到城市的空间上的位移,三十年的历史变迁,对中国的农民而言,其意义仅在于能否走向城市并能在城市定居;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隐喻式的表达。
其实某种程度上,《到城里去》中城市/乡村的二元对立以及那种不断走向城市的原动力,也是全球化进程的表征。全球化造就了区隔性的不同空间,同时也决定了空间中位移的方向,而从农村到城里去,某种程度上就是“地域空间”向“全球空间”旅行的表征。这一位移,对于大多数农村民众而言,无疑充满了创伤性的体验,这也是底层写作大都带有苦难叙述的原因。其实,对于农村民众而言,一方面是前赴后继地奔向城市,另一方面又是不断返回农村。这种返回既有季节性的空间位移,也有失败后的逃回农村,或者永远的被放逐。事实上,“宋家银”的创伤性体验也已预示着城市的冷酷和无情。这条道路注定了充满艰辛和血泪,她的小叔的死和她的老公二十多年的城市流浪史已再明显不过地证明,城市真正欢迎的并不是他们这些衣衫褴褛的农民,他们只能作为边缘人的身份出现在城市中,作为一道风景存在。但这并不能阻碍一批又一批的城市寻梦者的前仆后继。在陈应松的叙述中,城市就像一个永远的噩梦,他的《太平狗》极其震撼地展现了这一情形。在这篇小说中,程大种和他的狗(名叫太平)千里迢迢来到了武汉,作为人,程大种永远地留在城市,狗却最终回到了农村;而不管是人还是狗,城市对他们都是一个噩梦,程大种惨死在城市,狗也经历了九死一生。这种创伤性体验,在罗伟章的《我们的路》、孙惠芬的《天河洗浴》、白连春的《拯救父亲》中以另一种方式呈现出来。在《拯救父亲》中,城市对那些农村劳动者们一开始就是充满敌意的,而父亲这一形象也别具象征色彩,因而,“拯救父亲”其实就有了拯救未被城市玷污的淳朴之人的象征,以及对过往岁月的怀旧和希望了。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原来意义的村庄已然不再,故而在孙惠芬那里,虽然她一直写着“歇马山庄”的故事,但这村庄也已标刻着外面世界的痕迹,返乡其实并不能带给吉佳(《天河洗浴》)些许安慰;而对罗伟章的主人公而言,家乡显然也已不再是归路或港湾,因而最终只能是再一次远走他乡。城市既可畏,故乡又不可留,这种矛盾心理纠缠在一起,其结果往往是导致农民打工族在城乡之间不停地摇摆,只能作为在城乡之间游动的边缘人群了。
如果说,底层是一种结构性存在的话,那么在鬼子对底层苦难的书写中,则把它推到了极点。鬼子向来擅长底层的苦难书写,其越是充满暴力和偶然,也越让人感到荒诞而实则必然,他的《大年夜》也许是其中最让人欷歔不已的了。虽然,城市对进城打工的农民们是一贯的痛,但这种痛并不仅仅针对农民打工族,也指向城市或城镇中的底层和被剥夺者。曹征路的《那儿》和温亚军的《嫁女》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两篇,前者更是经常作为“底层写作”的代表作品被列举。《那儿》中的杜月梅和《嫁女》中的“男人”无疑是被剥夺者的典型,前者靠出卖自己的肉体维持生计,后者则堕落到天天靠赌博度日;对他(她)们而言,并非天生如此,实则是迫不得已:企业倒闭自己下岗,而青春不再。这“迫”势其实就是全球化时代的那种结构性的不平衡,是全球化所带来的资本的重组和优化组合所造成的,这里面虽然有人为的因素,但人力其实只表现在促进或延缓,而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从这个意义上说,《那儿》其实最为形象地展现了全球化所造成的结构性的底层的产生的过程。小说之让人感到反讽的地方就在于,革命曾经给予的承诺,在这全球化的大潮中竟显得如此的荒诞和微不足道,这不禁让人怀疑那美好的承诺是否曾经存在?或许,“英特纳雄那儿”最终只能混成为一个叫着“那儿”的不成调的发音?是耶非耶?
实际上,城市并不总是噩梦,这里面往往是既有恨又有爱,既充满创伤性的体验,也有美好承诺的实现和寄托。铁凝的《逃跑》就是这样一部小说,小说中,老宋就是带着对城市的寄托和期望来到剧团,而实际上,靠他二十多年的诚实勤劳,竟也意外地为他换来了第一桶金——剧团为他治腿募捐了住院所需的一万五千多块钱,他却以截肢省下了大部分钱作为日后开店的资本。他的逃离城市却并非源于失败,而实在是他日后生活提升的契机。其实,对于城市所带来的致命的诱惑,农民们并非没有可以逃避处,他们还可以向更高的山上退居,还可以待在山上不下来,但即使是像李锐那样执著于表现古物的《残摩》(《太平风物》之一),那些有着数千年历史积淀的农具,最终也在全球化的大潮下变得暗淡无光。看来,现代文明特别是全球化并不会在这些古物的光芒中止步!而实际上,所谓现代文明和传统之间并不是从来就对立的,至少在小说的叙述中如此;它们之间也并非城市与乡土之间的简单对应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迟子建的《采浆果的人》就超越了传统和现代之间简单的对立,而“还原”了日常生活的恒久的常态面。
四
其实,不论“底层”看起来多么的艰辛,还是如何的善良,在很大程度上都只是知识分子一厢情愿式的想象;就像不论是进步的乡土还是落后的乡土叙述,其实都是知识分子驰骋想象的方式一样。对于我们,“底层能说话吗?”这样的问题,虽被不断地追问,其实并不能真正成为一个问题。因为,当底层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在社会地位上有所上升,并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时,那么此时,他就已经不再是底层,而只能是“代”底层说话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底层永远是被想象被言说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王安忆的《民工刘建华》就显得很有象征意义。小说中,叙述者“我”一再显示出对刘建华想象和叙述的无力,因为显然,他既不能用憨厚质朴也不能仅仅用狡黠或蛮狠来形容,而这,正表明,任何对民工的想象和叙述,某种程度上都只是本质化的表现,都只是某种源于有意无意的一厢情愿式的想象。
刘心武的《榆钱》中,虽然以底层第一人称口吻讲述故事,但却假想一个作家对话者的存在,其在表现出对代言式写作不满的同时,也表明对底层自我叙述的不信任。
因此,某种程度上,如果作者能很好地把握叙述者同小说主人公之间的距离,倒能给人一种别样的底层面貌。从这个角度来看王祥夫的《端午》和吴君的《陈俊生大道》,就显得别有意味。前者虽写底层的卑微,但这卑微并不是那种叙述者俯视下同情式远距离的投射,而是那种冷静但又略带反讽理解的包容,因而也更能给人一种余韵。后者更是写出了一个小人物的可叹、可笑和可怜来,这使得小说始终笼罩在一种反讽的同情和理解中。而像尤凤伟的《替妹妹柳枝报仇》,更是从反面表现出想象底层的悖论。小说虽然是以第三人称的视角想象他人——即妹妹——的苦难,但其实这一被剥夺的处境对受之者本人却未必尽然,因而这一对所谓苦难施加者的报仇就显得多少有点荒诞而无力,而这其实是以反讽的形式表征了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底层之反抗的无力和虚妄。
五
在今天,或许只有那些进入历史或模糊时空的题材写作,才能表现出某种平静来,而即使是对往事的回忆之作,虽然充满抒情的笔调,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挽歌的味道,李云雷的《父亲与果园》就是这样的例子。因为显然,这种精神上的向后,并不能阻挡现实的推进,已逝的终究只能作为云烟消散在记忆的深处。就像果园之美好,正在其宁静谐和,其在今天,已然被全球化的触角揉碎,只留下回忆,连同作者无尽的感伤。从这个角度看,小说其实是在抒情的笔调中暗含着某种批判。可见,对于乡土写作而言,仅仅题材上的转移是不能解决这种困境的。在这方面,莫言的《大嘴》和阎连科的《黑猪毛白猪毛》可谓是典型。前者在怪异上保持了作者一贯的风格,小说虽然甚少现实的喧嚣,但对“文革”的批判仍渗透于字里行间,小说并不能做到真正的娴静。对于后者,虽然在构思上很见奇特,但仍不免使人想起鲁迅的国民性批判主题,其延续至今,却不太能见出当下时代性的特点;这也不禁让人心生困惑。倒是贾平凹的《羊事》和葛水平的《玻璃花儿》显出充分的余裕来。小说中的乡土,虽然总有一个潜在现代文明的“他者”式的存在,但在作者娓娓道来时却也给人以隔世之感,也更让人气定神闲。贾平凹仍执著于传统农民形象的刻画,尺短意长,余味很足。而对于葛水平,虽也写作现实中底层的故事,但记忆中的“山神凹”却是一个总也抹不去的符号,一个永远让人想象和寄予情思的意象,相反,故事的营造倒成了其次。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对如今的乡土农民而言,城市无疑已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回避的存在并左右着他们的生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以前那种单向被动地承受城市的影响这一状况已然发生逆转,这从新世纪以来的乡土叙述中可以明显看出。“到城里去”已经成为了几代中国农民自觉的意识和口号,这与此前文学对乡土农村和农民的叙述显然不尽一致。城乡流动自古有之,但像今天这样庞大的规模和意识的自觉,还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其间显然有不尽的血泪心酸和痛苦经历,但趋势使然,任谁也无法阻挡,每年仍有数以千万计的农民涌向大都市。这一过程无疑还在延续。其作为一个过程,一方面可能是噩梦,但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改变自身命运的契机,在这里面,可谓希望和失望乃至绝望同在。但只要有期望就可能有创造。既然“到城里去”已经不再是不切实际的美梦而慢慢成为农民们现实的一部分,他们其实是在进行一项伟大的创造:他们既改写了自身的命运,也在改写着中国的形象,当前中国经济的腾飞与作为大国的崛起无疑就有他们的心血在内。如果说,“新新中国”这一话语形态指涉着新世纪以来中国新的形象的产生的话,这一形象显然不仅属于城里人,也属于几千年来远离城市的山民/乡民,而随着中国“脱贫困化”和“脱第三世界化”进程的加快,对他们的想象和书写,也必将随之发生改变,这也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