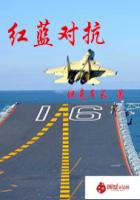却说郑注昨夜中了埋伏,将士们死伤大半,本以为南去的路径守卫松懈,所以才率残余将士连连往南败退。谁知还未撤出曲江池,便又遭了伏兵,幸而他数十年征战沙场,凤翔军一向训练有素,孤注一掷,拼死奋力一战,最后才冲破封锁,突出重围。
仇士良的手段还远不止于此,在西去的各个关口已令幽州军马设下埋伏,势必要将郑注等人斩尽杀绝。郑注眼见兵力不足,不敢再正面迎敌,便将所剩部将分为三队,中军将士保护他往北撤退,其余人马仍旧沿着西去凤翔的陇关古道进发。欲以声东击西之计,左右突围。待中军行至咸阳古渡西渭河桥畔,果然又有幽州人马追杀上来。这一战却是伤亡惨重,所来的数百精兵已然所剩无几。
好在梁副尉得知了音讯,率兵赶了数百里路前来增援,当下两军展开厮杀。待杀退敌兵,西渭桥血流成河,尸横遍地,众人过了河来到对岸,方见脱离险境。郑注便传令下去在渭河岸边稍稍停歇。过不一会儿,只见那陌上古道一匹战马正疾风如电般飞奔过来,说话到了跟前,却是西五营梁副尉的部下参将。
那参将跳下马来,马背上横着一墨黑布袋,里头似是装着一人。郑注瞧见早已明白过来,便道:“人抓到了?我说过,先不要伤她性命。”那参将回道:“她只是被卑职打晕,性命倒无碍,但请大人放心。”忽又道:“不过之前跟在她身边的那位婢女,卑职便自行做主,已将她就地解决了。”
郑注吩咐道:“解开布袋放她出来,先把她弄醒再说,我有话问她。”
那参将领命自去解开布袋。梁副尉趁机便上前回禀道:“大人英明,此事再明白不过。先前卑职就说过她身份可疑,此番咱们将士伤亡惨重,偏偏她安然无恙。仇士郎既是软禁了圣上和太后,又怎会偏偏对她手下留情。”郑注听罢,面色铁青,早不由愤怒起来,只道:“若非念着当年先帝的知遇之恩,好歹她也算皇嗣后裔,否则今日我必将拿她的人头来祭奠我凤翔将士死去的亡灵。”
梁副尉便道:“大人对她仁慈,可她未必会这样想。她仗着自己手中持有圣上的白折玉印,却对大人当俘虏一样驱使,视我们凤翔将士的性命如草芥。大人今日放了她,难保以后她不会再拿着玉印来,在大人面前耀武扬威。”郑注哼了声,道:“之前不过是因为看在先帝的份上,我才恪守臣子本分,听从她的鬼话。如今她再想着拿这个来要挟我,我岂能容她!”
一面说着,只见玥莞已被从布袋中放了出来,随即下令道:“来啊,收去她的白折玉印。看她日后还如何兴风作浪。”
便有参将连连领命,俯身将东西取来交给郑注。玥莞昏昏沉沉的躺在地上,只觉脸上一股冷水洒落,她一激灵,这才醒过来了。一醒来便发觉满脸血污的郑注,旁边则是梁副尉和适才抓她来的那位参将。但见他们神色诡异,个个目光中带着杀气,等回过神来,也就猜着了大概。便听郑注立时问她道:“公主设下的好计谋,把我凤翔将士害得好惨!”玥莞见他忽然这样问,心中更是绝望,只觉眼前这渭河水上的寒气冰冷刺骨,微眯着眼,道:“大人要抓我,我无可说,但不该让兰儿也白白的陪上一条性命!”
郑注忽然忿忿地道:“你不过是死了个婢女就这般受不了了。那我的那些将士们,被御林军围剿屠杀,一夜之间死伤殆尽,如今就剩下这几个人,那死去的数百条冤魂岂非更加无辜?”玥莞道:“大人为何就一口认定是我倒戈相向?此番你们是我的援军,你我同为一体,我岂会反过来蓄意加害?”
郑注冷笑道:“铁证摆在眼前,公主又何必这般抵赖呢。”梁副尉早伸手夺过玥莞腰间的紫金腰牌,回过头上交给郑注。郑注便接着问:“这紫金腰牌哪儿来的?到了此时你还敢说与枢密院毫无瓜葛!”玥莞心灰意冷,只觉浑身是嘴也难以言清。郑注继续追问:“昨夜在凤凰池畔,你我本来商议好了,待你认定圣上的真伪之后,咱们再动手。可那圣上明明是假扮的,这时候你又去了哪儿?你竟消失得无影无踪!”
玥莞听了,这才自悔昨夜因为对戎玉一顾回眸,却铸成大错,当下只得道:“原是我一时大意,因在芙蓉桥头遇见一位故人,心神恍惚,稍一迟疑却已经晚了。等我和兰儿回来,百姓群情躁动,大人已经下令动手了。”郑注面目狰狞,一时竟哈哈大笑,那笑声凄厉恐怖:“好一个心神恍惚?千钧一发之际,公主若还记挂着圣上的安危,怎可在这时候心神恍惚?我不是那三岁孩童,岂能由你这般花言巧语的戏弄!”他道:“事到如今,你我也不必再多费口舌。我凤翔军此番伤亡惨重,可都是拜公主所赐。但许公主不仁在先,我却不能不义,今日我便放了你,你好自为之!”
他收去白折玉印和紫金腰牌,便已然是斩断玥莞今后的所有退路,她再也无力回天。
郑注等人丢下她便走了,玥莞知道郑注心里一定恨她,不但郑注,连梁副尉和那几个死里逃生的将士也一定恨毒了她。然而她同样也没忘记石兰是因何而死。这一笔血账,却不知到底该算到谁的头上。
他们走后,玥莞立在河岸上想了很久很久。回想年节前的种种变故,仍旧不明白到底是谁走漏了风声与仇士良设下这等奸计。年节前仇士良故意放出圣驾夜游的消息,解了郭城九门的宵禁,正是要她放松警惕,好引她上钩。所以这一步步都是被人事先设计好的,她一步步落入被陷害的圈套之中而茫然不知。
最后竟输得这样惨。天下之大竟没有一处可以再让她容身。她也不知今后该何去何从。
她只是知道她还不能死。虽然也不确定活着还能做些什么。
她就这样茫然地沿着河岸往前走。不知不觉已然走了很远,渐渐日色西移,本来她受着风寒身子一直没好,这时筋疲力尽,全身如散架了一般。再也支撑不住,因想着先去驿站里找个地方歇歇脚。
那河岸不远处迎风飘着一面杏黄酒幌,见乃是秦关驿站。她便走了进去。
等走进那驿站正厅,只见过往的几个客商正在楼下吃酒,靠窗的位置另有位年青公子,看着眉目分明,自有一股英气。那公子穿着件宝蓝直领窄袍,腰间石青束带,倒也像赶路的,只不过手中提着一把长长的佩剑。玥莞走过去,那公子似乎不由自主向玥莞瞄了一眼。玥莞也并未怎样留意,径直与驿站的掌柜交涉。
她拔下头上的一支玉翅簪子交给掌柜的,请他收拾一间客房,再备好一匹马,弄些吃得送到房间里去。因为她身上没有任何钱币,所以只能用这簪子兑换。掌柜的听了,一时面色却有些为难,大概是嫌她要的东西太多,这一支簪子根本不够兑换的。玥莞斟酌了下,便道:“我不需什么千里良驹,随便一匹马,只要能行得路就成,至于吃食尽量安排就是了。”
那掌柜的这才呵呵笑着点头,问:“眼下驿站里倒有匹老马,娘子不嫌弃就给了您吧。只是有一样,若是行远路恐怕不成。冒昧问一句,娘子打算去什么地方?”玥莞也不知要去哪里,随道:“我要去往玉门关外。”掌柜惊愕:“娘子孤身一人去那么远的地方做什么。这匹老马最多行个百里路恐怕就走不动了。”
玥莞不过随口说说,当下也只得道:“等过了百里之外,我再想旁的法子罢了。多谢掌柜的费心。”
掌柜的笑了笑连连应诺。稍后便过来一位腿脚伶俐的小店家引着她上楼,穿过一条走廊,那客房的位置十分偏僻,进去就安排妥当了。很快小店家便捧来一些粗糙的吃食,撂在桌案上便又走了出去。
玥莞食不下咽,也总是强撑着吃了一些。之前因为心系营救皇兄的大计,所以一直绷着精神,这时一松懈下来,只觉浑身滚烫,那寒热发得愈发厉害。她不住地咳嗽,不等天黑便先躺进床帐中歇息。
在床帐中躺着也还是咳嗽,昏昏沉沉,几番不曾入梦。渐渐天就黑下来了,屋子也黑漆漆的,过了一阵,却听外面廊子里有动静。有脚步声停在房门前,是位年青公子的声音,敲了敲门,问道:“娘子,在下冒昧,可否请娘子出来一见?”玥莞从床头挣扎起来,将房门打开,只见门前立着个蓝袍公子,正是下半日前在楼下吃酒的那位。心中稍稍诧异,问道:“公子有何指教?”
那人拱手笑道:“在下就住在娘子隔壁,适才路过听得娘子咳嗽不断,想必是身子不适,所以冒昧打扰。敢问娘子可是从长安来的?在下也是长安人。”玥莞不想与他搭讪,便微微颔首示意,道:“多谢公子好意。你我素不相识,男女有别,公子若没什么事,还是请便吧。”
她将门关上,登时又一阵咳嗽,只觉天旋地转脚下险些站立不稳。那公子却并未离开,隔着门继续说道:“看来娘子病得不轻呢,若娘子不嫌弃,在下这里有些碎金子可借于娘子。好歹先请个郎中抓些药来吃,只一味这般硬撑着身子如何受得了呀。”
玥莞有些生气,微嗔道:“我自己会照顾自己,无须公子费心!”
那公子眼见如此,在门外顿了会儿,也就走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