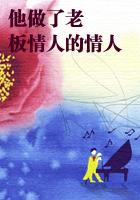我跟着云清疯乱的脚步走着,光从背影看都能感觉到她很愤怒,这种愤怒还杂夹着羞辱与无奈。
“滚!”她一把推开自己的房门,对站在门口的奴婢们怒吼道。
奴婢们才跪拜到一半,逃也似的连爬带跑退出了她的视线。
云清在房里发脾气,疯了似的把花瓶摆设全推在了地上,华丽金贵的摆件在我身边碎裂迸绽,我不再躲闪,对于这种怒气似乎已经有点麻木了。
云清这样子,我突然想起郑府那个曾经让我厌恶的大夫人。
初听郑珠宝的回忆时,我对那嚣张跋扈的大夫人也是没有半点好感,心想怎么会有这么坏的人呢?但是后来通过熊妈的砌词,我才知道那可怜之人的可怜处,谁是天生蛇蝎心肠呢?
而云清呢?是不是也有令人同情的地方?
也许她本没有这么坏,只是因为一念之差而走错了路,然后越走越远?更也许,只是她掩藏得太好,太不屑于直面自己的软弱,她没有熊妈这样忠心耿耿的仆人,没有人为她的所作所为解释过什么,才至使她的可恨之处无限扩大?
我是不是应该再耐心一点,从另一个角度去解读她呢?
难道这就是云清带我入梦的原因么?
她很孤独,需要别人的理解?
但是为什么?她不是已经死了么,她不是一直以自己的姿态存在着么,她也会在乎别人的看法吗?
没有朋友,没有亲人,没有爱人,没人关心她,没人会在乎她是否也会偶尔伤心难过,她甚至连真正的自己都已经失去,这就是她的报应么?
“你给我闭嘴!闭嘴!”她歇斯底里地对着镜子吼道。
我愣了愣,她能听见我的心声?不可能!
镜子里的她马上变得镇定平淡,一脸的兴灾乐祸:“我可什么都没说。”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这个贱人!”云清指着镜子,面目狰狞。
“既然你这么想我说,那我便说了吧。没想到,堂堂上官夫人云清,居然也会像条狗一样,摇尾乞怜地去求天底下所有孩子对母亲本应该就有的爱,真是好可笑,也好可悲。”镜中人间调上扬,嘲笑的语气恰到好处地点起别人的怒火。
云清气得瑟瑟发抖,这一点是不争的事实,她无言以对。
“哎,都是做娘的人,我怎会不明白你心中的滋味?”镜里的她似笑非笑。
“谁跟你一样,你引以为傲的女儿是个任人宰割的废物,我的儿子比你女儿好千百倍!”
一场自己与自己的较量,又开始了。
“我的小外孙儿的确很可爱,聪明漂亮,才华横溢,他的琴声纯净清澈,充满灵性。若是我尚在人世,扶灵弦传他是最适合不过。最重要的是他不像你,他明辨是非,善良正直,他的确比我的女儿好上千百倍呢。”镜里的人话里有话。
“他千般好也与你无关,他甚至都不知道你曾经是怎样的存在。”云清恶狠狠道。
镜中人不屑道:“我不需要他对我有多少感念,我看着他对你嘲讽抵触,就比什么都要解恨。”
云清瞪着镜中人:“原来是你这贱人从中作梗,你对他说了什么?!不可能,他不可能会信你说的话!你只不过是个无处可去的孤鬼,除了缠着我你哪都去不了!”
镜中人似乎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满意地笑着,落井下石:“看着礼儿这年纪,不禁就想你们小时候。我总是一手一个抱在怀里,你老是要抢着坐在我腿上,我为了不让你们任何一个感觉自己被忽视,总是让你们一个人坐一边。有一次你趁我不注意悄悄地把淡儿推在了地上,摔得她哇哇大哭,之后她再也没敢坐我腿上。我在镜子倒映中看到了你对她做的一切,可是你并不知道,你还在我面前装作一片好心,对她又哄又劝的,那时候你才五岁,你就有着这么重的占有欲与这么深的城府,若你有你儿子一半德行,也不至于酿成后来的苦果——”
“苦果?谁苦?若没有我的争取,我礼儿能有今天的锦衣玉食?你只会把好的给云淡,就算有如意郎君你也会藏着塞给她,你从来不会想到我!”
“好不好也都是你说了算,你永远都觉得别人的比你的好而已。你就是这样死性不改,迟早有一天会自食其果,不得善终!”云清想像出的镜中人是她母亲,但是天下哪样的母亲会对自己的孩子说出这样的话,一切都是她自己的幻想而已。
“我是好是坏轮不到你来管,我现在过得很好,比你那不知道死在哪里的云淡过得好多了,可惜没人为她拾骨归葬,永远只是流浪在外的荒骨。”
“淡儿有天护佑,我一点都不担心。我们就想看着你有什么样的下场。”镜里的人阴冷一笑。
云清瞪着镜子,迟疑地梗了梗脖子:“我们?——”
镜里的人得意笑着。
云清的脸突然变得悲伤,有点无所适从,走近镜子,好像在里面寻找着什么:“爹?爹?是不是您来了?您在吗?这么多年,这么多年了为什么您一次都不来见见我?”
“你还有脸见他么?”
“你滚!你滚,我不想听到你说话!爹,你出来见见我,你听我解释,你听我解释……”
我从来没听云清有这样的说话语气,卑微,低下,苦苦哀求,看来她也有软肋,她的软肋,是她的父亲。
听说云父在她出嫁后就云游去了,这些年不仅是云淡没见过她,连云清也没见过他。
听云清的语气好像是云父生了她的气,故意避而不见——但是什么样的父亲会这样狠心,扔着自己的一个女儿下落不明,另一个女儿嫁人生子都不过问一次呢?
“从你踏出第一步开始,一切就错了,而你不肯回头,不肯收手。清儿,你也是我的孩子,但为什么你一定要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淡儿的痛苦之上?你们是亲姐妹,是骨肉相连的啊!”镜中的脸柔和了许多。
光影透过窗纱打在镜上,我仿佛真的看到那里站着云母,那个巧笑嫣然、善良又有些孩子气的年轻母亲。
“别来跟我说这些恶心肉麻的话,你让爹来见我,我就放过云淡。”云清狠狠地跟虚无的母亲交换着条件。
“你真是无药可救,你爹不会原谅你,更不会与你做这种可笑的交易。除非你放下杀戳,向上官博吐露真相,交出你抢来的一切,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光影一下偏斜,仍旧是云清自己阴毒的脸。
云清瞪着镜中人,咬牙切齿地笑了:“让我放下今日一切,决不可能!”
镜中人冷笑。
“我不会放过云淡!她还活着,我知道她还活着!你说得这么多无非也只是想保住她!挖地三尺我都会找出她,我会让她生不如死!”
“那我们就不打扰相爷夫人你自残余生,等到下场好戏开幕了,我们再见。”镜里的人挑眉一笑。
好戏幕,我们再见。
云清面目抽搐地想要驳斥,但是镜里已经是她自己的脸,凶神恶煞,眼白泛红,眼圈发黑,丑陋不堪。
她咬牙切齿地拂着自己的额头,但手指带过处,发丝碎裂般一段一段地落下来,她慌乱地摸了摸头,掉下更多的碎发——她尖叫着砸碎了镜子,她以为这是在摧毁敌人,其实是在摧毁自己。
我感觉她要被自己的心魔给折磨疯了。
府门重院,嘶心裂肺的尖叫声回荡在半空。道上仆从低头疾走,对这尖叫之声置若惘闻。
廊道之中年幼的上官礼拦住了抬着大镜的仆从,双手对插在袖袋之中,问道:“怎么?又发脾气打碎镜子了?”
仆从不敢多言,只是谨慎地点了点头。
上官礼轻叹了口气,伸手摸了摸光滑的镜面,很快对将手缩了回去。
他身后的芙叶低声吩咐下人道:“趁夫人外出去快去打扫好,装镜的时候小心点,别侧歪了,免得惹得夫人不高兴。还有,镜台的水粉摆放仔细点,别乱了位子,颜色深浅也要逐次排好。”
上官礼轻扁着嘴,似乎在怪自己这任性的母亲给别人带来了这么多的麻烦。
蓉叶不放心道:“算了,还是我去盯着吧。小少爷快点洗备好,要准备用晚膳了。”
蓉叶护着大镜走了。
待得四下无人,芙叶才开口道:“夫人虽德行不善,但待你始终是好的。你在下人面前总也得卖她些面子,别像午间这样当着众人拂了她的脸面。若是她不在乎你,又怎会生这么大的气?”
上官礼垂着长长的睫毛,小小年纪却有着非常清晰的思绪与述事的道理:“她若对你们好一些,我自然也会亲近于她。她不应该将自己的错误化成怒气落降在你们身上,我不喜欢她任已所为不明事理。”
“人人都称道我们上官府的少爷不仅天赋异禀,而且谦和礼上,你能包容任何人,为何不愿多包容包容自己的母亲?这些年,她的确是多了许多心事,也总是心烦意外。”芙叶与他并行着,两人像是长辈与晚辈在闲话家常。
“正因为她是我的娘亲,我才不想看到她这样,如果连我都这样纵容忍让,她岂不是永远意识不到自己的错误了?我希望,她变回爹以前认识的娘。”上官礼突然扭头看芙叶,甜甜地笑着。
“相爷以前认识的夫人?那时你都还没出生呢,怎知道夫人以前是什么模样?”芙叶俯身给他拢了拢衣襟,生怕他冻着一般。
上官礼看着天空,笑道:“不知道,但是我听说过许多坊间传言,当年爹是如何顶着各方压力将娘亲迎娶进门,我想他如此执着沉迷,定是爱极了娘亲,她一定有许多过人之处,才能令爹如此。而近些年我看到的却是他对娘的疏离与视若无堵。定然是娘变了,才会改变了当初的一切。”
芙叶的笑容变得有些悲伤,问道:“那少爷你想要什么样的娘亲呢?”
上官礼歪了歪头,弯眼畅想:“我觉得最动人的母子情,莫过于那首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行,意恐迟迟归。每每读起,我便想起慈母挑灯夜逢的样子,昏暗的灯光,照着她仔细又担忧的脸,手中的戏结打了一个又一个,生怕一个意外结散了,裂了衣裳会冻到自己在外的游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