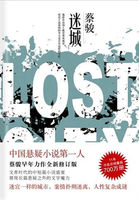丹文回到广州,便退了学,搬到胡力的地下室来。她的身体变得非常虚弱,又没有工作,常常闹心慌,心率莫名其妙地会突然上到每分钟一百三十次以上,夜里不时惊醒。看了很多中医、西医,查不出器质性病因,只说是焦虑过度。每次一闹心悸,丹文就跟胡力说,现在我只有你了,我只有你了。胡力抱着住她,说,是啊,你有我,我在这里。他们很快去领了结婚证。
胡力去了美国后,丹文便住到胡力走前为她在市区里租下的屋子里,深居简出地养病,平时只有姨妈和表姐久不久来看看她。她和胡力商量好,等她的身体好点了,就申请出去跟胡力团聚。胡力到了美国,真的开始了新的人生,一切都很顺利。他只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就念完了硕士。那时丹文身体还是时好时坏,但她开始申请赴美签证。当年探亲签证非常难得,她试了无数次,都被拒签。
那年冬天,圣诞前,胡力转学到在西雅图的华大去念博士。为了省钱,他是坐"灰狗"横跨美国大陆的。他一路写明信片来,告诉丹文所见所闻。那个冬天的美国风光,装饰了丹文在广州的晦暗小屋。她常常躺在床上,瞄着贴在墙上的那些明信片,听John Denver在录音机里唱出她的心声:
All of her days have gone soft and cloudy
All of her dreams have gone dry
All of her nights have gone sad and shady
She"s getting ready to fly
Fly away, fly away, fly away
In this whole world there"s nobody as lonely as she
There"s nowhere to go and there"s nowhere that she"d rather be
……
Fly away, fly away, fly away
她真心地以为,只要飞到胡力的身旁,她的人生就能修成正果。
可胡力到了西雅图后,信就越来越少了。丹文的签证又不顺利,事情就僵持起来。胡力的任何安慰,对丹文都起不了作用,等待的绝望让她几乎崩溃。丹文的身体又开始变坏,心悸的毛病又犯了,夜里常常惊醒过来,睡衣全是湿的。到这时,她再不能一犯病就抱着胡力哭诉:我只有你,我只有你了。她开始不停地给胡力打Collect Call(对方付费电话),只要情绪上来,连时差也不顾。她在电话里一遍遍地只是说,她是多么地爱他,为了他,她已经什么都放弃了。现在既然她出不来,她希望胡力放弃学位,回中国来。为了爱情,这是值得的,她哭着总结。为了爱情,我什么都放弃了,学位算什么?我只要你!她又说。每次接到这样的电话,胡力多半是不说话。终于有一天,他说了,他可以回来,可是,那只是为了你,丹文,而不是你说的那个"爱"。爱不是这样的,不是的。真正的爱,想的会全是为了对方的好,而不总是“我、我、我”。你总是说你对我好,可是这好还是不好,是不能只由你说的。丹文!我真不愿意说这样的话,但它是事实:跟你在一起,我常有窒息的感觉。我知道你做了很多,我都记在心上,可却象是憋在里面,让人喘不出气来。
丹文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胡力又接着说了一句:你知道吗?你对我的爱,就象一把刀爱它割出的伤口。你如果体会不出我在说什么,你可以回想一下你母亲过去是怎么对你的。
丹文向我说到这里时,咬着舌头停顿了很久。这的确是一句直戳心窝的狠话,我能够想象,丹文当时因此而受到的刺激有多大。
胡力把话说到这份上,便再也不提回来的事了。这样的情形过了大概一年半,也就是在胡力到美国之后的第三年,丹文突然收到了他委托律师寄来的离婚申请书。胡力拒绝告诉丹文他改换了的电话号码。他通过律师跟她说,他会对她负责的,在他找到工作之前,每个月付给她五百美元的生活费。等到工作之后,他会每月付给丹文税前工资的百分之十五,直到丹文有工作能力或另嫁他人。这种跨国单方面申请离婚的方法,曾被不少留学生采用。要求离婚的人只要在人在美国,如能证明双方分居两年以上,无论对方同不同意,半年调解期一过,只要申请人坚持,美国这边都能判离。
他妈的狗屎!丹文愤怒地说,眼睛里是亮亮的光。他在美国发达了,不愿回国就算了,另外找了女人也罢了,可他竟然找出这么无耻的理由来甩我!我的一生都搭上去了,我是那么爱他,他竟然会说,那是刀对它割出的伤口的爱。到底是谁在割谁?!你说,听过我的故事,你对人类还会有信心吗?说这话的时候,丹文眼睛红了,我轻轻捏了一下她的手臂,想安慰她。
丹文开始玩命学习英文,早晚到越秀公园跑步、登高。健康地到美国去,成了她生活里的新目标。说来也奇怪,她的身体竟然就好了起来,各种毛病似乎是不治而愈,看书到深夜,倒头便一觉到天明。我不为什么,我只想到美国去,我要的只是他当面给我一个Why。丹文说。
丹文见到我的时候,来到美国正好两年半。她也是先到新州落脚,改学了计算机,那阵刚找到工作。起初,丹文很庆幸美国让她的心情好了起来,身体也愈发健康了。可是,你强埋到心底的事情总是会回来的,你真不能不信,她说。
丹文找到工作安定下来,在生活已经走上正轨的时候,忽然觉得,这样朝九晚五的职业生涯并没有什么意思,更不是她来美国的真正目的。她心里的百孔千疮,在寂寞长夜里从心海中浮出,折磨着她。她的心情又变得时好时坏。丹文后来想通了,她觉得如果能够见到胡力,他能当她的面说出负她的原因,她就能平静下来。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啊。我付出了全部青春的感情,难道不值得讨回一个Why?丹文悲伤地问。
在这个冬天刚开始的时候,丹文的情绪又开始波动。她忽然就决定,到西部来找胡力。她听说胡力已经在西北的一所大学里教书。她特地选择了坐“灰狗”,按胡力当年西去的路线一路寻来,也看看胡力看过的美国。
丹文的故事结束的时候,我们已经抵达华州的斯波坎。天黑了下来,路边的松树上,挂着积雪。我要从那儿转车,再有两个小时,就能回到莫城。丹文则要进城,然后可能还要到离斯波坎半小时车程的爱州科德林去,那是一个依湖的小城,她说,线索告诉她,胡力在这一带教书。
我犹豫了一下,开始劝她,过去的就过去了,为过去折磨自己,是最不值的事情。她冷笑了一下,说,没有用的,你到底年轻,你不懂。那是一个刻进你生命里的痕迹,哪能这么轻易,说丢就丢了的?她很优雅地用左手的食指轻轻撩了一下右衣袖,说,你看,这里。我清楚地看到那是一只狐狸的刺青。我好奇地凑近了些,发现那是一只很可爱的狐狸,眼睛眯着,温厚地笑,带着某种我熟悉的味道。狐狸的大尾巴高高翘着,栩栩如生。
当我能将它亲手抹掉的时候,我的心才能真正平息。丹文将衣袖口放下,冷静地说。我张着眼睛,不太明白她的话。丹文又说,他和我在一起,胡力就是狐狸啊。我刚想笑,又想到她前面的话,就惊住了。我紧张得语无伦次起来:你这又何必,你这又何必?退一步海阔天空,真的,留得青山在,可不是吗?丹文忽然眼睛红起来,说,在别人,都是容易的。可你的脚不在我的鞋子里,你哪里懂我的感觉!我来美国后看到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被负的女人,她一直想要个说法。直到有一天,她杀掉了负她的男人,将那男人的睾丸压成一对耳环,天天戴在耳边,她的感情才平静下来。这个故事让我哭了,我觉得特别懂那个女人,真的,我特别懂。丹文说到这儿,见我脸色大变,马上很轻地一笑,说,我是说故事,你懂我的意思。
我给吓住了,一时不知如何反应。分手前,丹文忽然说,说了那么多的胡力,你想不想看看他长什么样子。我犹豫了一下,说好啊。她就伸手到棉大衣的内袋里去掏。一下,掏出了一把很小的深棕色手枪,很像我在书上见过的勃朗宁“掌心雷”。丹文将手枪拿出后,很快搁到军棉衣的另一只兜里。我压抑着“啊”了一声。我知道,在美国平民随身私携枪支是违法的,所以没加思索,就说,你有枪!丹文拍了我一把,说,嘘,别大惊小怪的。刚来美国时,我住在新州不太安全的区,每天夜里,都要在枕下垫着手枪才能睡着。后来就习惯了,出门都带着它,心里才踏实。今天早上就是差点把它忘在了旅馆里,我吓坏了,跑回去找,所以才来晚了。还闹了头疼。你会用枪吗?我小声问。还好。丹文点点头说。以前在国内军训时摸过,来美国后我常去练习的。习惯了,这玩艺儿会让人上瘾,我一到靶场就来精神,子弹一发发打出去,感觉特别放松。说起来你也许不信,我有时忙,太长时间没有练枪,就会感觉特别压抑。今天早上在比林斯,我的手忽然很痒,去找靶场,没找着。说着,她从兜里掏出了胡力的照片。
我将照片拿到手中,一下呆住了。
竟然是我的房东逸林!
逸林大哥,怎么可能是你?怎么会是你?
我松开了抓着小行李箱拖把的另一只手。双手握牢那张过了塑的彩色照片,同时急促地前移一步,寻找更明亮的光源。我听到脚下小行李箱倒下的响声,可眼睛却不愿意离开照片。
的确是逸林。五官、轮廓,特别是脑袋朝左微斜的习惯动作所呈现出的脸部线段,都是这样地熟悉、可感。候车厅里温度过高的暖气烘着熙来攘往的人流,我却感到似有一阵穿堂的寒风吹过,忍不住缩了缩脖子,压抑着没发出声。
这是一张多么好的照片。逸林年轻的时候,竟有这么好看的笑容,那笑容明朗得几乎能灼伤我的眼睛。我已经太习惯了他如今总是若有所思的表情里不愠不火的浅笑;他现在的皮肤似乎比过去粗糙很多,他的眼角额上如今已爬上不少细纹。我盯着照片,在心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自语。在这张照片里,逸林穿了一件色泽看上去很新的军衣,是只有两个兜儿的士兵服,眼睛因为陶醉而半眯起来,嘴角竟然还留有胡子。风吹过来,他额前的长发扬起几缕。我认识的逸林一直都是留着平头,没想到他留着大鬓角竟然是这个样子,虽然看着有点过时,却带着英勃的孟浪。他身后是烈火一样蔓延盛放的木棉花。我在遥远的南疆长大,我知道能开出如此繁盛花朵的木棉树,至少会有四、五层楼高,所以逸林应该是在半山腰上或建筑物的楼顶,迎着南国和煦的春风留下的影象。
你认识他?灰蓝的灯下,丹文将我的行李箱扶起,带着明显的狐疑,问。我强迫自己继续盯着照片,装着没在意她的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又该怎么解释自己见到照片后的不寻常反应。心中压迫性的紧张让我感到了内急,便下意识地捂了一下小腹。丹文不再响,我忽然感觉到右脸颊拂过一缕寒气,痒痒的,让我鸡皮顿起。我随即侧过脸来,发现丹文凑到了我身边,目光越过我的肩头,微蹙着长长的细眉,看着我手里的照片,然后又看看我。她离得那么近,脖子上红围巾的长绒毛,若有若无地触到了我的耳根、脸颊,我甚至能看到她藏在眉中的那颗痣在突突地跳着。我惊异地想,她带着如此冰寒的气场,真象一条突然窜出的冬眠的蛇。这个想法使我哆嗦了一下。我的失态换来了丹文意味深长的一笑。她很轻地按下我的肩头,然后伸过手来,将逸林的照片一把收了回去。
你认识他?丹文盯着我的眼睛,又问了一遍。No!──No,No,我快快答道,可心里在挣扎:要不要告诉她?要不要?
我一路沉浸在丹文的故事里,对她的悲愤已经产生了几近感同身受的同情。她冒着一路的风雪,朝着往事千里苦寻,本身就已经让我感动。可是她要找的人是逸林!逸林和许梅,是这些年来我在美国最亲近的朋友,我尊爱他们。而且,更重要的是,逸林牵涉其中的,还不仅仅是情事。如果丹文说的是真的,他伪造学历那档问题,很可能会毁了他在爱大的前程,甚至他将来在美国学术界发展的前程。当然,那也许不是绝路。美国是如此现实的国家,逸林凭自己在美国的一贯优良业绩,很可能逢凶化吉。可是,其间会有多少的沟坎、变数,只有天晓得了。
我开始后悔,全因为自己管不住自己,一不留神,竟卷入了本是萍水相逢的丹文的感情旋涡。现在绝对是三十六计,逃为上上计。我避开丹文的目光,弯腰去拉行李箱的拖把,扯了几下才将它扯出来。我尴尬地看看丹文,她却有点凄凉地笑笑,将照片慢慢放回她的军棉衣内袋里。
我掩饰着说,听你讲那些故事,我以为他是个很阴郁的人呢。其实他看上去很精神,简直有点意气风发呢。丹文伸手过来,拍了一下我的肩,说,那时他刚拿到来美国的签证,现在想起来,那应该是他一生最得意的时刻吧。
听了这话,我马上联想到逸林的假学历,心里有点慌张,好像丹文手里捏着了我自己的把柄一般,不敢去答她的话,支唔着点点头,又摇摇头。好了,再见了,阿兰。这一路多亏有你,真是奇遇。丹文递手过来,我们的手就握在了一起。我没想到她的手这么瘦软,很单薄的一把,让我一惊,心里生出极深的怜惜,一时竟有点不舍得放开,挣扎着想:该不该告诉她?
终于,丹文冰冷而坚硬的执着、她口袋里的枪、她手上的刺青、逸林不可弥补的历史性的过失可能对他的前途造成的致命伤害,吓住了我。我放开了丹文的手。
丹文──,我随即轻叫了一声,却又不知接下去该说什么。丹文点点头,看着我,等我的话。丹文,我在想──我在想,生活里很多已经丢失的东西,就是能找回来,你也会发现其实已经全不一样了,都变味了,真没什么意思的。你如果到了那儿找不到他,就赶紧回纽约去吧,明天才是我们活着的理由。我很喜欢美国人的一句话:最好的报复,就是生活得更好,你……
报复?我说到了报复吗?丹文盯着我的眼睛,表情有些无辜又有些嘲讽地打断了我的话。她将棉衣披上身,我注意到她的脸色在灰蓝的灯下显得疲惫而苍白。她朝我淡淡地苦笑了一下,说,谁又不知道时光飞速走远?可总会有些人被留在过去的。说着,她轻咬着嘴唇,摸了摸她棉衣的口袋,脸上的表情变得异常冷漠。
你能不能给我留个地址?我问。丹文想了想,摆摆手,说,如果真是有缘,我们自然会再见面的。而且说实话,我自己也说不准我最后会安顿在哪里。你保重吧。丹文的冷淡让我相当失望,只好讪笑一下,客气地也说了保重,提起行李,转身离去。
刚走出两步,便听到丹文在身后叫,阿兰,阿兰。我停下来,看她。丹文背着她的大双肩包,有些吃力地倒退着,说,你也帮我留意你们学校,看胡力在不在哪儿。说到这儿,丹文突然伸出右手,用大拇指和食指做出手枪的样子,朝我站立的方向一点,说,你如果见到他就告诉他,我在找他。说完,也不等我回话,摇了摇手,转身径自走了。
我站在那儿,脑袋不由自主地晃动起来,身上一阵冷一阵热,耳根烫得难受,视线有些模糊。我赶紧坐到边上的坐椅上,闭上眼睛,想休息一下,却烦燥得很。我觉得我应该做点什么,可又不能想明白该做什么。坐了一会儿,我忽然有非常强烈的冲动:马上给逸林打电话。想到给逸林打电话,我的视线又有一阵短暂的模糊,我起身到卫生间用冷水洗了好一阵脸,情绪才平静了下来。
从卫生间里出来时,车站里的广播响了,说因为西北部普降大雪,有一些汽车班次被取消,我注意听着,我和丹文的班次都将按时出发,便松了一口气。我找到公用电话,拨了逸林家里的号码,可一直都是忙音。我将电话放下又拿起,拿起又放下,直打到手都有些发软的时候,才拨通了。
"Hello!"话筒里传来逸林的男中音,是他一贯的从容不迫。我下意识地抓紧了话筒,眼前晃出逸林在木棉花前意气风发的年轻面容,还有他的小胡子。逸林,是我,阿兰、阿兰啊!我对着话筒压低了声说。你没事吧?正等你呢,路上还顺利吧?雪一直很大啊,你现在哪儿呢?逸林的口气很关切,一句接一句不紧不慢地问着。
我在斯波坎,我一边说,一边瞄了瞄手表。大概还有二十分钟就要上车了,十点左右能到。明晚就是平安夜了,唉,我叹了一口气,转眼去看窗外。对面街市上的几家快餐店闪烁着零星的圣诞灯饰。真的下雪了,薄薄的积雪开始在路边堆起。我忽然有些心悸,这样的情景让我想起了昨夜的冰山镇。我再一眨眼,看到街对面灯光不明的暗处,似乎有个女人的身影在晃动,我将脸贴到玻璃上去,再看,又好像没有什么。你怎么啦?逸林在电话那头警觉地追问。我,我,我们还是快点到西雅图去吧,我将手按到胸口,语无伦次起来。逸林便叹了口气,说,还提西雅图。你说怎么就这么不巧,先是你那边给风雪耽搁了,今早我起来刚送车子去保养换油,许梅在加州的妹妹就十万火急地来电话了。你猜怎么回事?在那儿探亲的许梅母亲腿摔断了,可老太太上了石膏就闹着要马上回中国。医生不同意,说至少要观察一两周。老太太这边呢,就是不认这理,说是想着要花那么些钱,头就发晕,大吵大闹要马上坐飞机回国去。这不,许梅只能赶飞加州救火去了。西雅图是去不成了,真是人算不如天算。不过在莫城过节也不错,老崔让我们到他们那儿吃火锅,他在地下室建的小电影院已经完工,可容几十人一块儿跳舞呢。总之你平安回来就好。
啊,啊,我听着,心里拧起了结,我忽然有点害怕回莫城了。至少是现在不想回。都是不祥之兆啊。你看,连许梅的母亲都赶在这时摔断了腿。西雅图也去不成了?下面是什么?可是不回莫城,我上哪儿呢?这么晚了,跟谁联系呢?我这时竟然想到了我的前任男友。他现在自由了,他得到了无限的空间:我选择离开了他。噢,如果是他选择离开我,我在这大冬天里,在突然无处可去的时候,有可能去找他吗?不会的,我不是丹文,永远不会是。我的脑袋此刻是一团浆糊。阿兰,你怎么啦?逸林的声音大起来,在那边催问。
没什么,就这样了,我回来再说吧,我颓丧地说。逸林说,你可能太累了,等下上车后睡一睡,我去接你。再见,我木讷地挂上了电话。出来的时候,已经到点上车了。
车上旅客很少,只有三分之一的位置坐了人。明天就是圣诞夜了,大学城里的学生们,都该回到各自家中了吧。只有我们这种浪迹他乡的异国游子,才会在这种时候,孤魂野鬼似地在外昼夜兼程地晃荡。
又是一个银色圣诞。司机在前面跟大家说。我想,可不是吗,这一路竟然是追着风雪赶路似的,便去看窗外。跟蒙大拿相比,虽然这儿的雪也不算小,可风却远没有那么强。我心里便对旅途的安全不再担心。车子转弯上高速的时候,我忽然注意到有一辆白色出租车跟在我们后面。上了高速公路之后,开了很长的一段,它也没超车。我的心情开始紧张起来。该不是丹文吧?我使劲回想我们分手后的细节,除了打电话时街对面似有似无的暗影有点可疑之外,别的细节都非常明了。这么一番前思后想,我居然有点平静下来,意识到这多疑显然是从冰山镇就染上的神经过敏。唉,就算是丹文,到了这一步,我又还能怎样?哼,天要下雪,娘要回国,由它去吧。我眯上了眼睛,竟然很快就睡过去了。
汽车在到达莫城前停的最后一站,是华州州大所在地普城。车子转下高速公路时,我醒了过来。普城离莫城只有七英哩的距离,中间是华州和爱州的州际线。华州州大比爱大大不少,可是普城却比莫城小,它甚至没有大型的购物中心,人们需要到莫城去采买百货。我转眼去看灯火零星的普城中心,一下就发现从斯波坎起就跟随我们的白色出租车,也跟着出来了,它很快超过我们,碾过路中的雪水,消失在街道尽头。我吁了一口气,心安下来。
到莫城的时候,已经是夜里近十一点。莫城的灰狗车站在城里一条僻静的街上,由一个来自巴基斯坦的家庭经营。男主人早年在爱大留学,毕业后不好找事,就盘下了灰狗在镇上的经营权,靠它养活一家老小。他对外国学生很友好,哪怕是自己少赚些钱,也总是尽量给他们提供优惠票价。
我一下车,就看到了站在门外的逸林。他穿着一件墨绿色的羽绒衣,朝我摇摇手,微微地一笑,趋上前来接我的行李。我的心"突、突、突"地跳着,不敢去看逸林的眼睛,只是跟在他身后,下意识地四下张望。快上车吧,挺冷的。逸林将我的行李搁到后车箱里,哈了一口气,搓着手朝我叫。
嗨,不冷,比起冰山镇,Nothing(没事儿)。我故作镇静地说,却总觉得腿脚有点不听使唤,磨磨蹭蹭了一阵才坐进车里。车子开出车站时,我看到并没有可疑的车辆跟踪我们,才放松下来,将身子靠到椅背上。
莫城的灯火比普城亮多了。可是街道同样是非常空旷,难得见到人影。跟开学时总是闹哄哄的情形成了鲜明对比。但我还是觉得很安心,毕竟这是我非常熟悉的地方。我看着窗外,由衷的说,回家真好。逸林笑笑,说,是啊。你看上去很累,回去好好休息一下。我仍然回避着他的目光,带点生分地应着,是啊,真是太累了。
逸林和许梅的家,座落在爱州大学校区边缘的山坡地带,在莫城属于中等偏上的住宅区,有山景、校景和市景──当然,莫城只是人口数万的大学城,所谓校景、市景,只是一些零散低矮的建筑而已。学校里很多建筑是彻夜灯火不熄的,夜景还挺好看。因为离学校不远,住在这儿,就是没有车子,上学、购物仍很方便。逸林的太太许梅是生化系的助理教授,跟在林产化工系当助理教授的逸林一样,正在争取终身教授的资格,为了写出一篇又一篇有质量的论文,经常在实验室里熬通宵,生活非常简单。招个房客,一来家里显得没那么冷清,二来他们两人都不在家时,还能有人给看门,让他们觉得放心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