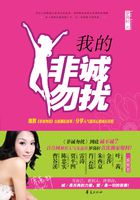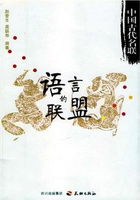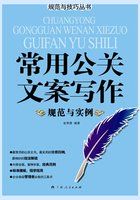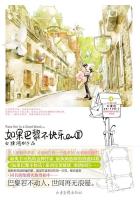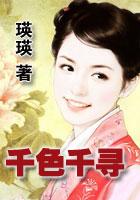据统计,从1944年到1949年,处于战乱时期的中国的婴儿死亡率是203.60‰,而1960年为109.92‰,1965年为72.13‰,1970年为51.95‰,2000年为32‰。不难发现,随着国家的安定与社会的进步,婴儿死亡率已经大幅降低。据黄岗村所在的双江乡计生站2004年3月28日上报给黎平县政府有关部门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2000年,黄岗村共有初生婴儿32人,死亡18人,初生婴儿死亡率高达56.25%。2001年,初生婴儿38人,死亡23人,死亡率高达60.53%。2002年,初生婴儿23人,死亡12人,死亡率达52.17%,当年出生的孩子的缺陷率高达43.48%。2003年,初生婴儿32人,死亡13人,死亡率达40.63%。在黄岗,有对夫妇在20年间虽然生了12个孩子,但最终活下来的只有两个。
黄岗婴儿死亡率为何如此之高?对于这个问题,官方和民间各有说法,有些甚至有些对立,比如官方说农民不注重营养,而农民则说没钱买肉。由于交通不便,卫生条件差,而且奶粉和药品多有过期,在当地一个常见的情形是:有人病了,找来医生扎上一针,就不行了。
应该说,相较于中国广袤的版图而言,“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北京农村与惨状连连的贵州黄岗更像是发展中的中国社会的两个极端,一首一尾,都不具代表性。然而,透过这两个极端的例子,一个真实倾斜的中国同样清晰可见。2005年,《华尔街日报》发表《中国农村依然需要“赤脚医生”》一文,谈到:“进入九十年代,医疗成本迅猛增长,而农村收入却难以跟上。对医疗成本的担忧已成为很多中国人节衣缩食的重要原因;人们在看病前必须预交押金,很多人只能靠向亲戚朋友借钱治病。在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对190个国家进行的医疗卫生公平性评价中,中国被排到了倒数第四位”。另一则来自卫生部的官方资料同样印证了这种不公平性:直到2007年,中国农村地区婴儿的死亡率仍是城市的2.42倍。
事实上,这种身份决定财富的格局不打破,即便到了北京,有些农村籍的孕妇也难免不发生意外。2007年,农妇李丽云之死显然不能简单归咎于她的丈夫如何愚昧、拒绝签字,背后的更多辛酸是贫穷让这位孕妇一次次地错过了孕检机会。
屈原有叹:“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看到发生在黄岗村的故事,回想我所在的村庄的过往,甚至包括我在前文提到的种种“计划不生育”,你的确该“哀民‘生’之多艰”了。
没有兄弟姐妹的社会
几十年来,政府虽然一直宣传“计划生育是一项基本国策”,然而事实上这里的“计划生育”指的是“计划不生育”或者“计划绝育”——谁能说给妇女结扎是为了“生育”而不是“绝育”?生育不用政府计划,性爱与受孕老天自有安排,政府计划并强制执行的不过是绝育与避孕。
而在早些年的宣传画上,几乎都是些没有逻辑推理的口号。比如在我出生后的一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幅“为革命实行计划生育”的招贴画,实行计划生育有以下几个好处——有利于学习马列主义、******思想;有利于教养后代;有利于妇女、儿童的身体健康;有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有利于民族的繁荣。
在“计划不生育”或者“计划绝育”政策极度苛严的时候,未生男孩的家庭通常都会想方设法再生一个男孩,哪怕举家外逃。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小堡村生下超生儿的家庭通常都得交纳四五百元的罚款,或者被计生干部牵走一头猪。也就是说,那时候一个超生孩子的价格差不多正好相当于一头猪的价格。我有一个超生的表弟,他的小名就叫“四百块”,那是他当时的出生价,来到这个国家的路桥费。
网上流传的一些标语口号见证了那个时期的野蛮,如“普及一胎,控制二胎,消灭三胎”、“宁可血流成河,不许超生一个”、“一胎环,二胎扎,三胎四胎杀杀杀!”、“一人超生,全村结扎!”……尽管这些嗜血的标语口号我在小堡村未曾见到过,但在我的印象中,为了避免农民私自下环,做到彻底绝育,当地许多妇女都是被抓上了卡车,一批批地运到镇上去做了结扎手术。如果妇女抓不到或者中途逃走,干部们便会去抓她们的丈夫来结扎。无论这个政策有多高尚,无论被执行者是男是女,当他(她)们被抓上手术台接受自己并不想做的绝育手术时,其人格尊严与生命权利受到冒犯是显而易见的。
2008年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首场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吴建民在回答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时透露,“任何政策都是从实际出发的,经过许多情况的变化,是不是需要对一些政策进行调整,有关部门正在考虑。”随后,计生委官员对此“调整说”予以否定。应该说,争论的出现已经是政策松动的开始。而现在乡村的“计划不生育”在有些地方执行得远不如过去苛严,没有完全进入张五常感慨的“没有兄弟姐妹的社会”。一方面,随着农民大量进城务工,以及对生活质量的追求,许多人并不愿意多生孩子;另一方面,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与社会老龄化问题上升等,也使国家在“计划不生育”政策上做了一些隐性的调整。
与此同时,另一个声音也渐渐浮出水面。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开始全面推行独生子女政策时,山西翼城县作为两胎制生育特区保留下来。三十多年来在这个地方的反向实验表明,两胎制并没有比一胎制增加更多的人口,而且避免了一胎制所带来的种种副作用乃至于无数人道悲剧。
十几年前,也就是我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小堡有一位青年因为未婚先育,闹得鸡飞狗跳,险些被村干部砸毁房屋。2008年的夏天,我在村子里遇到他刚刚返乡的妻子。这对夫妻恩恩爱爱,一直带着独生子在浙江一带打工,日子过得还算温馨红火。由于厌倦了打工生活,一年后我再遇到他妻子时,她正准备投点钱到镇上开家小店。我不知道那个“该扎不扎,房倒屋塌”的时代是否已渐渐消失在她的记忆里了。曾经不容置疑的“计划不生育”政策因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正接近尾声,只是没有人知道那个句号将会画在哪里。
9. 摸着石头进城
曾经读到一则新闻,说的是在与小堡相邻的新建县,有个不足400人的小村落,先后走出了三位进士、五十多位博士,大学生更是不计其数。诸如哈佛大学的博士、著名植物学家胡先骕便是从这个村走出去的。想着列位进士、博士,踩着同一条羊肠山路,集中从同一个村子走出,也着实有些壮观。不过,这一切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今日中国,有多少才子佳人不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不同的只是各自走出乡村的时间、地点以及方式。
和乡下人相比,城里人活得近乎茫然。表面上,后者每天都在奋斗,忙于各种晋级与各类考试,其实他们当中很多人都在为几张无用的证书耗费自己的锦绣年华,都是丢失了生活真谛的人。
城里人似乎总是有很多选择,下了单元楼,车钥匙在手里打转,他们会为去哪个馆子吃饭、到哪个商场购物发愁。如果几家馆子都吃遍了,就真觉得生活没有出路了。谈到为什么换一座城市读研,有学生对我开玩笑说:“学校周围已经没有什么好吃的了”。虽是玩笑,却也略值得回味。
而乡下人,因为只有一两条道路通向未来的旅程与外面的世界,生活过得简单而执著。无论是“生一梯子儿女”,还是拖家带口进城,因为清贫而无虚饰,他们的生活反而有着很强的方向感与使命感,让人不敢小觑。维系他们生活的是熟人社会与宗族文化下的朴素道德伦理,“城市病”似乎与他们无缘,他们为酒足饭饱而打拼,绝不像城里人一样因酒足饭饱而绝望。
这种简单与执著,同样表现在“出乡村”方面。在一个“虚掩着门”的年代,一个尚未脱去“土地拥有农民”的悖谬的年代,几十年来中国农民及其子女之“出乡村”,主要是以下几种形式:读书、参军与打工。而这一切,在我所叙述的小村庄里均有所体现。在此,我不妨称之为“进城三部曲”。
之一:上学记
相传圣西门在年少时,就开始命令自己的仆人每天用这样一句话来叫醒他:“伯爵,请起来,伟大的事业在等待着您”。和小堡村所有孩子一样,我年少时没有仆人,在那个时代能唤醒我的只是我的父母,而父母要我做的事情也只是靠着读书洗去脚上的泥巴,而不是什么伟大的事业。
我这里即将谈到的读书实指考大学,和我今天常说的“美好人生三部曲”(读书、写作与旅行)之“读书”显然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事实上,自从大学开始扩招以后,考大学不但不伟大,甚至已经为有些人所轻视了。
a. 小二郎从政
我还清晰地记得1979年我入学第一天时的情景。那天上午,刚雨过天晴,我和一群孩子踩着村南的泥泞小道去小学。到学校,交了两块六毛钱的学费,领完了语文和数学两本书,然后就放学回了家。那时候的语文课本仍充满了政治气息,“你办事,我放心”、“毛主席的恩情比海深”这样的句子随处可见。不过,数学的格调较以前已经大有改观。“****”期间的数学课本上面写满了阶级斗争的标语。典型的格式是,一页上面写着“最高指示”,如“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下面则紧接着问题:“解放前贫雇农受尽了地主残酷的剥削和压迫。陈大伯租种了地主9亩瘦地,被迫交租4572斤。平均每亩被地主剥削去多少斤?”现在你很难想象,只是教孩子计算的课本里,处处是“狗地主”这样充满暴力与侮辱性的字眼。
虽然小时候通过教科书接受了很多政治教育,但现在回想起来,那些话语对我从未构成决定性的影响。毕竟,我启蒙于“****”之后,此时类似“狗地主”这样的词汇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那个年纪还不能真正体会的充满政治色彩的爱的教育,如“邓妈妈送雨衣”,以及春风吹拂、江河解冻的种种故事。
在我生活的那个年代,战争的硝烟仍未散去。就在欧洲人传唱鲍里斯?维昂的反战歌曲《逃兵》,高呼“如果需要流血捐躯,总统您先来”时,我们还在唱着“准备好了么,时刻准备着”、“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长大以后,懂了些政治伦理,觉得自己从被系上红领巾的那一天开始,便算是“从政”了。当然,即便如此,你也不会真正认为自己的“从政生涯”始于童年。因为你这小二郎,那时候只有流鼻涕的尴尬,而没有流血的冲动。你的眼里,只有大千世界的重叠的影像,而没有真正的政治立场,更别说你会为这个政治立场奋斗几天。
无论如何,相较于从前的混乱岁月,一个去“泛政治化”的时代已经开启。只是,乡下人对于政治运动多少有些后知后觉。在我印象中,直到******下台几年后,学校才意识到不能再挂******的像了。那大概是我读到三四年级的时候,有天下午,来了几个陌生人将华主席的画像摘走。当时不知所以,其实那不过是大人们为一个逝去的时代追加了一个仪式罢了。
b. 一条鞭法
对于小堡村而言,1980年代的前几年至少有两件大事可以载入村志:一是村里(当时仍为生产队)合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二是村里出了第一个大学生。前者是空间意义上的,它让村民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尤其是城里“白人”的生活——有此对比,自是因为晒得黑黑的农民经常羡慕晒不着日头的街上人的缘故。我年少时写诗,怜惜农民的命运,也曾将他们比做“阿非利加洲的黑人”。而后者则是时间意义上的,它让村民们看到自家孩子可能的远大前程。这也是我和我的同伴们自小深切体验父母“一条鞭法”之诱因。
关于如何教育下一代,以及乡村父母在孩子身上赋予了怎样的希望,村里最有学识的一位农民(他同时是我的语文启蒙老师)与我谈到这样一段心路:
记得有次去了城里,看着城里人的白皮肤与城市里的阴凉,城里的繁华与悠闲,我觉得这辈子真是没意思,农民过的根本就不是人的日子。从那时起,我便在想,就是讨饭也要“把孩子奔出去”(当地土语,相当于“费尽心力把孩子送出农村”),不能让我的孩子和泥巴打交道了。
关于我的这位老师的故事,有两点给我印象最为深刻:一是如上所述,自从进城转了一圈后,回到家里觉得自己今生不幸、低人一等,在床上整整躺了三天;另一件事则是他对儿子苛刻的管教。
如今他的儿子早已经大学毕业,留在西部的一个城市工作,回忆起父亲当年对自己的严厉总是置之一笑。那是在小学暑假的一天,父亲发现他没做作业,而是和其他孩子们在“赌纸”(村里的孩子仿大人赌钱的一种游戏,以撕开的课本、作业本或烟壳纸当作赌资),于是将他提回家接受家教。
这位气急败坏的父亲先是逼迫他的孩子冒着正午烈日的酷晒到山里捡一小筐石子,然后让他把石子铺在门前太阳仍可以照着的台阶上,并让他在碎石子上跪一个小时。当孩子终于忍受不住开始大哭时,又被恼羞成怒的父亲关进盛稻谷的木桶里,直到孩子的母亲忍无可忍将他“救”出来。类似“严打”,在农村也算是司空见惯寻常事,我本人也曾像陀螺一样多次被父亲抽得满地打转,完全不堪回首。
透过类似家教事例可以看出,农民对孩子的暴力教育并非“一条鞭法”那么简单。而且,父辈对时代、对人生不可名状的怨怼也会变相转移到孩子身上。基于农村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小堡村的父亲们定是要通过这样近乎残酷的责罚,让孩子知道他这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受过太阳多少苦与热,并引以为戒。我没有亲见那位父亲对儿子的责罚场面,然而每念及此事,回想起自己年少时所受的鞭笞,也不得不感慨:上帝是如何热爱人类,竟要让不幸人家的孩子多此艰辛!
c. 露天电影院
小堡村出第一个大学生是在1985年,距国家恢复高考已经整整七年。自那以后,这个村子像是打开了通往城市的闸门,经常有孩子考上大学。刚开始,每考上一个大学生村里都会放两场电影,包括小队请一场,大队送一场。通常学生家长还会办几桌酒席以表谢意,以尽乡谊。
也许是因为少不更事,或早习惯了在外面闯荡,我已经忘记自己曾经是以一种怎样轻松而淡然的心境离开故乡去上大学的。然而今天,当我写作此文,重新回忆起旧时的一些细节,点点滴滴,竟忍不住潸然泪下。
遥想当地当年——你,一个即将进城的“准大学生”,面对几桌盛载纯朴乡情与父母恩情的酒席,以及入夜时分渐渐飘起的汽油的芬芳,放映机射出的洁白如烟的光束,悬挂在屋舍墙头的电光幻影……而这一切都是为你而设,既是你所熟识的乡下人为你这个未来的城里人专设的人生庆典,又像是一场出乡村的仪式,一个成年礼。年轻无依的你,将从此背负行囊,走过村后的山坡,望着故乡九月阳光里相送的父母与乡亲,远走他城,孤身一人,担负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