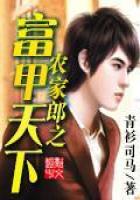林忆寒,你在吗?不要这样好吗?你知道的,我是真心喜欢你的,你总是说希望我过得好好的,可是我不希望你不开心啊,有时候我真是觉得很难过,我不知道你真的很开心吗?我知道有人说我们在一起不可思议,他们不明白你为什么偏偏会选择我,林忆寒,其实我真狠简单的,从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喜欢你,我相信我们一定会走到一起的,那种从没有过的感觉真的让我相信这就是缘分吧。你总是说只有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才觉得生活真的挺美好的,忆寒,你这样说,我真的觉得很幸福你知道吗?没有你我会很难过的,我离不开你,我求你。不要走好吗?别离开我,求你了忆寒。
忆寒,我忽然从睡梦中惊醒,浑身大汗,我喘着粗气从床上坐起来,觉得口干舌燥,一阵阵细小的针刺般的痛楚使我像个大病初愈的人,难过万分,感慨万分。
幸好是个梦啊,望着窗外雪早已经停了,天空上突然明朗起来,我现在突然特别想林忆寒,已经放假了,她到底在哪里呢?她此刻在干什么呢?她在想我吗?
我拿起电话拨通了林忆寒的电话,现在是半夜三点,可是电话那边依旧关机。第二天一早我就整理好自己的行李然后去医院与徐溪然告别。
病房里空无一人,我握着徐溪然的手把林忆寒离开的事情讲给了徐溪然听,她依旧沉默的样子,没有什么反应。我却不知道自己的眼睛里早已经布满了泪水。讲完后我便提起行李箱朝门外走去。我家到学校也不远,就几个小时的车程,所以我会有时间来医院看一次溪然的。
我回到家,奶奶在家做饭,而老头也不知道哪里去了。
我跟奶奶打了招呼后便自己去睡觉了,累了,真的是累了!第二天,李南音大清早就给我来了电话,我听到成绩的一刹那,右眼皮狠狠的一跳,心脏仿佛被重锤击中,霎时间崩溃掉了,内分泌严重失调。
“南音,你真的看清楚了吗?那是祁少的成绩吧。”我说。
“我亲自查的,没错的,不过祁少这次考得很好,二十多名呢,你是怎么考得啊?”
我还没等他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靠。我在房间里使劲喊了声,现在是上班时间,爸爸不在家,奶奶也不知道在哪里去了。我从我爸在家招待客人时的一包烟中抽出一根,缓缓夺给自己点上,火苗迅速蹿了上来,一缕缕青烟从烟头处缭绕的升起来了,为了避免弄得一屋子烟味,我在自己房间里解决了这根烟,完事后又刷了三次牙才使嘴里清新如初,我又把家里所有的窗子打开通了一阵风,这才觉得万无一失了。
教育制度害死人啊。我一字一句的说,声音竟然是那么的孱弱无力。
我忽然产生一种力量,便忽然跳起,在碟机里塞了盘CD,然后把音量开到了最大,我随着音乐甩着我的头发,随着音乐到达高潮,我心里也似乎像是冲破了堤坝的洪水,不可收拾。这个冬天我依然激情四溢,依然充满希望,依然勇往直前,我在密集的吉他声中大汗淋漓全身痛快。
我从柜子里翻出一本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上面薄薄的落了一层土,自从上了大学,我就再也没有翻过柜子里的书,沉重的学习压力几乎让我失去了阅读能力。我轻轻的吹落那些尘土,翻开一页,细细品味起来。第五天,托马斯突然回来,卡列宁向他扑过去,这一刻他们还来不及相互作出必要的表示。
他们都感到像站在冰雪覆盖的草原上,冷得直哆嗦。
然后,他们就像两个从未吻过的恋人那样互相靠近。
“一切都好吗?”他问。
“是的。”她回答。
“你去过杂志社拉?”
“打了一个电话。”
“是吗?”
“没有什么事情干,我在等着。”
“为什么?”
她没有回答,她不能告诉他,她一直在等他。
现在,我们回到了我们已经知道的时刻了,托马斯烦闷得要命而且胃痛得厉害,直到深夜都未能入睡。
特丽莎也很快醒了。她首先想到他是因为她回来的,因为她,她改变了自己命运,现在,他再也不要对她负责了,而她要对他负责。
她感到,她似乎还不能把握更多的力量,来胜任的肩负这种责任。
她立即想起前一天他出现在房门口之前,教堂的钟声正敲六点,而他们第一次见面那天,她下班各阶层是六点,她看到他坐在前面一条黄色凳子上,也听到钟楼里的钟正敲六点。
不,这不是什么迷信,是一种美感,治疗着她的忧郁,给了她继续生命的意志,机缘之鸟再一次飞落肩头闪闪发光,她眼含泪花,倾听着身边的呼吸声,感到说不出的快乐。
昆德拉之于我,就是一个贤明的圣人,我知道有一种东西叫,热情。
中午吃饭,奶奶给我夹了块肉说,“来,补补,下午去洗个澡,小脏孩,看你上学辛苦,你爸准备给你买个手机,下学期有什么事情就给家里打电话。”
“奶奶万岁!”我高兴的说。
“别一点小事就喜形于色。”老爸说,“这也是为了监督你,没什么大事也别总往家里打电话,过几天你就20岁了,你看看隔壁老王家的孩子,才大二,放假没回来就在北京打工呢,一个月二千多块钱,你看看人家国外那个什么比什么茨,大学没毕业就开了个电视机厂,现在是世界首富。你再看看你自己。”
我忍着没笑,嘟嚷着说,“你看看人家******,才四十多岁就当美国总统了。”
老爸显然不悦,呵斥道,“吃完饭感觉学习去。”
奶奶赶紧大圆场,“都别说了,他又不是不努力,管教也不是你这样的办法,快吃吧,菜都凉了。”
我看着两个老人沧桑布满皱纹的脸,默默的扒饭。
老爸给我买手机的诺言很快就兑现了,可是只是一部很普通的三星,即使是这样我也挺高兴的,我趴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研究这个手机的功能和里面巨小儿科的弱智游戏,只一个小时,手机就被我折腾得没有电了,我刚准备打个电话给祁少,结果手机一声刺耳的铃声响过,没电自动关机了。
我决定去医院看徐溪然,毕竟回来了几天都没有去看徐溪然了。
我打了个电话给祁少,让他来车站接我,他说好放假几天也没见到我了,甚是想念,然后我浑身一片鸡皮疙瘩。
我和祁少一起去医院的,徐溪然的妈妈不在,护士说刚走,我坐在床边,看着日渐消瘦的徐溪然,不禁自己悲伤起来。
祁少走出了病房,说消毒水的味道太浓了,出去抽支烟。
我说好。
我握着徐溪然的手,把手放在我的脸庞,让她感到我的温度。我向她诉说着没有她的日子里我是多么的痛苦之类的话。
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起林忆寒来。
有些话,说与不说,都是伤害;有些人,留与不留,都会离开。
突然我感觉到徐溪然的手指动了一下。
我惊站起身来叫了徐溪然一声,可是没有复苏的迹象,我大声叫来祁少,祁少说他去找医生。医生进来后仔细检查了下说这是病人好转的迹象。我说了谢谢医生然后继续坐在床边。
我想会好起来的。
果不其然,四天过后我来看徐溪然,她就已经醒了,而且已经恢复得快了。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而我大笑了起来,正因为这我却把脚崴了,脚上肿起来了一个包。
随着时日的推移,我脚上肿起来的包一天天消下去,散出一片淤血造成的黑青留在皮肤上,像一块黑生生的胎记一样,老爸说快要过年了,别一天在家待着,出去看看有什么合适的新衣服就买下来,然后他甩给我五百块钱就走了,自从徐溪然好了之后我一直没有见她,我们只是隔三差五通一次电话,其他人的电话更是少之又少,那帮家伙似乎散失多年,杳无音讯。我把那五张印有伟人头像的钞票装进兜里,然后拨了电话,约溪然在中心广场的旗杆下见面。
徐溪然来的时候我已经在寒风中等了半个小时了,她意识到自己迟到了连忙腼腆的对我笑了一下,我在她脑门上轻轻弹了一下算是原谅她了。
“猪,看在你等了我那么久的份上,本姑娘请你喝咖啡好不好啊?”
“好啊好啊,”我说。
“我知道有家咖啡很不错呢。”
“远吗?”
“就在那里。”徐溪然抬胳膊指着广场对面说。
“那我们过去吧,冻死我了。”
我们推着自行车慢慢走的往那家咖啡屋走,因为徐溪然是骑自行车来的,溪然问我脚伤怎么样了,我说还行,现在基本像个正常人,就是走路的姿势跟别人有点不一样,徐溪然说我都这样了还这么贫,我还真挺佩服你的,一次就能迈三个台阶,真牛啊。我说你怎么说话原来越像我了,她也意识到自己不知不觉吐出一句我的口头禅纳闷的吐了下舌头。
这家咖啡屋的主任显然是一个很讲究格调艺术的人,这里整体布局让我来有一种很温馨的感觉,门口的两台狂吐热气的落地式空调使我一进门便暖和了许多,这里一共有两层楼,一楼只有寥寥的几个人,我们上了二楼,竟然空空如也,我招手叫了两杯咖啡一盒小点心,他们很快便用一个很精致的盘子端着上来了,就这样,我俩坐在秋千上椅子上,一边漫无边际的聊天一边喝着香浓的咖啡,诺拉琼斯的音乐在哦我么耳边响起。
“对了,我还没有在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听你唱歌呢,你要不给我唱首歌吧。”我说。
徐溪然说,“你神经啊,在这儿?”
我说,“对啊,就在这儿。”
徐溪然说,“我不要唱,老别扭了。”
我说,“在这儿怎么了,反正又没有人,你小声点唱,只给我一个听到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