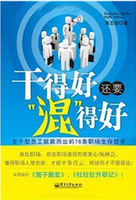随着重节春节的渐行渐近,陈妈妈与娉婷之间却是日显平静。每周的照会如旧,只不过,陈妈妈不再请来观众助威,娉婷也收敛回伶牙俐齿,彼此间客客气气地打招呼,漫谈几句天气、饭否,不咸不淡,不冷不热,反倒令陈君忆变来忐忑难安。
“其实这样也不错,反正,我没指望着她俩能象亲生母女那样亲厚,就是不知道会不会是激战前的宁静。”陈君忆向陈君予倾述内心的惶恐。
陈君予耸耸肩:“谁晓得呢。不如,你点把火试试看烧不烧得起来:告诉妈咪你今年春节要去娉婷家。”
你倒是,等着看大戏!陈君忆瞪弟弟。后者一脸无辜:“你总是要说的嘛。”
也对。每年年三十陪着父母在家看传统春晚、年初一一家人吃汤圆,是陈家恒定不变的规矩。用行动去打破,可比他在语言上答应娉婷要艰巨多了。
也许,找娉婷反悔要容易许多。
晚上,陈君忆每天不管再忙也要做的娉婷家报到功课快近尾声时,临走之际,他吞吞吐吐、晦涩含蓄地围着这个主题说了一大堆不着边际的话。
“就说你春节不能和我一起回老家了,是吧?行,我知道了。”娉婷替他总结。
陈君忆惊悸得大张着嘴,连闭合的气力都提不出来。他特特挑这个时候说,无非是怕有什么雷霆之灾时可以及时遁逃,不想,气氛煦和得完全出乎意料。
“你……你……你,别生气,我开玩笑的。”反悔难,反悔的反悔可就容易多了。虽然娉婷冷静得连继续这个话题的兴趣都没有,陈君忆还是立马主动反悔了。
娉婷正在做手部保养。剥开手蜡,在灯光下反转着细洁的双手自我欣赏,关注度显然比对陈君忆及他的心思转变要高得多。“别。春节年年有,今年你不能和我回去,那就约明年吧。”
她是真的豁达还是装豁达?陈君忆惊悚。宽慰的同时,又有种咬了口青橄榄般涩涩酸酸、说不出味的感觉。也许,爱得太不介意,就不能称为爱了。
“你,真的无所谓?”他问她。
娉婷细心地抹了层护手霜,突然,夸张地惊叫:“唉呀!我怎么这么粗心,还没洗脚就上护手膏!这……这……。”
陈君忆黑线,却不得不挺身而出,有气无力地说:“我帮你洗吧。”
瞬时,一双小脚高高地伸到了他面前。脚主人奸诈而得意地笑。
“娉婷,你真不生气?”一边给她洗脚,陈君忆一边不死心地问。
“不说了吗,春节年年有。”
“那,万一明年我还是不能和你回家呢?”
“那就后年呗。”天气冷,盆里的水不一会就凉了,娉婷着急,“要不,你先帮我把脚擦干,套上绒袜再说。”
陈君忆反将她的小光脚举得高高的。
娉婷受冷不过,苦了脸:“我很生气,很介意,行了吧?可是,生气也好,介意也好,有用吗?你有你的牵绊,我总不能,拿枪顶着你去吧。”
陈君忆无语,沉默一阵,还是忍不住说:“但是,你也不用选择在我面前把自己藏起来呀。”
“我没有把自己藏起来,我真的觉得没关系。”娉婷言辞诚恳,“你要我说心里话?不错,我当然希望你能陪我一起回老家过节。可过节图的是什么?高兴。你去不了我却勉强你硬要去,能高兴吗?第一次你违心将就了我,第二次、第三次呢?一次又一次的不高兴,结果必会适得其反。男女相爱,取两情相悦,如果在一起却达不到相悦的愿望,分手,是必然的事。我不要我们分手,所以,我愿意和你保持个性独立、空间独立。我相信,没有压力的爱,才会天长地久。”
跟着,娉婷皱眉咧嘴:“陈君忆,你把我的脚捏得好疼!”
陈君忆松手,取了干毛巾替她把脚擦干。娉婷愉悦哼歌,好象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了会,陈君忆实在忍不住了,闷闷地说:“你不在乎我。”
“我就是太在乎你,所以才不敢轻举妄动。你没听过‘无为方能无所不为’吗?”
“好,你‘无为’,就等着我妈妈‘无所不为’地把我拉回去吧。”
娉婷翻个白眼,手膜做完了,脚也洗了,睡觉时间到,懒得和他啰嗦些没技术含量的话了。
看她这模样,陈君忆来气:“娉婷,你一点进取心都没有!瞧你的惫懒样,我妈妈迟早把我争取走的,到时,看你怕不怕!”
不晓得外间的人看见陈总舵主一付自夸自卖的耍宝相会不会笑到抽搐?反正,娉婷会。她笑来捂着肚子在沙发上翻来转去。过了好久,看陈君忆还是余愤未消,只好强忍下笑意,无力地抬手伸向他。陈君忆愤愤中,仍还是伸手握住。纤细光滑的小手在掌心里激出从未散淡的爱怜,他暗暗叹口气,在女子就力扑上来时,抱紧了她。
“怕呀。”她咬着他的耳朵,轻声笑说,“怕极了,只不过,我更怕你夹在亲情和爱情之间,左右为难,被这两种世界上最珍贵的感情伤害。傻瓜,你说我怎么可能不爱你、不在乎你?我只是不想让爱变成你的负担和伤害而已。”
陈总舵主心里的那个激动啊,已然汹涌澎湃地汇成了汪洋大海,将自己全部淹没。
当晚,玩到深夜方回的陈君予意外地看见父亲居然还在客厅拖着
sky玩。
“爸,很晚了,你不困?”他诧异地问。
陈爸爸耸肩:“那也要有得睡嘛。你大哥一回来就冲到我们房里,坚定、沉着地说:‘爸、妈,和你们商量个事,今年春节我想到娉婷家去一趟’……。”
“娉婷又给他灌迷魂汤了?”陈君予嘿嘿冷笑,“那也不该把你给撵出来呀。”
客厅太大,暖气开着也起不到多大作用。陈爸爸扯着sky的尾巴想把它揪过来取暖,被折磨了一晚上的sky拼着老命地往陈君予处攀爬,呜呜叫着救命。
“你知道你妈那脾气,一提到‘教育’两字就得要我回避,小时候还可以说是怕我当和事佬惯着孩子,现在,一个个弯着腰都比我还高,哪还和宠惯贴得着边?真是让她让成习惯了。这以后哇,我偏不让她,看她能把我怎么着。”陈爸爸絮絮抱怨。
被大哥的勇气激出好奇心的陈君予懒听父亲抱怨,蹑手蹑脚上楼,匍到陈妈妈的房间贴耳门上。身后,终于等回垫背人的陈爸爸童心不泯地随行,压低嗓门问:“听到什么?”
什么都没听见。里间,安安静静。
陈君予将耳朵和身体贴得更紧,陈爸爸也是。
房门骤然被拉开。早有准备的陈爸爸一掌扇过陈君予头顶:“臭小子,教过你多少次,听墙角最没素质的。就是不改。”
从小到大背黑锅已背成精怪的陈君予眼皮都不抬一下。
门口,陈妈妈笑容澹澹地对陈君忆说:“那就这么说好了,你早点休息。”
“嗯。妈,你也是。”陈君忆温文尔雅地走出来。
陈爸爸和陈君予两两惊视:没责骂、没眼泪、没愤懑、没委屈,今天是什么日子?
不对,哪怕什么都没有,至少还有责骂。看见陈君予,陈妈妈眼睛瞪圆:“君予,你终于舍得回来了?自己看看几点钟了?这么大的一个人,拜托你能不能懂事一点、正经一点,让你妈少操点心,多活两年……。”
陈君忆也跟着帮腔:“妈,你真该教训教训他。萱兰你也是见过的,有品有貌,德才齐备,女孩爱他爱得要命,他自己也说喜欢人家,可就是拖着不结婚。玩吧玩吧,要是把这样的女孩玩丢了,我看你拿什么去后悔。”
“哦,就是前段时间跟着他来家里玩的那女孩?嗯,是挺不错的。君予……。”
真真是神仙打架,凡人遭殃。陈君予万万没想到,大哥点起火苗,烧着的,却是自己。眼见成众矢之的,他伤心地夹起尾巴回房。身后,三人仍在继续他的八卦。
陈爸爸:“你怎么知道他和那女孩的事?”
陈君忆俨然成八卦资深记者,得意地说:“萱兰和娉婷是闺蜜,她俩啥话都说,娉婷从不瞒我。”
陈妈妈:“萱兰外貌很开朗,不过,她眉直间宽,这样的女孩从面相上看很泼辣哟,不晓得咱们君予和她在一起会不会吃亏。”
陈爸爸:“那小子就该着让他在女人身上吃点亏,要不,老以为自己风流倜傥,自命不凡的。”
陈君予不晓得自己今天是招谁惹谁了,进了房都还听得见那三口仍在津津品着他的韵事。
几天之后,他受伤的心慢慢愈合,这才想起问大哥春节的计划有否得逞。
“妈默了很久,才说,她不想我打破陈家的传统,但是,她尊重我的决定。”
陈君忆平平淡淡的回答再度惊得陈君予跳起。他仰头湛蓝天空:就算大哥使劲在吹,却也没见着有牛牛满天飞呀。大哥没有吹牛,那向来跋扈的妈妈这次怎么会这么好说话?
“我也不清楚。不过,妈要我老实回答一个问题:在我心目中,她和娉婷,谁更重要?”
“你用我教你的那招‘区别性地表忠心、表爱心’应付过去了?”
陈君予自认答案只有一个。不料,陈君忆凝重地摇了摇头:“我告诉妈妈,这问题和那道婆媳二人同时掉水里、儿子先救谁的问题如出一辙。”
想死也没必要做得这么决烈哇!陈君予扼腕叹息,忍不住更为好奇:“你是如何死里逃生的?”
任谁都想不到他会把那道世界性难题拿出来做,而且,真实、诚挚地写答案。陈君忆想起那天母亲听到那道题时的惊愕,他是如何死里逃生的?一听到他坚定地说春节要去娉婷家,母亲赶走父亲,坚决地答:“No”。
“可是,妈妈,只要我结婚,就总是要面对这问题的呀!”当时,他嗟叹,“即便我娶Sherry,也无法避开矛盾啊。换位思考,如果你生个女儿,打一出嫁就不能再回娘家过春节,或是,年年一个人回娘家过春节,她又如何自处?”
母亲的凛冽被他苍凉的话击弱了几分,她喃喃地重复了几遍“换位思考”,陈君忆不失时机地抛出了那道世界性难题。
“是啊,你先救谁?”陈妈妈怔怔地问。也许,换她自己来回答,也不会有太肯定的答案。
彼时,夜暮沉沉,母亲和娉婷的样貌却象有八千瓦的强光灯照耀着般,在陈君忆心目中清晰异常。
“先救谁?妈,这个问题还用问吗?我和你,是母子,我肯定,先救你。”陈君忆不用转头去看母亲,也清楚她听到这句话的宽慰。他双手抱臂,拥紧血脉亲情的同时,微微笑,将另一派同样浓挚的温情尽揽。“提问假设只能救一个。我救了你,再去找娉婷,天上地下,生生死死,我和她,不离不弃。这就是,夫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