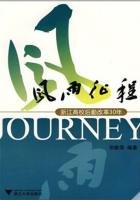那时候,夕阳下,波光粼粼的河面还是金色的,就落起雨来了。雨点渐渐密了,一河的金色流光被打碎了。
碎了以后呢?
对啦,芦花粉白粉白的。芦叶把脸颊划得怪痒痒。哥哥拉着她跑,穿过芦苇。脚下是松软的河沙,跑不快。哥哥说,以后一个人莫跑到河边来。又说,跑快点,雨下大了,淋了生雨要得病。……哥哥还说了,他不能老是像个逃犯似地躲在家里,他必须马上回学校去,丰娃子那一派的日子不会长,他们只是仗着人多,可我们是正确路线……她快跟他不上了,可还是拼命地跑,哥哥紧紧地拉着她的手,她觉得哥哥的手真有力。她说,从前丰哥常到我们家来,你们是好朋友,不该这么大的仇气。哥哥说,快跑,你真傻!这是路线斗争呢!朋友算什么,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突然,哥哥叫了声:“他们来了。”声音像闷雷一样。她停在他身边,抬眼看,只见前面一丛芦苇里闪出几个人来,都是公社中学的学生娃。哥哥一把将她拽在自己身后,命令她:“转过身去!”她并不惊惶,可她觉得此刻必须像一个真正的红小兵那样服从命令,转过脸去了。她又看见了河,雨点打在河面上,粉白的芦花,摇摇的,碎了的金色水面也摇摇的,更碎了……她听不懂背后的人们在说些什么,好像是骂着难听的话。但很快就没有声音了。她想看看勇士们怎么样了。便转过脸来,只见哥哥正埋着脑袋向那边扬沙子,而在这同一时候,像有无数根钢针突然扎进眼里,她只觉眼前一黑,不由自主地惊叫一声。她两手捂住脸,眼睛的深处一阵钻心的疼痛。双方立即停止攻击。哥哥回过头来,大声叫着她的名字:“小青!小青!”
对手们钻进芦苇跑了,只有一个黑瘦子没有跑,他愣了傻了似的站着,惶惶地走了过来,面色苍白,嘴唇打战:“小青,不要紧吧?……”没容他说下去,小青的哥哥直起身来,当胸一拳打去。这一拳打得太猛了,他跌倒在沙地上。但他完全没有反击的打算,爬起来,垂头丧气地溜走了。
“姓丰的,你记住,老子还要找你算账!”哥哥对着小丰背影,咬牙切齿地说。
小青叫着:“哥,我看不见了,我瞎了……”
一对亮晶晶的美丽的眼睛,半年以后真的就瞎了。人人都说怪可惜的。然而,那些年辰里,庄稼人连肚子都照顾不过来,可不就一对眼睛么,一个黄瘦小丫头的眼睛,能有几多要紧?
家门前有个小小斜坡,坡底脚横着一条石板路,石板已经残缺不全了,不知是哪个朝代铺的。路的外面有一坝肥沃田地。再往外,隔着大片芦苇,是大河。坐在家门口,可以看见路上行人南来北往,可以见着地里的庄稼,看见河滩的芦苇,以及河里的小木船。但是,小青什么也看不见了。
屋后有一架大山。全队的人家都把屋建在山脚,但远远离开,谁也挨不着谁。山很高,没有树。沿山有着好几处采石场。这里的石头特硬,卖到城里去修房造屋,或运到公社去修水库。石头永远也采不完。整天叮叮当当响,倒也热闹。小青从生下地的时候起就听熟了,这单调的音乐伴她度过了寂寞童年。如今,她什么也看不见,这叮当声倒成了不可缺少的。
父亲是个好石匠,但沾上了酒。攒不下钱。他没钱的时候常说,等攒起一笔钱来,送小青去省城的大医院治眼睛。可月终领得工钱,就赔进酒罐里去,喝得云里雾里的,连姓什么都忘了。他喝醉了还打人,打老婆,打儿子,只不打瞎眼的小青。和石匠打起架来,他总能把人打伤,赔上一点医药费。好像他不这样不能过日子。总之,他不是那种顾家的男人。家中日子艰难,小青她妈,在农业队里干活,闲日子在家打草鞋。她打草鞋打得结实又有样份儿,卖给石匠们。有时,还到石匠的工棚里领些破衣裳回来补,挣几个零钱帮补家用。
从下河一带来的石匠没家没室,而衣服裤子是时常要磨破的,又脏又烂,还汗臭,小青的妈不嫌,给他们洗净、补好送去。收钱也不在乎,由着人家给多给少。为石匠的生活服务的人也不少,老的,少的,姑娘媳妇都有,打草鞋、洗补衣服拆被子,卖零食、水果、糖精水。那年头只没有人开饭馆、卖私酒。采石工地办有伙食团,酒是供销社专营,可也有人不怕,偷偷在家卖酒菜。伙食团卖的东西有盐没味,不热烙,不少人就到那些“私人”家去加个餐。都是下力气的人,能吃就吃,钱攒不下就攒不下。没有钱寄回家里去,有些石匠的婆娘就找了来诉苦。婆娘来,工地上没得单人房间,都在工棚里打挤。做丈夫的倒没啥,女的不好意思,住上两天,钱没拿着也只好回去。这里是男人的“世界”,有些个人,就有了各自的“相好”。这地方原是挺封建的,自从开了采石场,来了大批石匠,封建就少了,有的妇女给石匠当“相好”,瞒着父母,背着丈夫。人世间无论什么好事坏事,就怕形成了风气,一成风气,就见怪不怪了。小青的妈也有个相好的。她本来比别人长得好看,瓜子脸,大眼睛,性情又随和,想和她勾搭的年轻石匠有几个,都不成。她那一个,是快五十岁了的半老头,黄黄瘦瘦,高个子,吐过血的。是她找他,不是他找她。几年里,没见他回过一次家,逢年过节也不离开采石场。他是隆昌县的人,虽然隆昌出好石匠,他的手艺可不咋样。他是劳改过的。他没有家室,整天沉默寡言,不吸烟,不喝酒,总是带个沙罐自己熬药吃。她找了他。悄悄地帮他熬药,或送些吃的去,逢年过节就让他到家里来吃几顿。他给她钱,她没要。小青的父亲也没话说,他挺讲义气的。那人对他也不薄,常借钱给他喝酒。那个人,待小青特别好,见了小青,眼光就变得温柔,充溢着那种父爱的情感,只可惜瞎眼姑娘小青看不见那眼光。全家人只有小青的哥哥不喜欢那外来人,他用一种阴冷的目光迎接他,从不招呼,更不和人家搭话。
日子就这么耐耐磨磨地过下来。
小青学着打草鞋。先学搓草绳,蓑草是哥哥从山崖上割来的。妈妈教她。经过很多次的失败,她就独自操作了,整天坐在堂屋里,草鞋架子放在怀面前。后来竟打出和妈妈打得一般光洁秀气的草鞋来,只是不那么结实。她的力气不如妈妈。后来越来越结实了,她长得比妈妈高了,肩膀也丰满起来。
她终日打草鞋,坐在迎门的阳光里。她什么也看不见,不需要光线来帮助她操作。但她喜欢阳光。她感觉得到阳光。每当一天过去,太阳的光线退到门外去,她也感觉到了,心里不免怅怅的。她不喜欢夜晚。她睡在被窝里等待天明。天明以后她又坐在门口去打草鞋,听着一片叮叮当当的声响从远远近近的采石场那边传过来。
世界留给她的最后景象,是夕阳染成金色的河面,是雨点打在河面上,破碎了的金色流光,是粉白粉白的芦花在风雨中摇晃,芦苇丛里飞扬着河沙……自从两眼瞎了以后,虽不再疼,但多年以来仍记得当时钻心的痛楚;当时她断定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灾难。沙子飞进眼睛里,妈妈给擦擦就会好的。谁知,擦不出来,眼球给扎坏了,这样的严重。
丰娃子来看过她。就在那场灾难以后,几天里,他天天来,她听见他对她说话,央求她原谅,还说要赔偿什么的。丰娃子每一次来,都叫哥哥给轰出去了,以后就再没有来。哥哥和丰娃子记了死仇。哥哥和丰娃子原来是很要好的朋友,他们不在一个大队,是公社中学读书结识的朋友,不久又为“观点”不一致,打起了派仗。但是,要不是因为她的眼睛,哥哥不会和丰娃子记死仇吧?小青常常这样想。她当时人小,简直不懂得丰娃子几次来看她的意义。也许并没有什么意义,赔礼道歉罢了;可是,后来,她觉得那是很有意义的,她盼望着他再来看他,听听他的声音也好。但显然是不可能的,来了也会被哥哥轰出去。唉……她长大以后,心里有时为这叹息一声。
哥哥到县城上高中去了。假期里也少有回家来,他在城里的工地去找零活干,给自己挣点生活费。他抽烟了,还喝酒,家里给他那点钱不够花。他给小青买回一副黑眼镜,小青高兴得很,戴着黑眼镜打草鞋,坐得累了就出门走走,走下斜坡,走上石板大路,有时还走到后边的采石场去。她慢慢地走,路太熟了,不要拄棍子。在采石场,石匠们都停下手上的活来看这个戴黑眼镜的漂亮姑娘。听见叮当稀落下来,她知道人家在看她了,心头很高兴。但她不停得太久,怀着愉快的心情,又回去打草鞋。
父亲又在外面和别人打架了。这一回,自己伤得不轻,被几个人抬着回家。妈妈没有出去找别人说理。找也没有用,石匠们就爱打架,争豪夺气,干部也管不了这种事。妈妈请了草药医生来看,说是打伤了内脏。草医三天来一回。两个月后,说是不行了,得送医院。送到医院去,又隔一个月,死了。花了不少的钱。妈妈没办法,借了那个“相好”的积蓄。不久,那个“相好”又吐血,打不成石头了,妈妈让他住到家里来,就睡在父亲从前睡的地方。哥哥毕业回家那天晚上,看见那人睡在妈妈的床上,当即和妈妈大吵了一场,夜饭也没吃,转身出门去了,声言再也不会回来。
有一天,小青坐在大门口,脑子里空空的,出神地“凝视”远处的平原河滩,突然觉得光线暗了。原来有两个人走上斜坡,堵住了大门。一个陌生的声音问:
“这儿是冯学海的家么?”
小青忙答道:“是呀!”
“冯学海是你的……”
“是我哥哥。他咋啦?”
“他犯投机倒把,判啦。你是冯学海的妹子冯小青吧?我们是公社的治安,今天接到县上通知,来转告你们家属……”
还说些什么,小青一句也没听见。心在往下沉,浑身没有一丝力气。
哥哥是她生命的唯一支撑。他曾对她说过多少次,等他毕业后,有了工作,就把她送到城里盲人学校去学习。这些年,她憧憬着那一天到来。哥哥说过,城市里,瞎眼的人也能有一份工作。现在,一切都完了……
落黑时,妈妈和“相好”从外面回来了。妈妈扶着他到乡场上去看病的。她在路上已经听说儿子在县里丢了监。她对小青说,明天她到监狱去看看,送床被子去。她说得很平淡,也没有流泪。
“妈,我也去!”小青说。
母亲好像没听见,骂了一声:“冤孽!”
左近一家人也姓冯,家里就一个老娘领着两个女子。大女子已经很大了,没出嫁,跟了一个外地的年轻石匠在家里过,算是“相好”。那石匠供养这一家。大女子和石匠都很“疯”,老娘管不住,怕脏了小女儿眼睛,学坏了,晚间就支使到小青家里来,和小青睡。这姑娘叫蛮蛮,有点傻气,但她懂得许多小青不懂的事。她无意间的谈话,教给了小青关于恋爱婚姻的道理和秘密。她说,她姐姐上个月里悄悄地去城里的医院做了流产,回来向干部请假,说是头风病发了,出不得工。可她姐姐却又不听娘的话,和那个石匠娃结婚。因为,姐姐说,这些石匠都靠不住的,打完了石头就飞了,都是些野人。
小青觉得自己简直离不开蛮蛮。蛮蛮夜里不来,她就久久不能入睡。这个在黑暗里长大起来的姑娘,除了缺少一对常人的眼睛外,她的身体哪一部分都和常人一样。这时,她才深深感到自己的不幸。她周身的血液,一忽儿变得灼热,恨不得打碎一些什么,冲出去,冲到山上去,冲到河里去;一忽儿却又变得冰凉,脑海里一片空白。而这一切她又无法确切地弄清楚是因为什么。她只隐约感到一种需要,一种很强烈的新需要,是什么呢?她不能明确地回答自己。尤其恼人的是她无法用语言表达那种渴望的具体内容,要是能够,也好说出来问一问蛮蛮。蛮蛮来了,她只能抱着蛮蛮嘤嘤哭泣。而她的哭泣也比常人痛苦,因为没有眼泪。
她像一条虫,一只猫,或一只老虎似的长大成熟起来。然而,她看不见这个世界。面前纵然已是万丈深渊,她也会走下去的。
妈妈顾不上小青。她的心整天在那个瘦高而多病的老石匠身上。老石匠病着的日子,她心焦如焚地为食物和药物去奔波;老石匠身体好起来,能够去干活挣钱的时候,她又完全沉迷在柔情蜜意中,四十岁的人了,那种缠绵,全不想想有个大姑娘在身边。小青看不见,当妈的也不把她放在眼里。而且,这些年来,妈妈真的一直把她当做一个残废无用的小姑娘,供她吃,供她穿,白养着她而已。
一天,小青问她:“妈,我今年十八岁了吧?”
她想了一阵,回答道:“二十了。”不再说什么。二十,在她看来,仿佛和二十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小青真的记不清自己的年龄了。她糊涂了,在前些年,每当冬天冷得睡不着的时候,她就知道一年又过去了,在心中默默地数着自己又长一岁。后来,常数,反而搞不清了。睡不着的情形越来越多,越数越糊涂。
二十。对了,蛮蛮自己说她十九。她曾被分派到采石场去清渣,那些不要脸的小石匠老要找些话逗她,老往她身上看。蛮蛮说,他们那些人肚皮不饿眼睛饿。想找女朋友又不争气,你和他多搭白几句,他就动手动脚,好像你心头真的有他似的。不想和他们来那一套,留着个清清白白的名声,哪些不好!蛮蛮不再去采石场做辅助工,她说,队里好几个大姑娘也不愿意去。虽然干那种活,能比在农业田里多挣工分,还有一点现钱支使,也拒绝去。可是,不多久,蛮蛮和那几个姑娘还是又去了。她告诉小青说,她不晓得是啥原因,就又去了。这个“不去了”,“又去了”,对于小青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她无比地羡慕她们。有一天黄昏时分,妈妈又挟着一大捆破脏衣服回来,丢在墙角的木盆里,准备明天洗。小青就觉得鼻孔里钻进一股味儿,从前可从来不曾有过这情形。她竟不由自主地蹲在木盆面前,把那些破衣拎起来闻着。妈妈见她这痴傻的举动,有点吃惊,骂道:“那汗臭味儿有啥子闻头嘛!整天没事干,二十岁了,还这么不懂事!真是冤孽……”她听着,突然像犯了罪似的,忙离开了。上床以后,老睡不着,那味儿总缠着她。
那味儿总缠着她。同时,一种羞耻心和犯罪感也折磨着她。不多久,刚刚丰润起来的面颊,就苍白消瘦了。
这情形,倒是引起了“后爹”的注意。他对小青的妈说:“这女子是病得深沉了,该领到医院去吃点药。”
小青的妈妈说:“该!哪个不晓得该,该去看病,该去吃药!我背得起两个药罐罐么?”
“我这病,医也医不好,不医也死不了。我说,还是给小青看病吧!”
“你挣了多少钱?你老觉着交了几七几八在我手上,是不是?这个月……”
“好啦,莫说了,我拖累了你们。”
“冤孽!死了吧!”
不知她骂的谁,人穷气大。但是,她还是同意了领小青去看病。
起了个大早。小青一手拄着根扁担,一手拉着妈妈的衣裳出门。她没有忘记戴上哥哥给她买的黑眼镜。一路上,累得什么似的。可那味儿还是老往鼻孔里钻来。到了公社医院,挂号等了半天,挨到进了诊断室,医生反复检查,结果说是:这姑娘没病,一切正常,只有眼睛不正常,但那是没法医治的。
石厂湾这个地方,叮叮当当的声音响了多少年,谁也没有寻思过。而一旦没有了这声音,想想,该是什么光景!人人都感到耳朵是不是有了毛病,人人都感到本来没盐没味的日子一下子变得更加枯燥和寂寞了。
说是,那个大水库的设计原本就不对头,选错了地方,经过三年的讨论,而今决定“下马”。水库决定“下马”,石头就不必再采了,打好的也不再运走。石匠们没处拿工资,纷纷卷铺盖走路,有的还乡,有的另谋出路,都远走高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