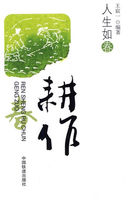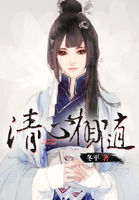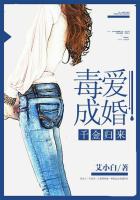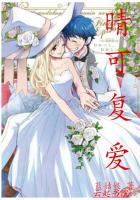双单向道:20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基本势态
下文说的是几点观察到的现象,不是分析,更不是评价。
就一个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而言,基本势态是:西方文化人来中国,是当老师;中国文化人去西方,是当学生。一百年来,这个格局基本上没有改变。原因是:西人来教的,中国人去学的,说是西学,实际上是普遍之学。更确切地说,西学一直被视为普遍之学。
现代中国一直有西方热,现代西方也一直有中国热。但是现代中西文化交往,一直是“两个单向道”——表面有来有往,实际是单向。
如何单向
中国人去西方当学生,西方人到中国当老师。这个局面已经一百多年,至今基本格局未变。从世纪初康梁到西方学维新之道,顾维钧马寅初等清末民初留学生,到五四一代(例如整个《新潮社》)几乎全部留学,一直到50年代的留苏,八九十年代的留美,中国文化人看来一百年还没有毕业;而西方人,赫德来教中国海关税法,庄士敦来给溥仪启蒙,李提摩太卡拉罕鲍罗廷教革命之术,杜威罗素讲现代哲学,瑞恰慈燕卜荪讲文学理论,一直到近年詹明信傅利曼,教的东西,学的东西,不是“西学西术”,而是“学术”。
这当然是老生常谈了。我想说的是例外,既是“规律”,就有例外,本无足奇,但这些例外常有规律可循。中国人在西方也有当老师的:在人文社科领域当教师的,基本上是“教国货”。从赵元任起,“海外学者”的教学研究大多与中国相关。自60年代起,中国人文社科留学生大量留居西方,造成近年来西方“中国学”的巨大进展。
以普遍理论,或以西方文化为专业的人,相当稀有;其中有独特贡献的,更是凤毛麟角。我曾经追踪卢飞白等在西洋教西方文化的人物,他们即使书教得不错,研究或著述,却很难坚持留在纯西方或纯学术领域,大多还是转向中国文化,或中西文化对比。
另一个例外,也一样不例外:西方到中国的当学生的,近年渐渐增多,但是他们绝大部分学的是汉语,或是作中国课题研究。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条让文化学者争论不休的口号,在实践中却是一目了然:一百年的实践,西学被等同为普遍性,为体;中学明白无误是特殊性,为用。我这么说,并不是赞同这种假定的普遍性,因为此种假定经常闯祸:李德到中国教革命战争,不明白面对的是中国战争;傅利曼到中国教价格改革,不明白面对的是中国市场。尽管有此种教训,西方性即普遍性,这个设定,基本如旧:今日的知识分子,认为可以套用西方学院左派的文化角色,建立中国学院左派;今日的时髦青年认为西方式酒吧舞厅文化,就是“文化”。
中国一个世纪翻译的西方文化文学著作,看来超过任何国家,几乎无书不译。但是有例外:西方人写中国的作品,哪怕影响巨大,如马尔罗的《人境》,赛珍珠的《大地》,一直无法使中国人感兴趣。即使译出,读者也看不出好处。批评家都怪“细节失真”,中国人自己写中国的作品,细节就那么真实?更主要的原因,恐怕是中国读者期待的西方性、普遍性被中国题材固有的特殊性破坏了。
西方人,不管他们对中国如何好感,很明白他们在当老师。詹明信到中国,讲的不是西方的后现代主义,而是“普世性”的后现代主义,并且想当然地认为适用与中国。他也讲中国文学,说证明了他的论点:第三世界的文学,具有特殊性质,都是“民族寓言”。我想不通:为什么鲁迅写的是民族寓言,而卡夫卡或福克纳不能读成“民族寓言”?
近20年来,海外华人的西文文学,蔚为景观,与林语堂的时代相比,已经进展巨大。这两种文学,有很大区别。但是两者有一个相同点:无论作者在哪里长大,无论使用何种语言,两类作者都是在西方写中国题材。由此也决定了这两种文学,都难以返回中国:林语堂用英文写的《京华烟云》名满欧美,哪怕林语堂是汉语散文大家,这本大作依然让国人看不到好处。至于汤婷婷的《女战士》,谭恩美的《喜福会》,在美国已经是现代经典,在中国始终受冷遇。
除了说,中西交流,实为单向轨辙,否则无法解释这个局面。
外行大师
西方对中国——这个希腊、希伯来文明最远的,也是最对应的他者——的密切注视,自17世纪耶稣会开始,至今已经有五个世纪。Colin Mackerras发现此种注视导致的“正面”与“负面”评价,形成钟摆式变动:大致每个世纪一变。但据他说,在20世纪,频率加快,有八次大摆动,几乎每十年一变。
此种摆动,受制于双向利益的周期变化:注视者(大部分关于中国的书籍与报道的作者)免不了受情绪影响。在先前,注视者大部分是传教士和外交官;在20世纪,还要加上记者和汉学家。所有这些“专业注视者”在西方文化中,大都是边缘性人物。作为一个集团,可能起相当大的作用,他们个人的影响力却有限,其爱憎不得不随“大气候”起伏。
然而,注视中国的,不只是这些专业人员。西方文化的核心人物——对现代文化的形成起了关键性作用的哲学家、思想家、艺术家、作家和诗人——他们的“中国爱好”超出于现实政治以上,更能凸现西方文化的长期关切点。而且,注视中国出于他们本人的主体意识需要,而不是职业必须。因此,如果他们的观察是负面的,例如巴尔特发现“文革”的口号政治是“符号过程的结束”,他就转到日本去寻找他的“符号帝国”,对中国三言两语打发。而不像“专业注视者”,失望就难免表示失望;“业余”观察者,不说便罢,真正钦佩才说话。现代西方的中国热,这才形成气候。
我不是说这些“一流文化人”超凡脱俗,他们也受制于正负摆动的大气候,但是有时我们会发觉,潮流正是由这些人推动,例如庞德之于“中国文字诗学”;马尔罗之于“东方革命热”,萨特等人之于“‘文革’热”。或许可以说,历史借他们的手推动潮流,而外行则是他们影响力的前提。
这与观察西方的中国人正成对比:中国专业翻译研究西方文化的人,尤其在本世纪上半期,常是知识界中坚:从鲁迅,茅盾,到傅雷,杨绛,都是如此。今天的人文学者,情况变化很大。但是谈到外国,依然不能容忍说外行话,说出来是丢脸的“硬伤”,内行才是影响力的前提。
三步三借
20世纪西方思想的主题,是现代性:先是推进深化现代性,后有反思批判现代性,最后试图代之以后现代性。有趣的是,每一步都起关键性作用的文化人“借鉴”中国文化——当然是外行地借鉴。
世纪初在各个文化领域中推进现代意识的人,哲学家如罗素、杜威,文学理论家如瑞恰慈、燕卜荪,政治学家如狄金森,美学家如弗赖,诗人如庞德、罗厄尔,都对中国文化给予令人感动的赞美,而且认为中国古代哲学,诗学,美学,具有“惊人的现代意识”。
一次大战之后,西方文化界的主流对现代性作反思批判。中国文化的某些方面,成为他们批判现代性的重要依据。最早是一批人道主义作家,如托尔斯泰,罗曼·罗兰,毛姆,以中国文化的受辱,抨击现代性与殖民主义之间的伦理矛盾;二三十年代,马尔罗,斯沫德莱,休斯,伊文思等作家艺术家,则进而寄希望于东方革命;奥尼尔,杰弗斯,以及50年代出现的垮掉派诗人作家,希望在道佛的清虚无为中找到对西方“过分的浮士德精神”的平衡;布莱希特,梅耶霍夫,阿尔陶等人推进的实验戏剧运动,则以中国戏曲为理想舞台,借以形成对意识形态的批判。
西方思想界从60年代后期,出现剧烈变化。从文化逻辑上,这是上述第二波的自然延伸。一连串的政治事件,主要是越战,中苏对立,以及“文化大革命”,直接推动了新思潮的兴起。存在主义的亲中国精神,在安东尼奥尼,沃霍尔等人手中变成中国图像,在斯奈德,布莱等人的诗中与“深度生态主义”结合;60年代末,法国结构主义突破进入后结构主义,德里达,索莱尔等人,以中国文字、文化传统颠覆西方的逻各斯中心,阿尔都赛,福柯,克莉斯苔娃等人,以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进行言说权力分析;此后,詹明信以中国为分析对象,把后结构主义导向后现代主义。
这三步的推进,全靠“非汉学家”。他们思想的“中国根据”,可以说全部是皮相之见,有时荒唐之甚。但是西方文化史的推动者,是他们,不是汉学家。实际上,如果他们对中国文化课题真正详加研究,他们就不得不成为拘泥“真相”的专家,而不再是西方文化的核心人物。考虑到这一层,它们对中国的阐释是否确当,只是一个次要的问题。
误读时髦
而在整个20世纪,西方学者到中国访问讲学,几乎绵延不断。某些特殊场合,例如抗战期间聚集武汉与重庆的西方文化人(奥顿,李约瑟,费正清,瑞恰慈,高罗佩,斯诺等等),例如70年代到北京的“文革亲历者”(宋塔格,克莉斯苔娃,安东尼奥尼等),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很大。
如果从他们各自在中国文化中发现“热点”上探讨,可以发现,20世纪西方的中国热,与先前几个世纪,有重要的区别。
曾经让莱布尼茨和黑格尔等哲学家为之着迷,为之高论一番的汉字文化,在20世纪更为迷人:费诺罗萨与庞德的汉字诗学,爱森斯坦的蒙太奇理论,德里达的“写作学”,索莱尔与克莉斯苔娃引申出的符号文化学。但是莱布尼茨与黑格尔,试图包揽全球文明,也认真地想对中文作个公正的评价;20世纪的讨论却有点明知故犯:庞德与克莉斯苔娃都承认过,汉语的真相,可能与他们的描述不同,但是无关紧要,他们演绎出来的复杂的理论,一样可以言之成理。
几乎相仿的情况出现在梅耶霍夫与布莱希特等戏剧实验家身上:他们对中国戏曲的观察,或许极为皮相(爱森斯坦还把戏曲舞姿比之于“中国象形文字”),但是发展出来的戏剧美学,的确发人深省,在现代文艺哲学的发展中,是个关键的转折点。以至于80年代的中国实验戏剧,都从他们的“误释”中寻找新起点。
第二个热点,则更与20世纪之前的关注点不同:除了狄金森,庞德,瑞恰慈等个别人,大部分中国爱好者都不再对儒家理论与政治秩序感兴趣,而道家与佛教(尤其是禅宗)却成为中国思想最迷人的地方。由于现代中国知识界,这两种思想缺少普遍热情,需要“参与”的垮掉派诗人作家,只能转向日本禅学或藏传佛教作为替代。但是道家对海德格尔和雅斯培尔的哲学,奥尼尔的戏剧,美国新超现实主义诗歌的影响,则无可替代。
第三个热点,是先前世代没有的。那就是东方土地革命,“文化大革命”。赛珍珠与马尔罗思想相差极大,他们笔下的中国,都离中国现实甚远。但是他们对西方30年代的影响,却相当类似。毛泽东对从萨特,威廉斯,到阿尔都赛,福柯,索莱尔,克莉斯苔娃,詹明信等西方学院左派奠基人,提供了一种非苏俄式的,也非纯西马式的,把支持“东方革命”与(西方)国内阶级斗争结合起来的新型马克思主义。
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后结构主义,却已经包含后殖民主义理论,三者很自然结合成一体。因为这三者都与中国有关。它们构成了主导西方学界的批判思潮,而批判必然需要模式的支持。后殖民主义学者,如赛以德,斯皮伐克,巴伯等,难以充分融贯马克思主义,因为作为他们的注视对象是伊斯兰文化或印度文化,这两种文化没有接受过,更没有创新过马克思主义。“文革”中国成为西方学院热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所有这些“热点”及其理论,都是西方文化“内需”的产物:其理论,其推论,适应西方文化内部话语权力平衡的需要。因此,批评他们“一厢情愿”,把中国“乌托邦化”,其实不过就是说,它们不能当作普世性的理论。虽然“来自”中国,却难以应用于中国。这与本文第一节所说一致: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讨论,自以为有普遍意义;在中国人眼中,一旦讨论中国问题,就失去了西方学说“应有”的普遍性。
哪怕看到这些皇皇大名,没有中国文化人,会糊涂到误认为克莉斯苔娃,福柯,詹明信等人对“文革”的观察,可以作我们的评价,就像不会说庞德或德里达对汉字的见解,可以给中国文学现代性。
中国特殊性,并非绝对不可能沿双单行道开回来。例如近20年中国“实验戏剧运动”就成功地把借鉴西方实验戏剧,解释为回到中国戏曲源头。但是任何此类“出口加工”式的借鉴,要中国思想者作双重转化阐释——先还原到西方现代的文化动机上,再还原到中国当代的必要性中。
把西人的无心误读,变成我们的有意错用。此中曲折的借鉴策略,看来复杂之极,实际上自然而然:沿着两条单行道,来回搭顺风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