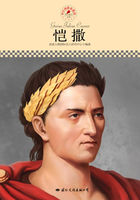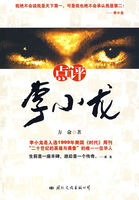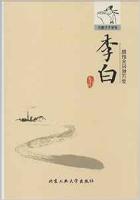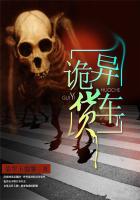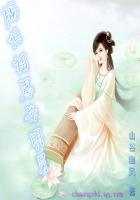五原举旗
1926年春,随着国民革命浪潮在全国不断掀起高潮,国民军在北方的势力也随之壮大。1925年3月,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之下,苏联政府通过了援助国民军武器弹药并派遣顾问和教官的决议。苏联认为主要目的不在于支持冯玉祥,而在于“按照广州的实例建立起对革命运动的实际支持。”
[苏]维·马·普里马科夫:《冯玉祥与国民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8页。是年5、6月间,冯玉祥接受苏联专家的帮助,在半镇厅建立骑兵学校,在平地泉建立了炮兵学校,随后在张家口,为军队的高级军官成立了高级军官学校,接着又在张家口成立机枪学校,以及小型通讯、工兵学校。这些学校共接纳了700多名官兵,通过训练军官的途径,达到整训全部军队的目的。与此同时,国民军得到了苏联援助的一批步枪、子弹、大炮、山炮、手榴弹、机枪、迫击炮及药品等。
同①。
奉军入关后,张作霖挟其余威,不断增兵关内,扩充地盘,而吴佩孚也企图东山再起。在南北压力之下,冯玉祥审时度势,进一步扩充和改造了军队。首先,将国民军一军扩编为步兵12个师、骑兵2个师,炮兵2个旅。冯的辖区除察、绥、甘三省外,还有北京地区,南苑至张家口均为冯军驻守。加上胡景翼、孙岳的国民军二、三军,总兵力已达40多万。其次,在苏联的帮助下,加强了空军建设。在北京设航空司令部,拥有20余架飞机,在北京、包头、张家口、平地泉、归绥等地,设有临时飞机场。再次,有中共北方党组织李大钊的帮助,此时的冯玉祥从苦闷、消极和徘徊中焕发起来,精神振奋。冯玉祥在治军中的壮举及国民军势力的壮大,自然会引起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日益恐慌,为了镇压国民军进而扑灭全国革命的烈焰,奉系军阀张作霖大造北方“赤化”的舆论,他们诬称孙中山及广东革命政权为“南赤”,冯玉祥及国民军为“北赤”。于是纠合各路军阀、反动势力,拼凑所谓“反赤大同盟”,进而组织起“讨赤联军”,与帝国主义勾结,对冯玉祥及国民军大举进攻。1926年1月5日,张作霖通电吴佩孚表示谅解。于是,由帝国主义牵线的反动军阀大联合之势,宣告形成。
当此紧要关头,冯玉祥感到险象环生,内外交困,于是想以辞职来避免战争,扶大厦之将倾,保存国民军实力。3月20日,冯玉祥在卸下西北边防督办一职后,携夫人及随从人员,由平地泉取道库伦赴苏联参观考察,5月9日抵达莫斯科。
在苏联,冯玉祥会见了苏联党政军高级领导人和共产国际负责人,参观了社会主义苏联的工厂、学校、军队,这些无不对冯玉祥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在苏联期间,国共两党都对冯玉祥伸出热情之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徐谦多次与冯长谈,启发他的革命思想,并劝说冯玉祥加入了国民党。
参看泰棻《国民军史稿》第301页。
于右任受
国民党中央委派专程赴苏敦促他回国参加国民革命。中共党员蔡和森、刘伯坚亲自对冯玉祥做了大量工作,这对冯及其国民军后来参加革命策应北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蔡和森是中共创始人之一,冯玉祥访苏期间,正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负责人。刘伯坚也是中共杰出的活动家,早年赴比利时勤工俭学,此时正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中国班学习。
由于他早就负责国民军将领到苏联学习考察的接待工作,因而冯玉祥对他早有耳闻。蔡和森、刘伯坚与冯玉祥的密切接触与往来,使冯玉祥对中国共产党和党的干部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冯玉祥很器重刘伯坚。他向共产国际提出,要求派刘伯坚和他一道回国去主持政治部的工作,共产国际同意了他的请求。”参看《刘伯坚》(《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四辑)。
7月,国民革命军在广州出师,一场旨在彻底埋葬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的北伐战争拉开了序幕,冯闻讯后倍受感动,认为革命道路已经开辟,革命的时机已经到来,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决心投入这场伟大的革命。在苏联政府的支持和国共两党的直接帮助下,他毅然决定回国,响应北伐。8月17日,冯秘密离开莫斯科,经蒙古库伦于9月15日到达绥远的五原镇。(今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五原县。)这是一个“空落落的土围子,人烟稀少,荒凉冷落得赶不上内地一个较大的村镇”。加之时至初秋,气候已寒,大地一片茫茫。冯玉祥来到五原时,正值国民军与奉直军作战失利,部分部队先后从南口退守到河套地区一带。
从冯玉祥通电下野到苏联考察的几个月间,国内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3月12日发生日本军舰闯入大沽口开枪打死打伤国民军事件。数日后,北京发生“3.18”惨案,段祺瑞政府卫队开枪打死游行示威群众47人。次日,靳云鹗指挥“讨赤联军”3个师11个旅约12万人,自河南分三路北上围击国民军。4月间,奉、直、鲁各派军阀联合向国民军总攻,兵分五路进攻北京,15日国民军退出北京,扼守南口。7月间,各系军阀会攻南口。经过数月激战,国民军有生力量伤亡过半,饷械俱缺。眼看与陕、甘断绝联络,乃于8月15日下令总退却,撤出南口,向绥远、包头、宁夏一带节节败退,战线延长二千余里,退却时所经道路,不是崎岖山路,就是广漠沙场,穷僻村落,交通不便,命令既难准确迅速下达,行军给养更感筹措困难,生活困苦,军纪松弛。有的已被敌军收买,国民军已处在土崩瓦解的状态。
面对此种状况,冯玉祥决定召集旧部,整顿军队,重新树起国民军的旗帜,以壮革命之威。冯玉祥不仅和国民军一军的将领见了面,而且和国民军三军的孙岳、五军的方振武、六军的弓富魁及二军的邓宝珊等人一一相见。这时统计各部武装力量,除原驻甘肃的之外,尚不满5万人。此时,韩复榘、石友三等将领因率队西撤时,给养困难,遂投靠了晋军,暂归商震节制,韩部驻归化、石部驻包头。冯玉祥抵五原后,国民军各部闻讯纷纷向五原集中,韩复榘、石友三等部也相继归来。
冯玉祥稍事休息后,即召集国民党左派代表于右任和国民军旧部各路将领,商讨重振国民军之大业,经商议决定组成国民军联军,一致推举冯玉祥为国民军联军总司令。
9月16日下午,冯玉祥在五原城内西北一平坦广阔的河滩上,就地取材,快速筑起了一个誓师台,于9月17日中午举行了誓师大会。宣誓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响应北伐,并宣布全体加入国民党。冯玉祥在大会上宣读了由国民党中央代表于右任亲笔书写的《誓师宣言》,慷慨激昂地郑重宣告全国,兴师转进,重振旗鼓,将与北伐军会师中原。共同铲除国内封建军阀,打倒帝国主义,誓死为国民革命奋斗到底。并以之勉励部属,激励士气。
五原誓师宣言是冯玉祥代表国民军宣布的新型政纲,标志着冯正式脱离北洋军阀,参加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参加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举起了北伐的大旗。
五原誓师后,冯玉祥采取了一列系措施,促使国民军重振雄风。
第一,加强与苏联的联系,争取苏联政府的支持。为了使国民军的高级军政官员及时地学习苏联革命胜利和苏军建军经验,冯玉祥组织以鹿钟麟为团长的国民军赴苏学习考察团。
团员中有他最亲信的师长程希贤,高级官员邓哲熙、浦化人和南汉宸等。他们在苏联开阔了眼界,得到苏联在军事和政治上极大的帮助。代表团回国时,冯电令鹿,留邓哲熙为他驻苏代表,继续保持和苏联的密切联系,同时也和共产国际建立了关系。第二,整编部队,重振雄风。国民军南口兵败后,各部损失极大,东零西散,不成体系。有的团不足二、三百人。有的旅也只剩下四、五百人,而且军纪废弛,军不成军。冯玉祥组建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委任鹿钟麟为参谋长,何其巩为秘书长,李兴中为参谋处长,石敬亭为政治部长,刘伯坚为副部长,又聘请苏联人乌斯马诺夫为政治军事顾问。冯针对所部溃败之余,精神涣散的状态,认为现在急需灌输革命思想、三民主义理论,使部队得以迅速振作,提出军队政治化、打破官僚习气、拔除阳奉阴违祸根的三个口号。整顿了军容军纪,遏制了溃乱现象。同时召唤旧部,重新加盟。一些曾在冯出国期间脱离冯军的部下纷纷回到国民军联军,石友三、韩复榘等人曾离冯投阎,这时也抵达五原,表示了忏悔之意,重新归入国民军联军。第三,加紧在国民军内的组党事宜。9月27日,冯玉祥在五原召开中国国民党国民军联军代表大会。会上成立了最高特别党部,由刘伯坚宣讲国民党的主张和北伐的意义,冯报告国民军联军及国内外形势,选出了方振武、刘伯坚、任右民、赵守德、王一飞、张兆丰、续培模、张允荣、武勉之、弓富魁、石敬亭等11人为执行委员;徐谦、冯玉祥、于右任、刘骥、史宗法等五人为监察委员周新一:《国民军的新生》,政协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编:《冯玉祥与五原誓师》(内部发行),第182页。。并发布命令,军队所到之处,必须帮助地方发展党务和民众团体,明确提出一些要求:首先,军队需要与民众结合,举凡保民爱民帮助民众等工作,务须切实力行。其次,军队党务训练工作、政治工作,俱属至要,所有各级党部,须迅速组织成立,以便指导规划。再次,地方党务、亦须尽力发展,各军所到地方,务即帮助地方党员迅速组织党部,在物质上,精神上均须尽力帮助。如给以印刷物品,办党经费,派人指导等等……周新一:《国民军的新生》,《冯玉祥五原誓师》,第188页。国民军联军中的建党及整顿党务,改变了过去军人不干政、不入党、不问政治是非的陈腐观念,使国民军联军开始成为一支具有初步革命志向和信仰的新型军队。
冯玉祥举旗五原,使国民军联军迅速成为北方地区一支反帝反封建的重要军事力量。它获得新生后,便开始了再一次的西北征战,挺进甘肃、陕西的战场。
李大钊提出进军西北的建议
五原誓师后,对冯玉祥来说,首要的问题便是如何进入北伐战场,并在北伐战争中使国民军军威再振,真正成为当世之雄。就当时的情况,总的说来有利于革命势力的发展,但具体到局部战场看,尚不平衡。一方面,国民革命军正在开辟两湖战场,北伐部队在两湖地区与吴佩孚、孙传芳激战,并有势不可挡之势。1926年9月,北伐军中路各部队,以叶挺独立团为先锋,先后在汀泗桥、贺胜桥取得重大胜利,一举挫败吴佩孚主力的气焰。吴佩孚把持北京政权,倾中原七、八省之财力、物力,经营数年,企图扫荡异己,以武力“统一”中国。而在北伐大军的打击下,数日之间,一败于汀泗桥,再败于贺胜桥,狼狈而走,仅以身免。9月初,北伐军已直逼武汉,武汉三镇已人心惶惶,北洋军阀在长江中上游势力已所剩无几。另一方面,中原一带的河南、山东、直隶诸省,张宗昌在张作霖支持下,为虎作伥,与直系相勾结,组成所谓直鲁联军,拥兵30余万,企图利用多年统治的基础,继续阻止北伐军的胜利进军。
直鲁联军的目的很明显,在吴佩孚败退后,一是由他们对付日益北上的国民革命军,二是在京津形成堡垒态势,以做最后的顽抗。这便给冯玉祥及国民军联军迅速投入北伐主战场造成一定困难。当时,仅靠冯自身力量,无论从数量上,还是经过南口战败的兵员战斗力上,均难以与奉张相匹敌,不可能在京、津地区与奉张再一决战。而欲联合北上的国民革命军又相距甚远,无法直接联合。此时,冯玉祥军中产生两种主张,一种是“由南口攻北京”,直捣北洋军阀老巢。另一种意见是,由五原挥师西征,进取陕西,出兵潼关,与北伐部队南北对进,会师中原。
然而,这两种方案都面临很大困难。如果国民军联军由京绥铁路向南反攻北京,取胜把握不大。如果向秦陇、包头西进援陕,又感兵力单薄,且西安被围已达数月,困难颇多。何去何从,国民军对这样一个战略问题争论不休。
正当冯玉祥处于举棋不定的困惑之中,9月下旬,中共中央对此作出了明确决策:“国民军现时地盘,只剩得甘肃及绥远一角,非取西安不能生存。得陕西后,可望东出潼关,沿陇海路直下河南,与北伐军联成一片。退亦可暂自保,以备将来与南方北伐军夹攻奉军。”《中央局报告》(1926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
而中共中央对国内北方局势和冯玉祥部队所处环境的客观认识,是来自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对此进行了大量考察和科学分析的。早在五原誓师前夕,李大钊于9月8日在给中共中央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了国民军的作战方针应是平甘援陕,东出潼关,会师中原。李大钊在报告中说:“出兵陕西,经富(府)谷县、佳县、延川、洛川、耀县,攻取同州,直扑潼关,一可以阻止吴败退入陕之路,一则可以解西安、三原之围。”《 守常政治报告》(1926年9月8日),《中央政治通讯》第3号(1926年11月15日)。五原誓师后,李大钊即派人将这一战略计划送给冯玉祥。
冯玉祥在其所著的《我的生活》中记载了这一当时情况:
“常有秘密文件带给我,都是写在绸子上或缝在衣服中,到手后,须用药水浸泡,始能现出字迹……李大钊等各位先生的信件和给我的作战计划等。他们多主张我们出宁夏、取潼关,而后会师北伐。”冯玉祥:《我的生活》(下),第500页。
冯玉祥接到李大钊的密函后,豁然开朗。当即召开高级将领会议,认真研究讨论,进一步领会到,出师南口,进攻北京,则敌强我弱,恐难取胜,且不能与南方北伐军互相接应,互相支持,更无法解西安之围。而入陕西,出潼关,则既可救陕西被围困之国民军,又可与北伐军会师中原,形成一支更加强大势力,直取北京则有较大把握。于是,一致决定,采取李大钊的战略建议,实行“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八字行动方针。即先驰援西安,而后出潼关,会师郑州。这一战略方针,正如当时中共中央给李大钊的信中所说:“国民军的出击,是构成阻止奉军南下,策应广东国民革命军胜利北伐的重要因素。”应当说这一方针的制定,从战略上使冯玉祥找到了一条由衰转盛,由败而胜的途径,更说明当时中国共产党对西北地区在北伐战争中所处的战略地位是有足够认识的。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即如何协调好与山西阎锡山的关系。
国民军联军为了南下进攻陕西,必须设法争取阎锡山保持中立态度,若能取得阎的合作将更有利一些。否则,晋军若与国民军为敌,国民军联军东侧必将受到晋军威胁,对于攻陕造成极大困难。因此,如何“联晋”以消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便成了西进战略的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