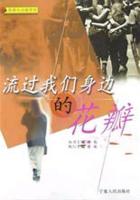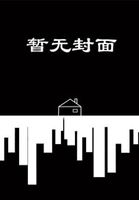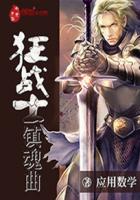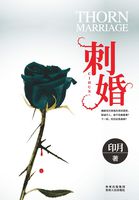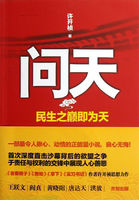(第一节) 叙述格局
一
中国传统小说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形式上惊人的一致——“模拟”或“保持”口头文学的诸特征,以致文学史上一直用其形式特征称呼之:“平话”,“话本”,“拟话本”或“说部”。
但“话本”这词意义不清楚,它可以是说书人表演的记录(“录本”)或是说书人手头参考书(“母本”)。从后一个意义上说,它不是为阅读而制作的;从前一个意义上说,是为阅读制作的。究竟为何义,史家从未弄清。鲁迅在讨论《全相平话五种》时说:“观其简率之处,颇足疑为说话人所用之话本,由此推演,大加波澜,即可愉悦听者,然页必有图,则仍亦供人阅览之书也。”这样,话本既是记录之本,又是演出之本,两者兼用。然而,如果认为古代白话小说是从口头文学演化出来的,那么,文本的口头文学特征,应当是越早越明显,渐渐消退。事实恰恰相反,古代白话小说从宋至元至明,其口述文学特征不是渐渐消退,而是开始时很少,渐次加强。“拟话本”比“话本”更具有口述性。
实际上,这两个词现在用来作为古典白话短篇小说的时代划分:现存的被文学史家公认是“话本”的小说,是宋元白话小说的代称,明代出现的小说,就被认为是“拟话本”。本来这两个词应当是标明古典白话小说的口述文学源流和演变方式,实际上很容易引起误会。
目前可以确认的唐五代话本“真本”只有敦煌变文。
从敦煌变文中看不出口头叙述文学的形式特征。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它们只是节要。后世“话本”或“拟话本”小说中据说源出说话艺术的种种风格标记,在敦煌变文中完全找不到。
现存的某些白话短篇小说,据说接近唐代说话原本,如《庐山远公话》《韩擒虎话本》《叶净能诗》等等,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使用浅近俗化的文言。现存宋元讲史话本中,保存宋话本原貌最多的可能是《大宋宣和遗事》,全书文言和白话相间,文言部分大抵源自旧籍,白话部分多为民间传说。而正由于这些白话部分,不少研究者认为它是半拟话本,非真话本。这样一说,话本与拟话本的区别似乎又是文体上的——不像口述艺术原貌的可称为话本,用白话写成而酷似口述艺术原貌的,反被认为是拟话本。
聂绀弩先生曾经谈过这问题。他指出:真正的话本供临场发挥,而在模拟的写本中,“话说”、“欲知后事”、“有分教”反而得全部写上,有一百次就得写一百次。他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
孙楷弟先生曾指出:“明末人作的短篇小说,从体裁上看,与现存的宋元话本相去甚微,但论造作的动机,则明人作短篇小说,与宋人编话本不同。” 他强调话本供说唱参考,而拟话本专供阅读。这里就产生了一个悖论:供说唱参考的,反而不需要口头文学诸标记,而为阅读而制作的,反而要努力保持(不如说,设立)口头艺术诸特征。
如何解释这奇怪现象呢?
唯一可能的解释是:既然中国传统小说叙述形式上的口述文学特征不是话本的程式,而是拟话本的程式,那么,它们也不是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的起源——口述文学留下的痕迹,只能说它们是中国小说由于某种需要而采用的程式。一定要说古代白话小说保持口述艺术特征,不仅不符合文学史,而且会导致许多错误的理解。
中国白话小说漫长的改写期中,由于白话小说在中国文化的文本层次中所处的几乎是最低的地位,它的文本丧失了著作主体,只剩下编辑主体,而编辑主体的非权威性使文本难以固定。这时期白话小说任何文本都有可能被不断改写,不管是话本还是拟话本,不管是旧著改写,还是创作,几乎每一次的刊印都是一次改写。
改写,成了小说文本存在的基本模式,不断改写造成写作主体特征平均化。从而使所有的中国传统小说形式特征趋向于均质一致。这种均质口述性并不是口述文学传统的结果(许多民族有比我国更漫长的口述文学期,却并没有口述模式化的小说),而是长达四个世纪的改写的结果。
明末改写期结束时,主体平均化与叙述特征均质性已形成了强大的叙述程式。即使如此,当中国小说进入创作期,小说作者们也并没有这个义务非要接受这个传统程式。这个传统程式得以延续的原因,是白话小说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没有改变,不管作者本人在创作中投入多少精力,对他自己的创作成果多么珍视,白话小说文类限制了它的文本地位,从而限制了它的著作主体强度与叙述形式的独创可能。
中国小说在改写期和创作期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证明这传统程式本身没有完全抑制主体对文本意义的创造力量。只有当整个文类的文本地位有所变化时,传统程式才有可能起根本的变化,这种情况,到晚清才出现。
固然,说古典期中国白话小说形式完全匀质,有点夸张,个别优秀作品突破传统程式,取得了很有意义的成绩。本书将强调指出在传统程式的压迫中取得这些突破是如何难能可贵。
从叙述学观点来看,口头叙述与书面叙述有本质上的不同。口头叙述是一种多中介传达,其物质表现形式(表演者的演艺、声音、服装道具布景等)在叙述文本(广义的文本)中结合得很紧,使得其文本本质上是“非重复的”。每次表演都创造一个新的文本,不管表演者对“底本”如何忠实。为了平衡这种非重复性,为了稳定表演的接受与理解,程式在口头叙述中就变得很重要。反过来,程式又保证了口头叙述所传达的意义之确在,保证了传达之有效。
而书面叙述情况则大为不同。书面文本的物质表现形式,(写本、抄本、版本等)与“文本”是互相脱离的,只要文本的语意没有变化,不同版本的文本实为同一意符。因此,书面文本本质上是重复性的(可重印,可重读)。相对口述文本来说,程式不是至关重要的稳定因素。重读的可能使书面文本在叙述技巧上出格创新的弹性较大。中国白话小说处于上述两者之间。它具有重读的重复性,却并没有重印的重复性。每次刊本的不断重写使它的重复性大为降低。重复性减低,使程式变得相当重要。
当然,书面叙述文本不是完全与其物质表现形式无关的。一部分超文本形式特征直接进入叙述。
第一类这种特征是图像性的,《金瓶梅》中引到公函牒文,照录了其顶格、空行的格式(就像现代小说说到主人公收到电报,也会引用不加标点符号的电报文),《红楼梦》写到通灵宝玉时,就画出了宝玉正反面的形状——这不是插图,插图是文本之外的类文本(paratext)因素,因版本而异,而通灵宝玉的图像是任何版本无法删去或更改的(就像《约翰·克利斯朵夫》中的乐谱),它们是叙述文本的一部分。
另一类是分章分节分段标点等印式特征,这类特征与文本结合得很紧,但于文本是“半加入”式关系,直接影响到文本的基本形态。在本书的讨论中,将详细谈到中国白话小说的印式造成的重要叙述学特征。五四小说的产生,如果没有“西式”标点、分段等印式,几乎不可想象。所以当时上海鸳鸯蝴蝶派作家把五四作家称为“新式标点作家”,倒也并非简单化的恶谥。
反过来说,传统白话小说的现代版本,都加上标点,有的甚至给予分段。这样,文本就受到了比以往任何改写更严重的变异。本书将谈到现代版本引入的物质形式特征对白话小说文本造成的诸种难题。
二
在非艺术的叙述中,口头叙述者与书面叙述者没有根本的区别,新闻报告者,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都是信息的实实在在的发出者。
但是虚构性叙述(小说,叙事诗),口头叙述者与书面叙述者很不同。在口头艺术叙述中,叙述者无可怀疑地是叙述信息的发送者,他是个有血有肉的存在,信息的接收者可以与他直接接触交流。叙述的作者(如果有个作者的话)反而只是一个假定,叙述行为并不一定需要这个假定作者才能成立。口头叙述者是文本信息主体的完整的、“饱和”的实现。
在书面叙述中,叙述者只是一个叙述学上的功能,一个“纸面上的存在”。是作者“偷听”到这个叙述者讲的故事,写到纸上成为叙述文本。实际上这个叙述者是作者创造的作品中的一个人物,一个特殊的人物。作者在创作整个小说时,必须创造这个特殊人物,并且安排他与整个叙述的各种关系,从而使叙述者能完成如下功能:
作为与叙述接收者相呼应的主体——传达职能;
作为小说的讲述者——叙述职能;
作为叙述进程的控制者——指挥职能;
作为对叙述中的故事之评论者——评论职能;
自己作为一个人物——自我人物化职能。
热拉尔·热奈特曾经讨论过叙述者的诸职能,他谈得略嫌混乱,而且他没有指出一个关键的问题,即口头叙述者与书面叙述者在完成以上职能的方式完全不同。在口头叙述中,叙述者自然而然地执行这五个职能,五种角色都是他的实体存在之自然推演。
他说话,他发出叙述信息;
他与叙述接收者——听众——直接接触,互相呼应,甚至当堂交流;
他控制着叙述进程,随便可以根据听众的反应添入解释,使听者不至于糊涂;
他君临于叙述“世界”之上,随时可以对叙述加以道德上的评论或解释,使听众得以“正确”理解叙述的故事之意义;
他可以用动作或声音模拟叙述中的一个人物,此时,他暂时搁置叙述者身份。
而在书面叙述中,叙述者只是个纸面存在,他虽然也得完成以上职能,方式却很不相同。
他唯一能比较自然地完成的只是自我人物化职能,因为他本来就是小说中一个特殊人物。他并不需要搁置他的叙述者身份,他本身就是一身兼二任。只是,他只能做一个固定的人物,他不可能任意改变身份。
除此之外,他完成其他四个职能的能力就很成问题了。
他只是叙述信息的假定的发送者,他自己是被叙述创造出来的。在书面小说叙述中,也会出现对叙述进程进行控制的语言(“花开两枝,各表一头”)或对叙述的故事进行道德评价(“看官,世上毒莫毒过妇人之心……”),但是我们既无法肯定这些话应当算作者的话,也无法把它们当作一个人物主体所发出的意见,毋宁说,这声音来自这两者之间一个非实在的“主体”。
小说叙述文本是假定作者在某场合抄下的故事。作者不可能直接进入叙述,必须由叙述者代言,叙述文本的任何部分,任何语言,都是叙述者的声音。叙述者既是作品中的一个人物,他就拥有自己的主体性,就不能等同于作者,他的话就不能自然而然当作作者的话。正如口头叙述中,当叙述者乔装一个人物说话的腔调时,他不能同时作为叙述者进行指点或评论。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书面小说叙述中一个最基本的矛盾:发送信息的主体分化了,分成两个——作者与叙述者。(在非虚构书面叙述者,这种情况不会出现,因为作者并不需要塑造一个叙述者,他自己就是叙述者。在新闻报道中,报道者就是叙述者。)
这个区分之所以有必要,是因为这二者在对叙述所采取的语调上,价值判断上,态度上很可能不一致。作者不通过叙述者不能直接在叙述中说话(因为整个小说是他用某种方式记录下来的叙述者讲过的),而叙述者既是一个人物,他说的话就不一定是作者想说的话。因此,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中所用的术语“作者干预”(authorial intrusion),在叙述学上是不能接受的。在本书中,我改用“叙述者干预”。
在口头叙述中,在非艺术书面叙述中,叙述者高踞于其叙述行为之上,他是个叙述的叙述者;而在书面艺术性叙述中,叙述者的人格是叙述产生的,是他自己的叙述行为的结果,因此他既是个叙述的叙述者,又是个被叙述出来的叙述者。这是理解虚构性书面叙述的一个关键问题。
在不同书面艺术性叙述中,叙述者的自我人物化程度是不同的,也就是说,他在叙述/被叙述的两难之境中的位置可以变动,形成不同的叙述表现方式。叙述学研究者一般区分两类叙述者:现身叙述者与隐身叙述者。现身叙述者是明显地被叙述出来的叙述者,出场的叙述者;而隐身叙述者是不明显地被叙述出来的叙述者,即从不出场的叙述者。
现身叙述者常被称作“第一人称叙述者”;隐身叙述者则称作“第三人称叙述者”。这两个“俗称”易引起误会,因为任何言语主体凡要提起自己,只能用第一人称(即自称“我”或“我”的变体,如“说书的”),第三人称叙述者只是不说起自己的叙述者。
隐身与现身这两个术语所指的,实际上是两种极端情况:几乎不可能有完全隐身到不露任何痕迹的叙述者,绝大部分隐身叙述者只是隐到一定程度而已。这种隐身程度与叙述者执行上述五个功能的个性化程度正成反比,也就是说,叙述者越是现身,他在叙述中的声音越“清晰”。如果叙述者做到完全隐身(在所谓“墙上苍蝇式”叙述者的现代小说中),他的叙述读起来好像来自虚空。
分析中国传统小说时,这个“隐身程度”概念特别重要。因为中国传统小说的叙述者的自我角色化是固定的,他总是用第一人称自称“说话的”,或“说书的”,而且在进行干预时总是毫不犹豫地亮明自己是以叙述者身份进行干预。但是他从来不在叙述的故事中扮演一个角色,他是个“出场但不介入式”叙述者,这就使他能处于隐身叙述者与现身叙述者的地位之间,进行一种具有充分主体权威却又超然的叙述。
叙述者的这个地位是中国传统白话小说这文类预定的,是不可更改的。在中国传统白话小说中,有个别例子(例如《红楼梦》),叙述者自我化的程度加强,多少变成了叙述中的一个人物。可是这种自我化往往发生在楔子之类开场中。当小说进行下去时,叙述者不再记得他的新身份,而依然以“说书者”这个不加入式显身叙述者身份讲述全部故事。
三
叙述者的职能之一是招来叙述接收者,并与之相呼应,因为任何信息传达从定义上说必须有个接收者。
叙述接收者在叙述中相应地完成五个职能:
与叙述者的叙述职能相应,他是听故事者;
与叙述者的传达职能相应,他是叙述信息的接收者;
与叙述者的指挥职能相应,他需要叙述者告诉他叙述如何展开故事,以便弄懂叙述技巧;
与叙述者的评论职能相应,他需要叙述者告诉他如何理解故事;
他多少是被人物化的,也就是说以不同方式在叙述中作为一个人物出现。
前面四个职能是与叙述者相呼应而形成的,只有最后一个职能可以说是独立完成的,但也要靠叙述者讲述出来。没有叙述接收者与叙述者相呼应,叙述者不可能完成其职能,叙述行为要靠这两个人格合作才能完成。叙述者不可能对着虚空讲故事,叙述者也不能无缘无故发表评论。从这个意义上说,叙述接收者与其说是需要听叙述者的评论,不如说为这些评论提供了借口。